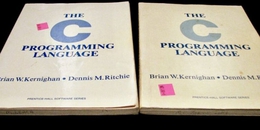Covid的起源:人或自然开放潘多拉的盒子吗?
Covid-19大流行破坏了世界超过一年的世界。它的死亡人数很快就达到了300万人。然而,大流行的起源仍然不确定:政府和科学家的政治议程产生了厚厚的混淆云,主流媒体似乎无助地消除。
在如下所以我将归功于可用的科学事实,这占据了发生的许多线索,并为读者提供了证据制定自己的判断。然后,我会尝试评估复杂的责任问题,从而远远超过了中国政府。
在本文结束时,您可能已经了解了关于病毒的分子生物学的很多。我会尽量保持这种过程尽可能无痛。但是,由于目前,而且可能长时间,它不能避免科学,它提供了迷宫的唯一肯定。
导致大流行的病毒是正式已知的,作为SARS-COV-2,但可以致短缺。正如许多人所知道的,它的起源有两个主要的理论。一个是它自然地从野生动物到人们跳起来。另一种是病毒在实验室中进行了研究,从中逃脱。如果我们希望防止第二个这样的事件,这是一个很大的事项。
我将描述这两个理论,解释了为什么每个都是合理的,然后询问它提供了更好地解释了可用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理论都没有直接证据。每个人都取决于一套合理的猜想,但到目前为止缺乏证据。所以我只有线索,而不是结论,提供。但那些线索在特定方向上指向。并推断出来的方向,我将在这个纠结的灾难中描绘一些股线。
两个理论的故事。大流行于2019年12月爆发后,中国当局报告说,在潮湿的市场中发生了许多案件 - 武汉销售野生动物的地方。这一提醒了2002年SARS1流行病的专家,其中蝙蝠病毒首先传播到雪橇,潮湿市场上销售的动物,以及向人们销售的动物。类似的蝙蝠病毒引起了第二个疫情,在2012年引起了称为MERS。这次中间宿主动物是骆驼。
病毒基因组的解码表明它属于称为β-冠状病毒的病毒性家庭,SARS1和MERS病毒也属于β-冠状病毒。这段关系支持了这样的想法,就像他们一样,它是一种自然病毒,该病毒已经通过另一个动物主持人从蝙蝠跳到了人们。潮湿的市场联系,与SARS1和MERS流行病相似的主要观点,很快被破坏:中国研究人员在武汉发现了早期的案件,没有链接潮湿市场。但这似乎不再有很大的进一步证据支持自然出现的迹象。
然而,武汉是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主导,是冠状病毒研究领先的研究中心。因此,SARS2病毒从实验室逃离的可能性无法排除。两个合理的原产地在桌子上。
从早期开始,通过两个科学群体的强大陈述,塑造了公众和媒体的感知,支持自然出现情景。这些陈述起初不一于批评,因为他们应该是。
“我们坚持强烈谴责阴谋理论,暗示Covid-19没有自然的原产地,”一群病毒学家和其他人在2020年2月19日在柳叶服写在柳叶刀上,因为任何人都非常肯定地走得太早发生了什么事。科学家们“绝大地得出结论,这种冠状病毒起源于野生动物,”他们说,举行了读者的集会呼吁,读者在战斗疾病的前线上站在中国同事。
违背了信作者的断言,病毒可能从实验室中逃脱的想法,而不是引人注谋。肯定需要探索,没有被拒绝。一个善良科学家的定义标志是他们去了巨大的痛苦,以区分他们所知道的以及他们不知道的东西。通过这个标准,柳叶诗信的签署国表现为贫困科学家:他们保证了他们不知道的公众,肯定是真的。
后来据一旦证明兰蔻信函被纽约欧洲欧洲欧洲常产联盟总裁彼得达斯扎克组织和起草。 Daszak的组织在武汉病毒学研究所进行了冠状病毒研究。如果SARS2病毒确实从他资助的研究中逃脱,那么Daszak将可能是令人艰难的。这种急性利益冲突没有宣布给柳叶赛人的读者。相反,这封信得出结论,“我们宣布没有竞争利益。”
像Daszak这样的病毒学家在分配大流行的指责中有很多股权。 20年来,主要是在公众的关注之下,他们一直在玩危险游戏。在他们的实验室中,他们经常创造了比本质上存在的病毒更危险。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安全地这样做,而且通过超越自然,他们可以预测和预防自然的“溢出,”动物宿主对人的交叉病毒。如果SARS2确实从这样的实验室实验中逃脱,可以预期野蛮的反吹,并且公众愤怒的风暴会影响来自中国的病毒学家。 “它将将科学大厦粉碎至底,”Antonio Regalado Mit Mit Technology Revice Editor在2020年3月表示。
第二份声明,对塑造公众态度有巨大影响的是在2020年3月17日在自然医学期刊上发表的一封信(换句话说,而不是科学文章)。其作者是由克里斯蒂安G.安德森的克里希斯研究所的一组病毒学家。 “我们的分析清楚地表明,SARS-COV-2不是实验室构建或有目的地操纵病毒,”在其信的第二段中宣布的五位病毒学家。
不幸的是,这是另一个糟糕的科学,在上面定义的意义上。真实的,一些较旧的切割和粘贴病毒基因组的方法保留了讲述的操纵迹象。但是更新的方法,称为“无见”或“无缝”方法,留下没有定义标记。也没有其他方法来操纵序列通道等病毒,从一种细胞的一种培养物到另一个细胞培养物重复转移。如果已经操纵了病毒,无论是无缝方法还是通过串行通道,都无法知道这是这种情况。安德森和他的同事们向他们的读者保证他们无法知道的东西。
他们的信的讨论部分开始,“SARS-COV-2无法通过实验室操纵相关的SARS-COV样冠状病毒。”但等等,没有领导者说病毒已经清楚没有被操纵?当作者的确定性似乎在铺设推理时似乎滑倒了几个凹口。
一旦技术语言被渗透,滑动的原因就是明确的。作者给予操作的两个原因是要不可能实现的理论不确定。
首先,他们说SARS2的尖峰蛋白与其靶,人ACE2受体的刺激性相结合,而是以不同的方式从其所表达的物理计算将是最合适的。因此,病毒必须通过自然选择而产生,而不是操纵。
如果这个论点似乎很难掌握,这是因为它是如此紧张。作者的基本假设并没有拼写出来,是任何试图使蝙蝠病毒与人类细胞的蝙蝠病毒有可能以一种方式这样做。首先,它们将计算人ACE2受体和尖峰蛋白质之间的最强劲的拟合,病毒锁定在其上。然后,它们将相应地设计尖峰蛋白质(通过选择构成其的右氨酸单元)。由于SARS2穗蛋白不是这种计算的最佳设计,因此Andersen纸张所说,因此它不能被操纵。
但这忽略了恶作剧者实际上使尖刺蛋白结合到所选靶标,这不是通过计算而不是从其他病毒或通过连续通过剪接刺激蛋白质基因。通过连续通道,每次病毒的后代转移到新细胞培养物或动物时,选择更成功的是,直到出现对人体细胞真正紧绷的。自然选择已经完成了所有繁重的举重。 Andersen纸张关于通过计算设计病毒刺蛋白的猜测没有轴承对其他两种方法中的一种进行操纵。
作者对操纵的第二个争论更为重要。虽然大多数生物使用DNA作为其遗传物质,但许多病毒使用RNA,DNA的亲密化学表表。但RNA难以操纵,因此研究冠状病毒的研究人员是基于RNA的,首先将RNA基因组转化为DNA。它们操纵DNA版本,无论是通过添加还是改变基因,然后安排被操纵的DNA基因组被转化为传染性RNA。
在科学文献中仅描述了一定数量的这些DNA骨架。操纵SARS2病毒的人“可能”已经使用了其中一个已知的骨干,并且由于SARS2不是从其中任何一个衍生的,因此它没有被操纵。但论点明显不确定。 DNA骨架很容易制作,因此明显可能使用未发表的DNA骨架操纵SARS2。
就是这样。这些是Andersen集团支持他们的宣言,即SARS2病毒清楚地没有操纵的两个论点。而这一结论,除了两个不确定的投机中,都没有接地,相信世界的媒体,SARS2无法从实验室中逃脱。 Andersen信的技术批评将其置于Harsher的话语中。
科学据说是一个自我纠正的专家社区,他们不断检查彼此的工作。那么为什么其他病毒学家不指出安德森集团的论点充满了荒谬的大洞?也许是因为在今天的大学中,演讲可以非常昂贵。职业可以被摧毁,以踩出线。任何挑战社区宣布的病毒学家的病毒学家都宣布具有他的下一个拨款申请的风险,由他的病毒学家小组拒绝,该小组向政府授予分发机构提供建议。
Daszak和Andersen的信件是真正的政治,而不是科学的,陈述,但却是惊人的。主流媒体中的文章一再表示,专家的共识已经统治了实验室逃脱了问题或极其不太可能。他们的作者依赖于Daszak和Andersen信件的大部分依赖,未能了解他们的论据中的打呵欠差距。主流报纸全部对其员工有科学记者,正如主要网络,这些专家记者都应该能够质疑科学家并检查他们的断言。但Daszak和Andersen断言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冒险。
对自然出现的疑虑。自然出现是媒体的首选理论,直到2021年2月左右,并由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委员会访问中国。委员会的成分和访问受到中国当局的严重控制。它的成员包括普遍存在的Daszak,在访问之前,在他们的访问之前,在他们的访问之前保持着声称,实验室逃生是极不可能的。但这不是宣传中国当局可能希望的宣传胜利。明确的是,中国人没有证据表明委员会提供支持自然出现理论。
这令人惊讶,因为SARS1和MERS病毒都在环境中留下了大量痕迹。 SARS1中间体宿主物种在流行病爆发的四个月内确定,九个月内的MERS宿主。然而,在SARS2大流行开始之后的约15个月,经过一定可能的重症搜索,中国研究人员未能找到原来的蝙蝠人口,或者SARS2可能已经跳过的中间物种,或任何中国人口的血清学证据,包括武汉的那些在2019年12月之前暴露于病毒。自然的出现仍然是一个猜想,然而符合众所律,无论是从一年内都有一个支持证据的人才能获得。
只要剩下的情况,它就会认真关注替代猜想是逻辑,即SARS2从实验室逃脱。
为什么有人想创造一种能够引起大流行的新型病毒?自从病毒学家获得了操纵病毒基因的工具,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探索给定的动物病毒可能是为了使人类跳跃的近距离而领先潜在的大流行。病毒剂们被证实,在提高危险的动物病毒感染人们感染者的能力方面进行了证明的实验室实验。
通过这一理由,他们重新创建了1918年的流感病毒,显示了几乎灭绝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如何从其发表的DNA序列合成,并将SmallPox基因引入相关病毒。
病毒能力的这些增强性是充满活力的作为功能性实验。用冠状病毒,穗蛋白特别感兴趣,尖峰蛋白质围绕病毒的球形表面,几乎确定它将靶向哪些动物。例如,在2000年,荷兰研究人员通过遗传工程鼠标冠状病毒的尖峰蛋白来赢得啮齿动物的感恩,以便只攻击猫。
恶作剧学家开始认真研究蝙蝠冠状病毒,因为这些原因是SARS1和MERS流行病的来源。特别是,研究人员希望了解在蝙蝠病毒在感染者之前所需的发生变化。
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由中国领先的蝙蝠病毒专家领导,施正李或“蝙蝠夫人”,在中国南方云南的蝙蝠感染洞穴中常用的探险,并收集了一百不同的蝙蝠冠状虫病。
然后,Shi与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一个知名冠状病毒研究员联合了Ralph S.律师。他们的作品专注于提高蝙蝠病毒攻击人类的能力,以“检查出苗潜力(即潜在的感染人类)的循环蝙蝠COV [冠状病毒]。”在追求这一目标,2015年11月,他们通过占据SARS1病毒的骨干并用一个来自蝙蝠病毒(称为SHC014-COV)的尖刺蛋白来制造一种新的病毒。这种制造的病毒能够感染人气道的细胞,至少当测试这种细胞的实验室培养物时。
SHC014-COV / SARS1病毒被称为嵌合体,因为其基因组含有来自两个病毒株的遗传物质。如果SARS2病毒在SHI的实验室里煮熟,那么它的直接原型将是SHC014-COV / SARS1 Chimera,其潜在的危险有关许多观察者并提示激烈的讨论。
“如果病毒逃脱,没有人可以预测轨迹,”巴黎巴斯特研究所的病毒学家Simon Wain-Hobson说。
律师和施在论文中提到了明显的风险,但争论他们应该根据预示未来溢出率的效益来权衡。他们写的科学评论小组,“可能认为类似研究基于循环菌株越来越追求的循环菌株建设嵌合病毒。”鉴于职能获得的各种限制(GOF)研究,事项已达到了“GOF研究担忧的十字路口;必须权衡为未来爆发的准备和减轻未来爆发的可能性,以防止产生更危险的病原体的风险。在进行发展的政策方面,重要的是要考虑这些研究产生的数据的价值以及这些类型的嵌合病毒研究是否需要进一步调查与所涉及的固有风险进行进一步调查。“
该声明是在2015年制定的。从2021年的后视,可以说,在预防SARS2流行病中的职能研究的价值为零。如果实际上,风险是灾难性的,如果SARS2病毒在函数的实验中产生。
在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内。律师开发了,并教授Shi,是工程蝙蝠冠状病毒的一般方法来攻击其他物种。特定靶标是在培养物和人源化小鼠中生长的人体细胞。这些实验室小鼠,廉价和道德的人类受试者的脱务是遗传设计的,以携带称为ACE2的人类蛋白质,该蛋白质剥去线路的细胞表面。
Shi在武汉病毒学研究所返回了她的实验室,并恢复了她在遗传工程冠状病毒攻击人类细胞的工作中的工作。我们怎样可以如此确定?
因为,在故事中的一个奇怪的扭曲,她的工作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AID)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资助。并提供资助她的工作的提案,这是一个公共录制的问题,指定了她计划与金钱做的事情。
赠款被分配给eCohealth联盟的德斯扎克,他们将他们分包给施。以下是2018年和2019财年的补助金。(“COV”代表冠状病毒,“S蛋白质”是指病毒的穗蛋白质。)
“COV地区差异的测试预测。宿主范围的预测模型(即出苗电位)将在通过逆向遗传,假瘤病毒和受体结合测定和来自不同物种和人源化小鼠的一系列细胞培养物的病毒感染实验进行测试。“
“我们将使用蛋白质序列数据,传染性克隆技术,体外和体内感染实验和受体结合的分析,以测试S蛋白质序列中%发散阈值预测溢出潜力的假设。”
这意味着以非技术语言,是施列出了为人类细胞的最高可能感染性创造新的冠状虫。她的计划是服用编码为人类细胞具有各种测量的多样性的钉蛋白的基因,从高到低。她会逐一将这些穗基因逐一插入许多病毒基因组(“反向遗传学”和“传染性克隆技术”)中,产生一系列嵌合病毒。然后将这些嵌合病毒进行测试以攻击人细胞培养物(“体外”)和人源化小鼠(“体内”)的能力。这些信息有助于预测“溢出”的可能性,从蝙蝠到人们的冠状病毒的跳跃。
该方法方法旨在寻找冠状病毒骨干和穗蛋白的最佳组合,用于感染人体细胞。该方法可以产生SARS2样病毒,并且实际上可能已经用病毒骨架和尖峰蛋白的右组合产生SARS2病毒本身。
尚不讨论施史或没有在她的实验室中生成SARS2,因为她的记录已被密封,但似乎她肯定是在正确的轨道上所做的那样。 “很明显,武汉病毒学研究所正在系统地构建新的嵌合冠状虫病毒,并评估其感染人细胞和人类表达的小鼠的能力,”分子生物学家理查德H.埃布里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