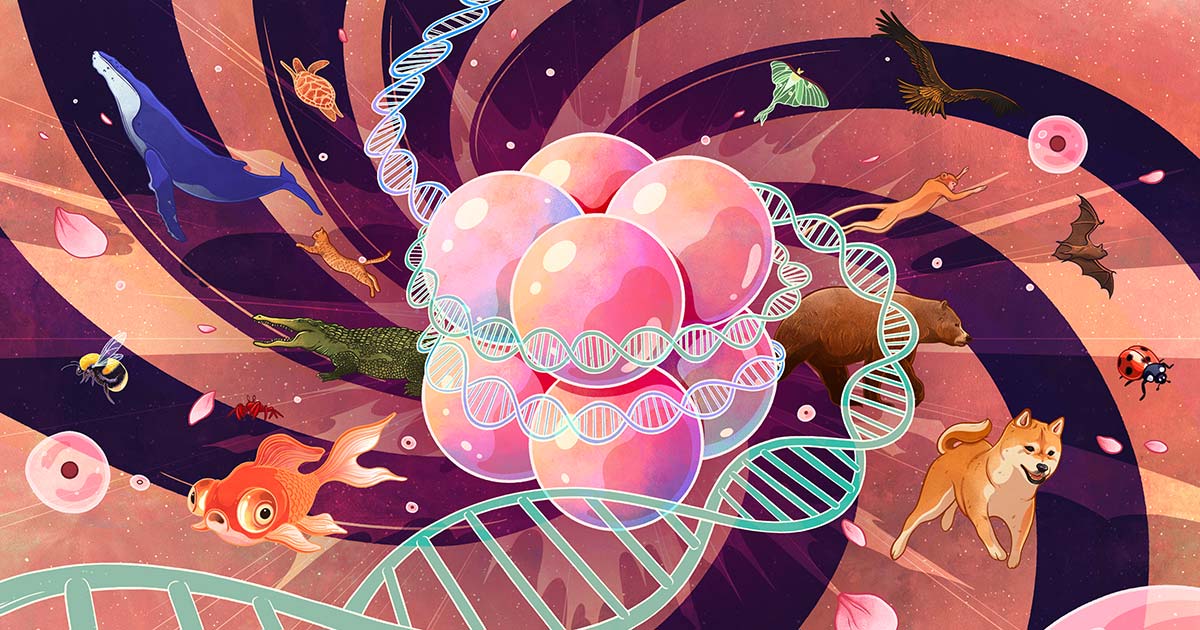DNA组蛋白线轴提示复杂的细胞演变
但早期的真核生物通过严重的生长痛苦,因为他们的基因组扩张:较大的基因组带来了源于管理越来越笨拙的DNA串的必要性。该细胞的机械必须可访问DNA,用于在无望的意大利面球中纠缠在一起而转录和复制它。
DNA也有时需要紧凑,无论是有助于调节转录和调节,并在细胞分裂期间分离DNA的相同副本。如果一个人的骨干与另一个凹槽相互作用,则DNA股可以不可逆转地绑定DNA股的一个危险。
细菌具有溶液,涉及各种蛋白质,共同“超级卷轴”细胞的DNA的相对有限的文库。但是真核生物的DNA管理解决方案是使用组蛋白蛋白,这具有独特的能力,可以将DNA周围包裹在一起,而不是粘在其上。真核生物的四个主要组蛋白 - H2A,H2B,H3和H4 - 组装成具有每个副拷贝的八寡。这些八羟种子称为核心,是真核DNA包装的基本单元。
通过弯曲核小体周围的DNA,组蛋白可以防止其团聚在一起并保持其功能。这是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 - 但是真核生物并没有完全发明它。
在20世纪80年代,当蜂窝和分子生物学家Kathleen Sandman是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的博士后,她和她的顾问,约翰雷夫,鉴定并排序了古代的第一个已知的组蛋。它们显示了四个主要真核组蛋白是如何彼此相关的和古代组蛋白。他们的工作提供了早期证据,在原始的内骨生物事件中导致真核生物,宿主可能是古代细胞。
但是认为古老的组织只是在等待真核生物的到来以及扩大他们的基因组的机会,这将是一个目的地错误。 “许多早期假设在他们允许细胞扩大其基因组的能力方面看了组蛋白。但这并没有真正告诉你为什么他们首先在那里,“加州大学洛杉矶大学的生物化学家Siavash Kurdistani说。
作为朝着这些答案的第一步,桑德曼几年前加入了力量,他在1997年解决了真核核小体的结构。在一起,他们制定了他们与同事发表的古核小瓶的结晶结构2017年,他们发现,在结构上的结构中,古代核肉是“不甲型相似”的结构,但是龙眼表达 - 尽管它们的肽序列具有显着的差异。
凯尔,现在已经“弄清楚了如何在这种美丽的弧中绑定和弯曲DNA,”霍尔多罗大学霍尔德大学霍华德休斯医学院调查员。但真核生物和古核肉之间的差异是古核心的晶体结构似乎形成了变化的不同尺寸的松动器,相同的组件。
在伊利诺伊州的卢尔,卢瓦尔,她的学生塞缪尔Bowerman和伊利诺伊州理工学院的杰夫Wereszczynski举行的一篇文章中。它们使用了低温电子显微镜,以在更代表活细胞的状态下解决古核小体的结构。他们的观察结果证实,古核肉的结构较小。真核核肉总是稳定地包裹约147个碱基对DNA,并始终由八个组蛋白组成。 (对于真核核肉,“降压在八个停止,”Luger说。)在古亚亚群中的等同物在60和600碱基对之间。这些“archaeasomes”有时持续少于三个组蛋白二聚体,但最大的一个是多达15个二聚体。
他们还发现,与紧密的真核核肉不同,像蛤壳一样平坦的古南溃烂的斑块。研究人员表明,这种安排简化了古痤疮的基因表达,因为与真核生物不同,它们不需要任何能量昂贵的补充蛋白,以帮助从组蛋白中解放DNA以使它们可用于转录。
这就是为什么托比亚斯科克在伦敦帝国学院研究古群众群岛,认为“有些特殊的东西必须发生在真核生物的曙光中,在那里我们从只有简单的组蛋白......具有八大核素。他们似乎正在做一些定性不同的事情。“
然而,这仍然是一个谜。在古代物种中,有“有些有组蛋白的物种,还有其他物种没有组蛋白。 “甚至那些那些已经有了组蛋白的人也很有变化,”Warnecke说。去年12月,他发表了一篇论文,表明具有不同功能的组蛋白蛋白质的不同变体。组蛋白-DNA复合物在它们对DNA的稳定性和亲和力的稳定性和亲和力方面变化。但它们并不像真核核肉一样稳定或定期组织。
作为古代组蛋白的多样性的令人费解,它提供了理解基因表达系统的不同方式的机会。 Warnecke说:通过了解archaeal系统的组合学,“我们也可以弄清楚真核系统的特殊性,这是我们无法从真核的相对”厌恶“。”各种不同的组蛋白类型和古代配置的配置也可能有助于我们推断出在基因调节中的作用之前可能做的事情。
因为古代是具有小型基因组的代理相对简单,“我不认为组蛋白的原始作用是控制基因表达,或者至少以我们用于从真核生物的方式进行控制,”Warnecke说。相反,他假设组蛋白可能会保护来自损伤的基因组。
Archaea经常生活在极端环境中,如海底的温泉和火山通风口,其特点是高温,高压,高盐度,高酸度或其他威胁。用组蛋白稳定他们的DNA可能使DNA链更难以在那些极端条件下融化。组蛋白也可能保护archaea反对入侵者,例如噬菌体或转移元素,这会发现它在缠绕在蛋白质周围时难以进入基因组。
Kurdistani同意了。 “如果你在20亿年前学习古代,那么基因组压实和基因调节不是当你在考虑组蛋白时想到的第一件事,”他说。事实上,他暂时推测了组蛋白可能提供古代的不同种类的化学保护。
去年7月,Kurdistani的团队报告说,在酵母核肉中,在两个组蛋白H3蛋白的界面中存在催化位点,其可以结合和电化学减少铜。为了解开这种进化意义,Kurdistani返回地球上的氧气大规模增加,巨大的氧化事件,发生在大约20亿多年前的时间左右。较高的氧气水平必须引起铜和铁等全球金属氧化,这对生物化学至关重要(虽然过量有毒)。一旦氧化,金属将变得越大少于细胞,因此将金属以减少形式保留的任何细胞都具有优势。
Kurdistani说,在巨大氧化事件中,减少铜的能力将是“非常有价值的商品”。它可能对线粒体的先驱的细菌可能是特别有吸引力的,因为细胞色素C氧化酶,在线粒体用于产生能量的反应链中的最后一种酶需要铜的功能。
由于Archaea生活在极端环境中,因此他们可能已经找到了在巨大氧化事件前长期杀死的方式产生和处理减少的铜。 Kurdistani建议,如果是这样,Propo-Mitochondria可能会侵犯古代主持人偷走他们的铜缩减。
假设是有趣的,因为它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氧气水平在大气中升起时出现了真核生物。 “在此之前有15亿多年的生命,没有真核生物的迹象,”库尔德塔尼说。 “所以氧气驱使我的形成第一个真核细胞的想法应该是任何试图提出为什么这些功能发展的假设的核心。”
Kurdistani的猜想也表明了为什么真核基因组变大的替代假设。组蛋白的铜还原活性仅发生在用DNA包裹的组装核小体内的两个H3组蛋白的界面处。 “我认为细胞想要更多的组蛋白是一种独特的可能性。而这是为了扩大这个DNA曲目的唯一方法,“Kurdistani说。随着更多DNA,细胞可以包裹更多的核体并使组蛋白能够减少更多的铜,这将支持更多的线粒体活性。 “不仅仅是允许更多的DNA,但更多的DNA允许更多的组蛋白,”他说。
“这是一个关于这一点的一件事是铜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会破坏DNA,”西雅图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的染色质生物学家和HHMI调查员斯蒂芬·亨基诺“这是一个你有一个活跃的铜所做的铜的地方,它在DNA旁边,但它不会破坏DNA,因为大概,这是一种紧密包装的形式,”他说。通过包裹DNA,核心将DNA安全地脱离。
假设潜在地解释了真核基因组的结构如何发展的方面,但它遇到了一些怀疑。关键的突出问题是古代组蛋白是否具有相同的铜减少能力,即一些真核生物的能力。 Kurdistani现在正在调查这一点。
底线是,我们仍然不明确地了解archaea中服务的功能。但即便如此,“你看到他们在长途跋涉的事实中强烈建议他们正在做一些明显和重要的事情,”Warnecke说。 “我们只需要了解它是什么。”
虽然复杂的真核组蛋白装置由于它的起源而言大约十亿年前没有变化,但它并没有完全冻结。 2018年,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的团队报告说,一组名为H2A.B的短组蛋白变体正在快速发展。变化的步伐是争夺监管资源的基因之间的“军备竞赛”的肯定迹象。最初没有对研究人员清楚的遗传冲突是关于的,而是通过小鼠的一系列优雅的杂交实验,他们最终表明H2A.B变体决定了胚胎的存活率和生长速度,如12月份所述Plos生物学。
研究结果表明,组蛋白变体的父母和母亲版本正在介绍怀孕期间如何将资源分配给后代的冲突。它们是父母效应基因的罕见例子 - 一种不会直接影响携带它们的个人,而是强烈影响个人的后代。
当UTERo Development的演变重写父母投资时,H2A.B变体与第一个哺乳动物产生。母亲们总是在他们的卵中投入了很多资源,但哺乳动物母亲突然突然对他们的后代的早期发展负责。建立冲突:胚胎中的父母基因因积极要求的资源而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而母体基因受益于抚养母亲的负担,让她活着养殖另一天。
“谈判仍在继续,”弗雷德·霍金森癌症研究中心的HHMI调查员艾鲁特马里克说,他研究遗传冲突。完全如何影响后代的生长和活力仍然没有完全理解,但达到工作的博士球菌和现在在法国克莱蒙·奥比涅大学领导自己的研究小组的博士莫拉罗正在调查它。
一些组蛋白变体也可能导致健康问题。 1月份,Molaro,Malik,Henikoff及其同事据报道,短的H2A组蛋白变体涉及一些癌症: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的一半以上的弥漫性。其他组蛋白变体与神经变性疾病有关。
但是尚未理解的是如何产生这种戏剧性疾病影响的单一拷贝。明显的假设是该变体影响核体的稳定性并破坏其信号传导功能,以改变细胞生理的方式改变基因表达。但是,如果组蛋白可以作为酶,那么Kurdistani表明另一种可能性:变体可以改变细胞内的酶活性。
尽管来自桑德曼的数十年的证据和其他人从古代组织种植的真核生物组蛋白,但最近的一些有趣的工作意外地将门敞开了大门,以替代的原因。据一本文发表于4月29日在自然结构& Marseilleviridae家族的分子生物学,Marseilleviridae家族的病毒性质具有可识别与四个主要真核特征有关的病毒组蛋白。唯一的区别在于,在病毒版本中,在真核生物中常规地对八寡(H2a的H2a和H3)内常规的组蛋白已经融合成双重。根据本文的作者,融合的病毒组蛋白形式的结构是“与规范真核核酸几乎相同”。
Luger的团队在同一天发布了关于病毒组蛋白的Biorxiv.org的预印刷品,表明在感染细胞的细胞质中,病毒组蛋白保持在产生新的病毒颗粒的“工厂”附近。
“这是真正引人注目的事情,”Henikoff说,在新的自然结构和amp上的作者中;分子生物学论文。 “所有组蛋白变体都从出来的祖先源自在真核生物和巨大病毒之间共享的共同祖先。通过标准的系统发育标准,这些是对真核生物的姐妹组。“
他说,它使这个普通的祖先来自真核生物组蛋白来的令人信服的案例。具有组蛋白双峰的“原核”可能是巨型病毒和真核生物的祖先,并且很久以前可以通过两种生物体来通过蛋白质。
然而,Warnecke对从病毒序列推断出从病毒序列的系统发育关系是令人疑问的,这是众所周知的变形的。正如他在电子邮件中解释的那样,共享祖先以外的原因可能会解释组蛋白在两个谱系中的结尾。此外,该思想将要求组蛋白双胞胎后来“未使用”进入H 2 G,H2B,H3和H4组蛋白,因为在拉伸真核生物中没有那些组蛋白的双重。 “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尚不清楚,”他写道。
虽然Warnecke并不相信病毒组蛋白告诉我们真核组蛋白的起源,但他对可能的功能令人着迷。 一种可能性是它们有助于紧致病毒DNA; 另一个想法是,他们可以从主持人的防御中伪造病毒性DNA。 由于时间的黎明以来,组蛋白已有多种角色。 但它真的在真核华中,他们成为复杂生活和无数进化创新的亚文。 这就是为什么马丁呼叫组成的“一个基本的建筑块,从未在没有线粒体的帮助下实现它的全部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