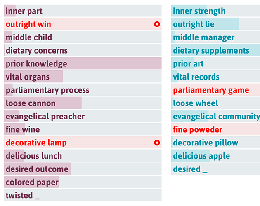我对更多游戏对待了我不健康的游戏痴迷
博彩在童年时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种族主义也是如此。有一天,我大约10岁的时候,我从学校回家,在我母亲面前泪流满面,同时告诉她我是如何被欺负的。她忽略了我,而不是向我提供支持或保证,而不是倾听我的微软心灵的比赛。
在90年代初,在英格兰的一个小市场镇上,我们的家庭是操场上唯一的颜色人,在工作和购物中心。我母亲在马来西亚的保守教养上没有准备好她在敌对环境中应对作为护士的要求,她遭受来自同事和医院患者的虐待。
相反,她挣扎着有挑战性的感情,特别是悲伤,并且当我告诉她我害怕散步时,我会被“愚蠢”。星期天对我来说特别糟糕,我总是挣扎睡觉,而楼下我可以听到母亲的噪音,因为她也推迟了未来一周的一周。
我们有电脑,因为我的父亲修复了他从工作中回家的286秒。与其他家庭不同,我们在家里有几台机器会玩游戏。这意味着我的母亲可以把她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盯着灰色的监视器,逃离了她所觉得自己的种族主义冲突和有毒压力的生活中的创伤。第二天,她总是回到电脑上,只停止吃一个微波的晚餐。
久后我在二十岁时离开家后,我变得沮丧,并在家庭模式之后,还经常开始转向我的电脑或游戏控制台寻求慰借。我会在我的卧室里度过整个周末演奏锦标赛经理。但我违反了这种行为链,而不是通过停止游戏,而是用它作为一种力量来使用它。这就是为什么我讨厌“游戏成瘾”一词,这就是多年来我可以成为一个游戏记者的方式。游戏可能是问题的一部分,但对我来说,他们也成为了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使得最大的差异是花,十多年前发布了。在它中,玩家可以通过空气来改变风的方向。游戏中没有任何设定目标或目标。就像我母亲的痴迷,更像是创造性的玩耍或玩耍的缘故,从我的单调童年中缺乏一些严重的东西。
拥抱游戏帮助我应对抑郁症,我相信是我和母亲在游戏中的潜在事业。这也是一位学习视频游戏的心理学家克里斯·弗格森等专家,首先考虑他们遇到可能有与游戏有不健康关系的人,完全不同意这是一个导致成瘾的游戏自己的想法。
“通常,游戏障碍的模式是心理健康问题首先是,”他说。
这也是为什么我和许多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困扰着世界卫生组织目前定义了一种游戏障碍,因为当一个人在博彩优先于其他利益方面提出了其他活动时,当一个人提出“其他活动的优先权增加时和日常活动,“当您可以用任何其他活动取代”游戏“时:购物,去健身房,检查您的电子邮件,甚至每晚订购摘要。”如果你使用相同,猫是令人上瘾的论点逻辑,“弗格森说。
“我是半笑话,但猫有让你订婚的机制。抚摸一只猫在大脑中释放多巴胺,就像其他一切都很有趣,“他继续。 “他们家里有70只猫的人,他们显然存在问题,但没有诊断'猫障碍。为什么谁和其他组织如此关注游戏,排除所有其他组织事情,人们可能会过度的?“
但是,如果我们继续争论,游戏可能不会直接成为成瘾风险,而是一个更广泛问题或其他潜在的心理健康问题的症状,那么你可以争论酒精和毒品吗?
“如果你要将海洛因秘密地融入某人的食物,”弗格森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造成成瘾,也许甚至没有注意到它直到为时已晚。有生理机制会导致成瘾。你得到了很多人沉迷于咖啡因并每天醒来,需要咖啡或百事可乐。他们可以在没有它的情况下' t功能并获得了宽容,因此他们需要越来越多的咖啡来获取踢球。如果他们试图停止,他们会得到头痛,疲劳,烦躁。当涉及容忍和退出的概念时,游戏中没有相同的游戏。“
听到了这一点,因为我已经使用游戏在我的生命中破坏上瘾模式。我有最大的问题正在检查我的手机供电子邮件。如果没有选中,可以导致屏幕在晚上,周末,或者当我应该在度假时。
请参阅这篇文章:一旦我发出球场,我就会关闭我的电脑并拿起我的Bittboy(一个复古手持式游戏机),在Super Nintendo上玩10分钟的俄罗斯攻击(我设置了一个计时器)。它用多巴胺“奖励”为我提供了我期待的直接电子邮件回复。这意味着我可以忘记电子邮件,然后恢复工作。但是我的小说习惯背后有什么科学吗?
“简单的回答是,是的,你可以绝对可以做游戏作为奖励,”弗格森说。
“这是一种复杂的情况,因为多巴胺做了很多东西,但你会在你做点令人兴奋之前看到多巴胺水平飙升。当你在迪士尼世界之后,当你在迪士尼世界后,当你在空间山前面的队列前面时。这可能是完全像从一个非常好的球场收到电子邮件一样。“
弗格森然后告诉我,当你第一次玩游戏时,多巴胺水平升高约50%至100%,这是对任何愉快活动的完全正常的反应:从吃披萨到性别(比较至甲基苯丙胺使用,这可能提高1,300%的水平)。相比之下,多巴胺 - 明智的是,玩游戏很好,之后你不会对披萨或(也许)从性别中吃同样的遗憾。
我担心游戏如何影响年轻的思想,因为我的4岁的女儿刚刚开始与我的iPad一起玩。我担心她可以与游戏的不健康关系,我所做的方式,以及她的祖母所做的方式。布里格姆大学家庭生活中学校副主任莎拉·科伊恩,亚光了我的恐惧。
“视频游戏的积极用法有这么多的研究,”她说。 “如何帮助社会关系和心理健康和认知问题。”
“视频游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你可以用它们来好或坏,”她继续。 “所以你想确保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真的为你而工作。如果你对孩子过于严格限制,那么他们反叛然后只想要限制内容和禁止的果树类型的想法。“
Coyne表示,在让父母滥用游戏作为一种爱好的父母的影响,我的母亲没有太多的研究,但我母亲扮演了不暴力的游戏。这是我倾向于的那种游戏,特别是益智游戏,提供了脑经验和解决问题的快乐。
“如果你正在演奏令人心旷的视频游戏,或者连接到你的视频游戏或帮助你思考世界的视频游戏,那将对大型盗窃汽车造成显着不同的影响,”Coyne说。
我对游戏和我的女儿的恐惧是考虑到我与我不和父母不同时的方式相连的令人沮丧。我的伴侣和我看不到游戏,作为我们从孩子们休息的方式。
“如果你有高父母的温暖,”Coyne补充道,“和与父母的良好关系,孩子们不太可能上瘾。监控游戏的父母不太可能有上瘾的孩子。“
我的早期生活可能是由一位母亲认为游戏作为抑郁症和世界其他地方避难所的母亲的标志,但我的世界被视频游戏丰富了。当我采访我喜欢的比赛的人时,我分享他们的孩子奇迹,介绍媒体如何可访问和生命变化。我玩冠军经理的日子似乎似乎浪费时间,但是当你沮丧时,他们会教我一个有价值的课程,了解在游戏中失去自己的危险。
现在,当我沮丧时,我和我爱和信任的人谈论它。我仍然拿起一个控制器,但通过认识到为什么我在开始游戏之前我不开心,我可以用我的爱好作为健康的撤退,而不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度假。
✨优化您的家庭生活与我们的齿轮队的最佳选择,从机器人真空到实惠的床垫到智能扬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