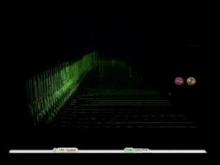大学应该保留精英管理的理念吗?
早在2月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公共话语项目就召集了一个关于高等教育精英管理的论坛。该活动由北卡罗来纳大学政治学家莎拉·特雷尔主持,“纽约时报”观点专栏作家罗斯·杜塞、人类学家凯特琳·扎卢姆、哲学家阿纳斯塔西娅·伯格和作家托马斯·查特顿·威廉姆斯都曾为“纪事评论”撰写过关于精英管理的文章。这三个人都曾为“纪事评论”撰写过关于精英教育的文章,其中包括“纽约时报”的观点专栏作家罗斯·杜塞、人类学家凯特琳·扎卢姆、哲学家阿纳斯塔西娅·伯格和作家托马斯·查特顿·威廉姆斯(Thomas Chatterton Williams)。
这场讨论发生在冠状病毒改变一切之前。但是这些话题--精英管理的定义,大学在公正社会中的作用,社会经济阶层的构成,以及教育的真正目的--一如既往地切合实际。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之后,当我们在思考如何看待我们的大学系统时,这场对话提供了一个紧迫而明智的指南。
莎拉·特雷尔:当我想到任人唯贤的理想,即社会和经济回报,而不是家庭地位,应该跟踪成就时,它与美国梦非常一致,努力工作,靠自己的自力更生。但在这里,除了托马斯,你们似乎都反对任人唯贤,这是美国文化中越来越受欢迎的观点。
凯特琳·扎卢姆:精英管理始于这样一种理念,即必须以人的价值的尺度来衡量人。因此,当我们决定精英教育是进入高等教育的途径,或者特别是通过高等教育进入政府时,这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参与是以在价值层次上取得成就的想法为前提的,而你可能首先同意也可能没有认同。
阿纳斯塔西娅·伯格:我不认为我反对任人唯贤。显然,社会中的某些角色和某些荣誉应该授予最有能力的人:诺贝尔奖,或者教学奖,或者应该给我们做眼科手术的人。
问题是,这是否是决定谁应该进入大学的正确标准。左翼和右翼都有反对意见。我觉得左边的那些很有说服力,也就是说,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看一下进入大学的人,就会发现所谓的精英制度并没有得到证实。我们发现,人们拥有的物质支持与他们在允许人们进入大学的考试中的表现之间存在巨大的相关性。
但我发现的问题也与以前被认为是保守派的批评有关,尽管我认为左翼人士、自由派和进步人士应该和其他人一样关注这一问题:目前的大学招生方式集中了极少数领域的人才、雄心和能力-在很少的几所大学-并从其他地方吸引了潜在的领导人。此外,目前的制度让人们对他们欠社区的所有方式都视而不见,因为他们得到了所有允许他们实现的帮助。
罗斯·杜塞:记住,精英统治这个词是在一本由一位英国公务员在50年代末写的名为“精英统治的崛起”的书中创造出来的,用来描述反乌托邦,这一点很有用。这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某个地方的一些浮夸的公务员的半开玩笑的召唤,回顾他认为的认知精英自我选择的行为,以统治一个人才枯竭、野心枯竭、精英之外的所有权力中心都被剥夺了领导力和内部才华的社会。
看一看美国和西方大部分地区的阶级分化,并说这种反乌托邦至少有一部分已经成为现实,这是合理的。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和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聚集在地理中心,这是五六十年前没有的。这种集中带来了经济和文化分层的混合,这与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骚乱都有关。你可以追溯到英国退欧的相似地理位置,以及法国对国民阵线的支持等等。
有两个问题笼罩着精英管理的辩论。首先,在我们的社会中,有没有方法可以成功地将权力下放或从下面获得权力,而不是依赖于证书制度?第二,我们有没有一种不同的教育,可以给我们的精英们提供更好的装备,让他们比过去20年左右统治西方世界的方式更好地治理西方世界?
托马斯·查特顿·威廉姆斯(Thomas Chatterton Williams):冒着成为这里最短视的分析师的风险,我不想抽象地谈论精英管理,而是从个人经验的角度来讨论。我父亲是一个来自实行种族隔离的南方的黑人,他的年龄真的足以当我的祖父了--他82岁,出生于1937年。他是家里第一个接受教育的人,而且他不是在精英社会长大的。他在美国长大,当他继续研究生教育时,美国人告诉他,黑人在德克萨斯州是不会被延期的。所以他是在每个白人学生都被推迟的时候被征召入伍的。在我看来,这不是任人唯贤。
但他带着一种移民的信念教育了我和我的兄弟,他们相信知识、努力和努力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唯一力量。我们攻击了一切在我们控制之下的东西。对我来说,这真的要归结为SAT考试,因为我甚至没有上过那种提供AP课程的高中。所以我的平均绩点不会反映出和那些要去预科学校的人一样的努力。但是有一个标准化的衡量标准我可以全力以赴,那就是SAT。在SAT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也给了我信心,让我相信我不会得到施舍,我可以在别人比我更有优势的地方表现得更好。我明白这是一种自私的看待问题的方式,但我得出的结论是,嘲笑允许人们晋升的精英措施需要一种特权。
崔尔:为什么与大学招生相关的精英管理会成为避雷针?
Zaloom:对于家庭来说,进入一所名牌大学感觉就像是他们可以给孩子一个机会的方式。但低收入人群在很大程度上被名牌大学拒之门外或望而却步-这是一个背景事实-现在,即使是对中产阶级来说,50%的中产阶级年轻人预计也会不如他们的父母做得好。我们正处于这种非常不平等和不稳定的情况,即使是对这些大学旨在支持的中产阶级来说也是如此。
崔尔:我们如何加强大学前的公共教育?我觉得我们在大学上投入了很多。
Zaloom:公共政策中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资金削减,特别是自2008年以来。因此,首先要做的是回到早期的水平:加强中间力量,不仅是在世界上的教堂山,而且在州级公立大学和社区学院也是如此。这将使这种登月计划变得不那么重要,这样年轻人就可以在离家很近的地方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不会感觉到事关生死、成败的精英评估。
伯格:在这个国家的150所顶尖学院和大学里,到处都是令人惊叹的、资历过高的教师。我去了哈佛,我不记得我在大学里学过的任何东西。哈佛与众不同的不是班级,也不是老师,也不是图书馆,也不是阅读清单。真正让我在哈佛的经历与众不同的是我的同事或同龄人。
我的经验是看到许多人的才华完全被孤立所浪费:道德孤立、地理孤立、文化孤立。即使是那些开始从事有趣职业的人,也很难去开发应用程序或赚更多的钱。
杜塞:这就是哈佛正在做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是人脉的凝聚,人们可以接触到彼此的想法和家庭关系,以及其他所有东西。这就是哈佛在制度上所致力于的,这就是常春藤联盟如何在20世纪60年代从为在东北部拥有特殊权力的特定精英、在美国外交政策和华尔街上完成学业的转变,但这还不是全国性的,更不用说国际精英了。所以常春藤联盟基本上说,好了,WASP的时代结束了,我们要自杀WASP-这是一件非常有尊严的事情,涉及到船鞋和欧洲-我们将派出一支国际精英队伍。我们要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是成为一个网络中心,不试图教授任何特定的量。
没有哈佛的课程。那里有很棒的教授和很棒的课程,上帝保佑你,你可以自己拼凑起来。但这并不是学校成立的目的。精英管理的部分问题是,它成为说你不需要传授某些特定思想的正当理由,因为我们只是在挑选最好的学生-我们不是在建设精英或其他什么。与此同时,他们完全是在打造一支精英队伍!
这与平权行动的动力相同。如果哈佛是一所精英形成的机构,那么我们希望班上学生的百分比反映美国的种族构成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你不能一边用嘴说,一边说,哦,我们的机会差不多相等。这是任人唯贤生活中的一种永久性紧张。
1998年至2002年,当我还在上学的时候,我的感觉是,这个体系正处于萌芽状态--人们相信精英管理。我父母这一代人从精英制度中受益匪浅,并对这一制度抱有非常坚定的信念。从那以后,我的感觉是,任人唯贤的那种无情的内在逻辑已经成为一种吞噬力量,许多中上阶层的白人都想要退出。
他们特别想退出,因为突然之间,他们的竞争对手大多是亚洲移民。所以你有这种奇怪的中上阶层白人的动态,他们突然想,好吧,也许我们应该取消SAT!你必须研究整个学生!
我不确定是否应该表示同情。一方面,我认为精英政治的内在逻辑在某些方面是邪恶和可怕的。这是一种野心主义,令人毛骨悚然。与此同时,如果另一种选择是中上阶层的白人拉起梯子,让移民奋斗者无法进入常春藤盟校,我不确定这是否一定是一种进步。
崔尔:我想你的很多作品都提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我们过分强调分数、平均绩点(GPA)这一大学毕业后的高权力职业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失去了公民责任感。我们怎么才能把它带回来呢?
威廉姆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生活是为了什么?任人唯贤是为了什么?这不可能是所有这些巨大的情感、财务和学术投资都用于创建下一个毫无意义的应用程序。
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平等?人类如何才能平等呢?我们平等吗?如果我们不能弄清楚平等,弄清楚平等和公平之间的区别,我不确定你们能不能就精英制度进行决定性的对话。想清楚如何在这个不平等的特殊时代遏制一些这种情况。任人唯贤只是反映了我们的不平等的很大一部分--而且不仅仅是社会内部的不平等。在一个四口之家,成员的能力并不平等。你怎么能假装纽约市可以一视同仁呢?
崔尔:也许我们不应该那么关心平等和结果。也许更多的是机会。
Zaloom:专注于精英大学的问题之一是,我们将大学的一个使命置于另一个使命之上,那就是,我们如何培养公民?这就是大学从一开始就致力于的:不仅在哈佛或北卡罗来纳大学或其他地方培养精英,而且实际上培养公民和公民技能,让毕业生能够回到他们的社区,领导和参与。围绕精英管理的讨论把我们从大学公民使命的讨论中拉了出来。
威廉姆斯:我确实认为我们一直在进行错误的对话。上哈佛很酷,但这不是人权,你知道吗?我哥哥反抗我父亲试图让我们渡过难关的那种精英制度。他会从德国这样一个重视职业培训的社会中受益,在那里你可以有一条通往高薪、有尊严的职业的道路,而不需要你假装想坐在那里学习伟大的书籍,而你并不是这样做的。
伯格:如果大学能让他们成为公民,那就太好了。但是,人们现在相当自豪的数字是,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上过大学,这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我是说如果这是唯一能让公民…。。
伯格:就算只做了一半也行。那就剩下另一半了。如果这就是让他们成为公民的方式,我们该怎么处理剩下的呢?我们必须为其他道路的尊严腾出空间。
扎卢姆:我不认为大学能独家做到这一点,但他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地方之一。
伯格:当我们谈论公民责任时,有一些抽象的理想可以教给我们的学生,但公民责任的一部分是感觉你和一个与你截然不同的人有一些共同之处。而这是哈佛永远不会给你的。你再也不会回头了。我认为真正认识与你不同的人对于培养公民责任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不是我们可以在课堂上简单地做的事情。
扎卢姆:但这是在课堂上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在我们的公立学院和大学里。我毕业于加州大学,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能像加州大学的九所学校那样,让那些认为他们不会最终在一起的人混在一起。课堂是传授公民身份的地方,因为我们走进教室,跨越差异-这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的大学系统在最好的时候所做的事情。
杜塞:公民身份就是民主参与。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精英义务--给予的人越多,要求的就越多。这两个模糊在一起,但它们并不完全相同。一些专门针对精英教育的争论是关于第二个的。我认为你可以在校园里看到一些被描述为社会正义斗士的激进主义,部分原因是对你所描述的动态的回应。人们感觉自己置身于一个关于精英、自我交易和自我利益的世界,从不与精英以外的人接触。人们对宗教或服兵役之类的东西有一种渴望,这类事情我们会把它们与年长的精英联系在一起。
你可以将校园里的左翼骚动部分视为重新说教的愿望。可以说,你是精英,这些是你的义务--你需要仔细审视自己的特权。我对那些演讲最终结束的一些地方有相当强烈的异议,包括有一天可能会把我排除在校园演讲之外的地方,但我认为这种冲动是合理的。
这并没有解决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为什么精英们都去了硅谷或华尔街。他们确实去了华盛顿,只是不是本着服务的精神。有一种感觉是,美国的机会存在于哈佛、硅谷、华盛顿特区和华尔街的纠葛中。这就是今天美国的机会。哪些权力中心没有连接到那个世界?工会?不,他们走了。宗教?不,它在下降。地区精英和权力掮客?不,他们不再重要了。这一动态不能用精英体制内部的话语来解决。它必须通过政治行动来解决,让那些背叛他们阶级的人参与进来。它也必须来自下面。
阿纳斯塔西娅·伯格(Anastasia Berg)是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哲学初级研究员。罗斯·杜塔特是“纽约时报”的观点专栏作家。托马斯·查特顿·威廉姆斯(Thomas Chatterton Williams)是“纽约时报”杂志的特约撰稿人。萨拉·特雷尔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政治学副教授。凯特琳·扎卢姆(Caitlin Zaloom)是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社会和文化分析副教授。
对这篇文章有什么疑问或担忧?给我们发电子邮件,或向编辑提交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