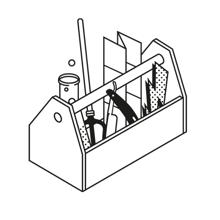流行病学家:瑞典的冷酷反应不是™t非正统的,世界其他地方是
瑞典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做法继续招致密切关注,既有赞扬,也有批评。
批评者和支持者都同意的一件事是,瑞典的“较轻的接触”方法,通过更温和的措施来鼓励社会疏远,而不是大规模关闭,是非正统的或例外的。
正如瑞典顶级传染病专家最近解释的那样,瑞典应对大流行的方法比目前的封锁方法更正统,至少与历史标准相比是这样的。
“人们完全封闭社会,这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吗?这或多或少比瑞典更正统吗?”安德斯·泰内尔(Anders Tegnell)最近问道。“(瑞典正在做)我们在公共卫生方面通常做的事情:赋予民众很大的责任,努力实现与民众的良好对话,并取得良好的结果。”
泰内尔的观点值得关注。虽然今天的国家似乎乐于实施大规模封锁,以防止致命呼吸道病毒的传播,但这种做法似乎是史无前例的。
历史表明,隔离病人是一种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做法。第一个有记录的做法似乎来自“旧约”,它在一些经文中规定了麻风病患者的隔离,如数字5:2-3。
隔离被怀疑为致命疾病携带者的人也有历史上的先例。根据FiveThirtyEight的说法,这种做法似乎可以追溯到14世纪,当时克罗地亚城市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开始对城外的商人和其他旅行者进行为期30天的隔离,以防他们在旅行期间感染鼠疫。
历史表明,特内尔是正确的:各国命令数百万健康人连续数周处于隔离状态的做法似乎是没有先例的-直到中国下令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规模隔离。
这很重要,有几个原因。首先,因为我们处于未知水域,我们无法知道这样的隔离会有多有效。在实验之前,卫生政策专家对这一战略表示怀疑。
东北大学法学院卫生政策和法律中心主任温迪·帕尔梅特(Wendy Parmet)在2月份告诉FiveThirtyEight:“有理由怀疑隔离的效果,特别是对呼吸道疾病(如冠状病毒)。”
其次,我们无法知道大规模停摆的代价-尽管我们开始看到它们:大规模失业,数十万企业倒闭,退休人员被消灭,政府支出激增,以及普遍的情绪困扰。
如果目前应对COVID大流行的方法是史无前例的,那就会引发问题。尤其是,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这次呢?
毕竟,美国从来不缺少致命的流行病。从1793年费城的黄热病(当时的美国首都)到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再到1957年至1958年的亚洲流感大流行,美国人一直在与在许多情况下比新冠肺炎更致命的疾病作斗争。
事实上,据“纽约时报”报道,就在2006年,当全世界都在与快速变异的禽流感作斗争时,封锁被认为“不切实际、没有必要、政治上也不可行”。
当时该政策的主要批评者之一是D.A.亨德森博士,他领导了根除天花的国际努力。
“亨德森博士确信,强迫学校停课或停止公众集会是没有意义的。青少年会逃离他们的家,去商场闲逛,“泰晤士报报道。“学校午餐计划将关闭,贫困儿童将吃不饱饭。如果他们的孩子在家,医院的工作人员会很难去上班。“
亨德森在2006年的一篇学术论文中写道,州强制的社会疏远将“导致社区社会功能的严重混乱,并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问题”。亨德森在回应一项联邦社会疏远提议时写道,该提议源于一个14岁女孩的科学项目和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去图书馆的一次旅行。
亨德森于2016年去世,他提出了一条不同的路线:让大流行顺其自然,治疗和隔离病人,并迅速开发疫苗。
看起来,乌托邦主义和集体主义是危险的思想混合体。这一提法让知识分子对中央计划的有效性产生了过大的信心。
亨德森在治疗病人的同时听其自然的做法根本不为专家和官僚所接受,他们很早以前就得出结论,认为中央计划可以解决任何问题,甚至是数百万无症状人类携带的高传染性、看不见的病毒的传播。
伟大的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在他的经典著作“从黎明到颓废”中写道:“现代应该是计划和建议之一,也就是说,未来主义到了偏执的地步。”
正如安德斯·泰内尔(Anders Tegnell)所说,封锁并不是真正基于科学。更准确地说,封锁是基于意识形态。甚至可以说是信仰。
正是这种信念导致世界上数十个国家的政府实施了封锁,这些封锁对遏制新冠肺炎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却造成了大规模的经济和心理破坏。
如果中央计划是新的正统-一个词被定义为“坚持正确或被接受的信仰,特别是在宗教上”-瑞典应该佩戴它的“非正统”标签作为荣誉的徽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