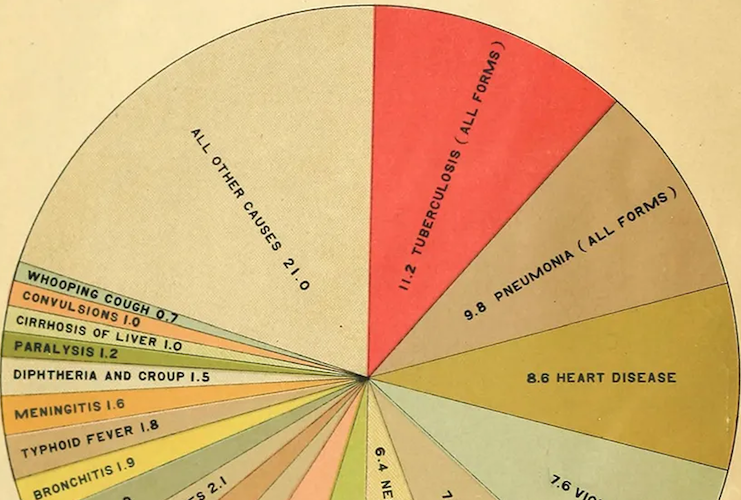流行病结束:历史告诉我们,疾病的结局往往是模糊不清的。
与新冠肺炎大流行有一个整洁的结局的希望相反,历史表明,传染病的爆发往往会产生更模糊的结果-包括被简单地遗忘,或者被当作别人的问题而不屑一顾。
近代史告诉我们很多关于流行病如何展开、疫情如何传播以及如何控制的信息。我们也很了解开始-广东的第一批肺炎病例标志着2002-03年的SARS爆发,韦拉克鲁斯最早的流感病例导致了2009-10年的H1N1流感大流行,几内亚的出血热爆发引发了2014-16年的埃博拉大流行。但这些行动不断增加和戏剧性结局的故事,只能让我们到目前为止才能接受全球危机。断了全世界的病例侦破和监视的缰绳,并浸透了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为了理解这场流行病可能的结局,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其他地方,而不是开始和结束的整齐模式--并重新考虑我们所说的“结束”流行病的开始是什么意思。
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对流行病着迷,部分原因是,即使在细节上不同,他们也表现出一种典型的社会编排模式,可以跨越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辨认出来。尽管6世纪查士丁尼瘟疫、14世纪黑死病和20世纪早期满洲鼠疫的生物病原体几乎可以肯定是不相同的,但流行病本身有共同的特征,将历史行为者与现在的经验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历史学家查尔斯·罗森伯格(Charles Rosenberg)认为,“流行病有一种戏剧性的形式。流行病在某个时刻开始,在空间和持续时间有限的舞台上进行,遵循一条日益紧张和具有启发性的情节线,走向个人和集体性质的危机,然后走向闭幕。“。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疾病都如此整齐地符合这种类型学结构。罗森博格在1992年,也就是北美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近十年后写下了这些话。关于这种疾病的起源,他的话听起来是真的--部分归功于对其“零号患者”的不懈、过分热衷的追求--但并不是关于它的终结,就像新冠肺炎一样,它的终结遥遥无期。
在新冠状病毒的案例中,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最初对起源的固执让位于结局的问题。三月份,大西洋月刊提供了四个可能的“生命恢复正常的时间表”,所有这些都取决于足够数量的发展免疫力的人口(可能是60%到80%)的生物学基础,以遏制进一步的传播。这一自信的断言源于一个世纪前由流行病学家W.H.弗罗斯特等人正式建立的传染病爆发模型。如果世界可以定义为对某种疾病易感(S)、受感染(I)和抗药性(R)的人,并且病原体有一个繁殖数R0(发音为R-0),描述了有多少易感人群可以被单个感染者感染,那么当易感人群的比例降到倒数1/R0以下时,流行病就开始结束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平均而言,一个人感染这种疾病的人比另一个人少。
这些公式让我们放心,也许是欺骗性的。他们召唤出一套自然规律,使灾难的节奏变得有条不紊。模型所产生的曲线,在较好的时期属于流行病学家的奥秘,现在却是数十亿人生活中的常见数字,人们学习如何生活在公民社会的收缩中,这些收缩是以“弯曲”、“扁平”或“挤压”的名义推动的。与此同时,正如大卫·琼斯(David Jones)和斯特凡·海姆里奇(Stefan Helmreich)最近在这些页面上所写的那样,这些曲线的平滑线条与流行病日常经历的参差不齐的现实相去甚远-包括那些建模人员曾预测会继续下降的“重新开放”州的急剧上升。
换句话说,流行病不仅仅是生物现象。从头到尾,我们对它们的社会反应不可避免地框定和塑造了它们(无论这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可能意味着什么)。现在,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临床医生、市长、州长、总理和总统们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这种流行病的生物现象什么时候能解决?”而是“冠状病毒的名义对我们的社会生活造成的破坏,何时才能结束?”随着疫情高峰期的临近,而且在许多地方似乎已经过去,来自政治光谱两端的民选官员和智库将提供“路线图”和“框架”,说明这场以至少一个世纪以来全球都没有见过的方式关闭了经济、公民和社会生活的流行病最终可能会消退,并允许恢复“新常态”。
流行病的这两个面孔,生物体
历史提醒我们,生物性和社会性流行病发生的时间之间的相互联系远不明显。在某些情况下,如18世纪的黄热病流行和19世纪的霍乱流行,这种疾病本身的戏剧性症状本身可以使其时间很容易追踪。就像一袋爆米花在微波炉里爆裂一样,可见病例事件的节奏开始缓慢,升级到疯狂的顶峰,然后逐渐消退,留下越来越少的新病例,这些病例最终间隔得足够远,足以被遏制,然后被消除。然而,在其他例子中,如20世纪的脊髓灰质炎流行,疾病过程本身是隐藏的,通常表现温和,有复发的危险,并且不是在一天内结束,而是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以不同的方式针对不同的人。
对抗传染病的运动经常用军事术语来讨论,这个比喻的一个结果是表明流行病也必须有一个单一的终点。我们接近感染高峰,就好像这是一场像滑铁卢那样的决战,或者就像1918年11月康比涅停战那样的外交安排。然而,当然,即使对于军事史来说,单一的、决定性的结局的年表也不总是正确的。正如一场军事战争的明确结束并不一定会结束日常生活中的战争体验一样,生物性流行病的解决也不会立即消除社会流行病的影响。例如,1918-1919年大流行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在第三波也可能是最后一波病毒结束后很久才能感受到。虽然停工对当地许多企业造成的直接经济影响似乎在几个月内就解决了,但在1920年、1921年和1930年的经济调查中,仍然可以看到疫情对劳资关系的更广泛的经济影响。
然而,就像历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1918-19年的流感大流行一开始似乎有一个独特的结局。在个别城市,疫情经常以同样快的速度产生戏剧性的高峰和下降。在费城,正如约翰·巴里(John Barry)在“大流感”(The Great Influza,2004)中指出的那样,在1919年10月出现爆炸性和致命的上升,在一周内死亡人数达到4597人的峰值后,病例突然急剧下降,以至于公众集会禁令可以在这个月结束前解除,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几乎没有新的病例。破坏潜力受到物质法则限制的一种现象是,“病毒烧毁了可用的燃料,然后很快就消失了。”
然而,正如巴里提醒我们的那样,自那以后,学者们已经学会了在更广泛的大流行中区分至少三种不同的流行病序列。第一波在1918年春席卷军事设施,第二波在1918年夏秋造成毁灭性的死亡高峰,第三波始于1918年12月,一直持续到1919年夏天。一些城市,如旧金山,相对安然无恙地度过了第一波和第二波,但却被第三波摧毁了。那些在1919年还活着的人也不清楚,在第三次浪潮消退后,大流行是否已经结束。即使到了1922年,华盛顿州的一个严重的流感季节也值得公共卫生官员做出回应,像1918年至1919年那样实施绝对隔离。回首过去,很难说这场20世纪的典型流感大流行真正结束的确切时间。
谁能说出大流行何时结束?今天,严格地说,只有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世卫组织紧急事务委员会负责全球卫生治理和疫情应对的国际协调。在2002-2003年SARS冠状病毒大流行之后,该机构被授予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开始和结束的唯一权力。虽然与新冠肺炎的巨大规模相比,非典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26个国家大约有8,000例和800人死亡--相形见绌,但这场流行病对各国和全球经济的影响促使人们在2005年修订了《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这是一套自1969年以来一直保持不变的国际法。此次修订扩大了全球对世卫组织认为值得国际关注的任何公共卫生事件的全球协调应对范围,并从反应性应对框架转变为基于实时监测、检测和源头遏制的主动应对框架,而不仅仅是在国际边境采取行动。
这种社会基础设施有重要的后果,但不一定都是积极的。每当世卫组织宣布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时-通常是当它选择不宣布事件时-
因此,我们终止目前的PHEIC的许多希望现在都寄托在新冠肺炎疫苗的承诺上。然而,仔细看看20世纪的一个核心疫苗成功故事就会发现,技术解决方案本身很少能解决大流行问题。与我们的预期相反,疫苗并不是通用的技术。他们总是部署在当地,拥有不同的资源和对科学专业知识的承诺。有效疫苗的研究、开发和传播方面的国际差异对全球抗击脊髓灰质炎流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发展相对来说是众所周知的,通常是作为一个美国悲剧和胜利的故事来讲述的。然而,尽管战后几十年席卷全球的脊髓灰质炎流行病不尊重国界或铁幕,但冷战为合作和对抗提供了背景。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的灭活疫苗在美国获得许可仅几年后,他的技术就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广泛应用,尽管其在美国以外的效力受到质疑。然而,阿尔伯特·萨宾(Albert Sabin)开发的第二种口服活疫苗涉及与东欧和苏联同事的广泛合作。由于苏联脊髓灰质炎疫苗试验的成功标志着冷战合作的一个罕见的里程碑,迪梅斯运动进行曲的主席巴兹尔·奥康纳(Basil O‘Connor)在1960年的第五届国际脊髓灰质炎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宣布,“在寻找使人类免于疾病的真相时,没有冷战。”
然而,这种疫苗的差异接种追溯了冷战地理上的分歧。苏联、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接种沙宾疫苗的国家,紧随其后的是古巴,它是西半球第一个消灭这种疾病的国家。到1963年沙宾疫苗在美国获得许可时,东欧大部分地区已经消灭了流行病,基本上没有脊髓灰质炎。共产主义世界内这种流行病的成功结束立即被认为是他们政治制度优越性的证明。
然而,信任苏联疫苗试验的西方专家,包括耶鲁大学病毒学家和世卫组织特使多萝西·霍斯特曼(Dorothy Horstmann),强调他们的结果是可能的,因为苏联医疗保健系统的军事化组织。然而,这些关于威权主义本身是结束流行病的关键工具的长期担忧-这一担忧反映在目前关于中国今年在武汉进行的高压干预的辩论中-也可能被夸大了。冷战时期的东方不仅因为威权主义和国家组织和社会中严格的等级制度而团结在一起,而且还因为一个强大的共同信念而团结在一起,即父权国家、生物医学研究和社会化医学的整合。这些国家的流行病管理结合了对预防的强调、易于动员的卫生工作者、自上而下地组织疫苗接种以及团结的言论,所有这些都依赖于旨在为所有公民提供服务的卫生保健系统。
尽管如此,作为控制流行病的催化剂的威权主义可以被挑出来,并带来长期的后果。流行病可能是重大政治变革的先兆,这些变革远远超出了它们的终结,在威胁过去后极大地重塑了新的“常态”。例如,许多匈牙利人惊恐地关注着议会完全靠边站,并在今年3月底通过法令引入政府。任何流行病危机的结束,以及对维克多·奥班(Viktor Orbán)权力大幅增加的需要的结束,将由奥班本人决定。同样,许多其他州敦促动员新技术作为结束流行病的解决方案,正在为加强对其公民的国家监测敞开大门。现在正在设计的应用程序和跟踪器可以收集数据并建立远远超出最初意图的机制,这些应用程序和跟踪器现在被设计成跟踪人们的行动和暴露,以实现疫情封锁的结束。这些做法的数字化后遗症提出了新的、前所未有的问题,即流行病何时以及如何结束。
尽管我们希望相信一项技术突破就能结束目前的危机,但任何全球卫生技术的应用总是由当地决定的。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控制脊髓灰质炎流行方面取得巨大成功后,口服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在20世纪80年代末成为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倡议的首选工具,因为它承诺结束全球的“夏季恐惧”。但是,由于疫苗在一定程度上是值得信任的技术,结束脊髓灰质炎疫情取决于保持对提供疫苗的国家和国际结构的信心。无论这种经常脆弱的信任在哪里破裂或被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