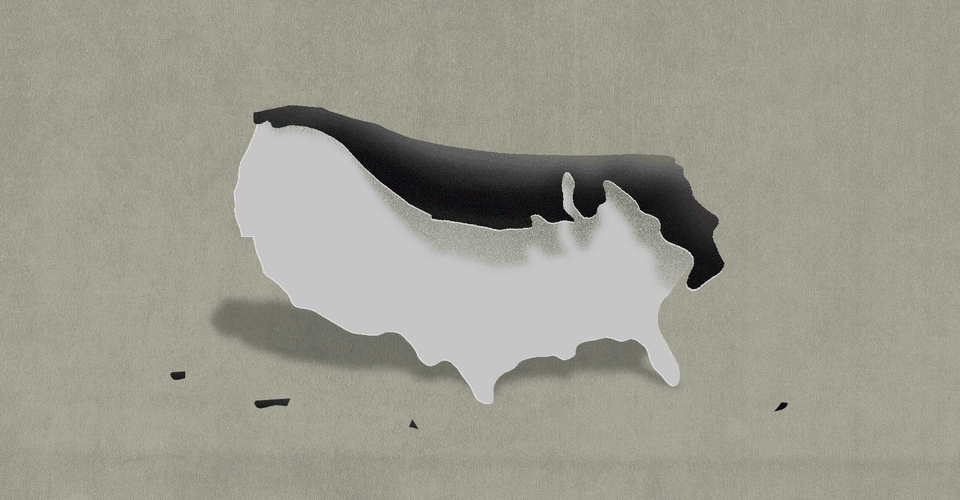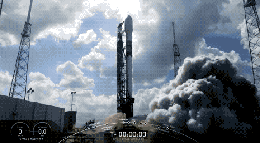美国世界的衰落
其他国家习惯于厌恶美国、钦佩美国、恐惧美国(有时是同时进行的)。但是可怜美国呢?那个是新的。
“他非常痛恨美国,”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在“小叮当裁缝士兵间谍”(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中这样描述他虚构的苏联内鬼比尔·海登(Bill Haydon)。海登刚刚被揭露为英国特勤局核心的双重间谍,他的背叛是出于敌意,与其说是对英国,不如说是对美国。“这更多的是一种审美判断,”海登解释道,然后匆忙补充道:“当然,部分是道德判断。”
当我看到乔治·弗洛伊德被杀的抗议和暴力场面在美国蔓延,然后在欧洲和其他地方蔓延时,我想到了这一点。起初,整件事看起来是如此丑陋-如此充满仇恨和暴力,以及对抗议者的原始、纯粹的偏见。美国的美似乎已经消失了,我们许多人从国外进入的那种乐观、魅力和轻松的不拘礼节。
在某种程度上,当下的丑陋似乎是一种陈词滥调的观察。然而,它触及了世界其他国家与美国之间复杂关系的核心。在“小叮当裁缝”中,海顿最初试图用长长的政治道歉来证明自己的背叛是正当的,但最终,正如他和勒卡雷的英雄、间谍大师乔治·斯迈利(George Smiley)都知道的那样,政治只是外壳。真正的动机就在下面:审美,本能。海顿-上流社会,受过教育,有文化,欧洲人-就是无法忍受看到美国。对于海登和现实世界中许多像他一样的人来说,这种发自内心的厌恶被证明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们对苏联的恐怖视而不见,而苏联的恐怖远远超出了审美范畴。
勒卡雷对反美主义动机的反思--尽管这些动机与他自己对美国的矛盾情绪息息相关--与1974年小说首次出版时一样具有现实意义。当时有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地方,现在有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这是这个世界上海顿家族已经鄙视的漫画:傲慢、贪婪、富有和当家作主。在总统和第一夫人身上,燃烧的城市和种族分歧,警察的暴行和贫困,美国的形象被投射出来,证实了世界上大多数人已经存在的偏见-同时也是掩盖自己的不公正、虚伪、种族主义和丑陋的有用工具。
对于美国来说,这是一个独特的耻辱时刻,这是很难逃脱的感觉。作为美国创造的世界的公民,我们习惯于听那些厌恶美国、钦佩美国和恐惧美国的人(有时是同时)。但是对美国感到同情吗?这是新的,尽管幸灾乐祸是痛苦的短视。如果重要的是审美,那么今天的美国看起来根本不像是我们其他人应该向往、羡慕或复制的国家。
即使在美国之前脆弱的时刻,华盛顿也占据了上风。无论它面临什么道德或战略挑战,人们都感觉到它的政治活力与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相匹配,它的制度和民主文化是如此根深蒂固,总是能够自我重生。似乎美国的概念很重要,发动机驱动它的是引擎盖下存在的任何其他故障。现在,一些事情似乎正在发生变化。美国似乎深陷泥潭,其反弹的能力受到质疑。世界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挑战美国霸权的新力量-中国-用一种苏联从未拥有过的武器:相互保证的经济破坏。
与苏联不同,中国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财富、活力和技术进步-尽管还没有达到美国的水平-同时受到西方文化和语言不理解的丝幕保护。相比之下,如果美国是一个大家庭,那就是卡戴珊家族,生活在目瞪口呆的全球公众的公开注视下-它的来来去去,瑕疵和矛盾,所有人都能看到。今天,从外部看,这个奇怪的、功能失调但非常成功的家庭暴发户似乎正在遭受一种全面的崩溃;这个家庭之所以伟大,显然已经不足以阻止它的衰落。
美国--在各国中是独一无二的--必须与我们其他国家一起承受这场事关生死存亡的斗争带来的痛苦。美国的戏剧很快就变成了我们的戏剧。当抗议活动在美国首次爆发时,我开车去伦敦见一位朋友,路过一名身穿背面印有徽章的篮球运动衫的青少年;我之所以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和妻子一直在一个美国流媒体平台上观看Netflix上关于美国运动队的纪录片“最后的舞蹈”(The Last Dance)。这位朋友告诉我,他在过来的路上发现了涂鸦:。在那之后的几周里,抗议者在伦敦、柏林、巴黎、奥克兰和其他地方游行,支持黑人的生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反映出美国继续对西方世界其他国家拥有非同寻常的文化影响力。
在伦敦的一次集会上,英国重量级冠军安东尼·约书亚(Anthony Joshua)与其他抗议者一起唱起了图帕克“改变”的歌词。这些词如此刺耳,如此强大,如此美国化,却又如此容易被翻译,而且看起来是通用的-尽管英国警察基本上没有武器,警察枪击事件也很少。自从最初对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支持源源不断以来,欧洲的聚光灯已经转向国内。布里斯托尔一座老奴隶贩子的雕像被推倒,而温斯顿·丘吉尔的一座雕像在伦敦遭到种族主义字样的破坏。在比利时,抗议者瞄准了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的纪念馆,利奥波德二世是比利时国王,他把刚果作为自己的种族灭绝私人财产。星星之火可能是在美国点燃的,但全球大火是由国家不满情绪的推波助澜来维持的。
对美国来说,这种文化优势既是巨大的优势,也是微妙的弱点。它吸引有才华的外部人士来学习、创业和振兴自己,就像它所做的那样塑造和拖累世界,影响和扭曲那些无法逃脱其吸引的人。然而,这种主导地位是有代价的:世界可以看到美国,但美国不能回头。今天,正在展示的丑陋被美国总统放大了,而不是平息了下来。
为了了解世界其他国家如何看待美国历史上的这一时刻,我采访了来自欧洲五个主要国家的十几名高级外交官、政府官员、政治家和学者,其中包括两位最有权势的领导人的顾问,以及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这些对话大多要求匿名,以便自由发言。从这些对话中可以看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带着一种震惊的不理解看着,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不确定这意味着什么,也不确定他们应该做什么。正如一位有影响力的顾问告诉我的那样,这些对话在很大程度上与焦虑联系在一起,并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即美国和西方正在接近某种程度上的临界点。“现在是怀孕的时刻,”这位顾问说。“我们只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今天的动乱并非没有先例-我采访的许多人都提到了以前的抗议和骚乱,或者美国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可以肯定的是,这场战争得到了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支持)后地位的下降-然而,最近的事件和现代力量的交汇使得目前的挑战变得特别危险。过去几周的街头抗议、暴力和种族主义爆发之际,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中国的制度缺陷,明显不可逾越的党派分歧加剧了这一缺陷,这种分歧现在甚至感染了美国机器中迄今未被触及的部分:联邦机构、外交服务机构,以及支撑平民和军方关系的长期规范。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美国现代史上最混乱、最令人厌恶和最不受尊重的总统第一任期的最后一年。
当然,并不是所有这些都可以归咎于特朗普;事实上,我采访过的一些人说,他是其中许多趋势的继承者,甚至是受益者,这些趋势是对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第一个后和平时代美国阴阳的愤世嫉俗、不道德的阳阳,而阴阴本身就是9·11事件后美国在伊拉克过度扩张的结果。布莱尔和其他人也很快指出,无论谁入主白宫,美国实力的非凡深度仍然存在,以及中国、欧洲和其他地缘政治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在这方面,布莱尔和其他人很快就指出了美国实力的非凡深度,无论谁入主白宫,中国、欧洲和其他地缘政治都面临着结构性问题。
然而,与我交谈的大多数人都明确表示,特朗普的领导层以以前无法想象的方式和速度,将这些潮流-与相对经济衰退、中国崛起、大国政治死灰复燃以及西方作为精神联盟的衰落-带到了顶点。
在特朗普担任总统近四年后,欧洲外交官、官员和政界人士都不同程度地感到震惊、震惊和恐惧。他们一直被困在有人对我描述的“特朗普诱导的昏迷”中,无法
前法国驻叙利亚大使米歇尔·杜克洛斯(Michel Duclos)曾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在联合国任职,目前担任总部设在巴黎的智库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的特别顾问。他告诉我,到目前为止,美国声望的最低谷一直是2004年巴格达附近的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内酷刑和虐待的曝光。“今天,情况要糟糕得多,”他说。根据杜克洛的说法,现在让事情变得不同的是,美国内部的分歧程度和白宫缺乏领导力。杜克洛说:“我们认为,美国几乎有能力无限反弹。”“我第一次开始产生一些疑虑.”
A,斯迈利耐心地听着海顿对西方不道德和贪婪的冗长而杂乱无章的攻击。勒卡雷写道:“在其他情况下,斯迈利可能会同意这一点。”让他疏远的是语气,而不是音乐。“。
当全世界都在关注美国的时候,是基调还是音乐引起了如此发自内心的反应?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审美上的东西吗?换言之,这是对特朗普所代表的一切的本能反应,而不是他外交政策的内容或不公正的规模?如果是后者,为什么欧洲没有举行游行,抗议中国大规模监禁维吾尔穆斯林,香港稳步扼杀民主,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或者反对整个中东地区的杀戮政权,如伊朗、叙利亚或沙特阿拉伯?正如我采访的许多人所说的那样,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遇害和特朗普对此的回应,不是已经成为世界上所有错误和不公平的东西的比喻--对美国实力本身的比喻吗?
如果这是真的,用一位欧洲领导人的高级顾问的话说,对美国的反感仅仅是又一轮“作为行为艺术的政治”-一种象征性的挑衅行为吗?我们是否正在见证美国的帝国领地比喻地跪下来表示他们反对帝国所代表的价值观?
毕竟,在越南和伊拉克、世界贸易和气候变化问题上,世界以前也反对过美国政策的音乐。偶尔,基调和音乐甚至结合在一起,疏远了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比如在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的领导下,他在国外受到了广泛的嘲笑、辱骂和反对。但即使是这个反对党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记住,当时在反对党中的是年轻的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她在2003年为“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写了一篇题为“施罗德不代表所有德国人”的专栏文章,表明尽管德国反对伊拉克战争,但她的政党仍与美国保持联盟关系。说白了,特朗普是独一无二的。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布什从未放弃过这样的核心想法,即有一首西方歌曲,歌词应该在华盛顿创作。如今,特朗普听不到统一的音乐--只有乏味的利己主义节拍。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欧洲领导人的高级顾问告诉我,特朗普的愤世嫉俗突然暴露了欧洲大陆对美国领导自由世界、“美国梦”和其他陈词滥调的势利,直到现在,这些陈词滥调都被认为是天真得无可救药的。这位顾问不愿透露姓名,因为这与私下商议有关,他告诉我,欧洲大陆对美国领导自由世界的概念、“美国梦”和其他陈词滥调的势利态度突然暴露了出来。这位顾问说,只有当天真被带走后,人们才能看到它是“一股比大多数…更强大、更有组织的力量”实现了。“。在本文中,腐烂始于奥巴马,一个对西方充满教授式的愤世嫉俗者,最终在特朗普身上达到顶峰,他放弃了美国的想法,这标志着世界历史的突破。然而,如果美国不再相信自己的道德优越感,那么除了道德等价性之外,还剩下什么呢?
这似乎是特朗普在证实美国最狂热的批评者对美国的一些指控-即使这些指控并不属实。例如,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和其他人注意到,勒卡雷(le Carré)的小说中贯穿着一条反美主义的缝隙,发现它的表达方式是道德上的对等,经不起推敲。在“小叮当裁缝”(Tinker Tailor)中,勒·卡雷(Le Carré)将读者带回了过去的某个时刻,当时斯迈利试图招募未来的俄罗斯特勤局局长。“听着,”斯迈利对俄罗斯人说,“我们都快要变老了,我们一生都在寻找彼此系统中的弱点。”我能看穿东方价值观,就像你能看透我们的西方价值观…一样。你不认为是时候认识到,你这一边和我这一边一样没什么价值了吗?“。
正如我的同事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所展示的那样,苏联监督了饥荒、恐怖和数百万人的大屠杀。无论美国最近的缺陷是什么,它们在实践上和道德上都无法与那些恐怖事件相提并论。今天,随着北京监督对其公民的大规模监控,并几乎全部监禁一个少数民族群体,中国也可以这样说。然而,这种道德平等的说法已经不再是
这种愤世嫉俗-所有的社会都和下一个一样腐败和自私-之前曾被美国完全拒绝。今天,对美国来说,国际关系只不过是一笔交易性的交易,而权力--而不是理想、历史或联盟--才是货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全球化的道德对等的世界秩序,剔除了民主民族国家的“自由世界”的天真概念,在过去几周我们看到的国际化的、后民族的反对种族主义的街头抗议活动中找到了自己的镜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示威者走上街头,这两个国家都有自己鲜明的种族分歧和虐待历史,英国和法国也是如此,每个国家都有殖民主义的历史,种族和阶级分歧持续不断。正如华盛顿邮报的Ishaan Tharoor所指出的那样,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明尼阿波利斯一名黑人男子死亡,比利时当局才推倒了一座对历史上一些最令人发指的殖民罪行负有责任的人的雕像。
特别是对欧洲来说,美国在文化、经济和军事上的持续统治仍然是其基本现实。与我交谈的一些人表示,不仅仅是抗议者犯下了某种形式的选择性失明,欧洲领导人本身也在寻求美国的保护,同时拒绝屈服于特朗普以外的任何民主表达的担忧。一位欧洲领导人的一位顾问告诉我:“(特朗普)管理得太多了,而行动不够。”目前,欧洲的战略范围似乎是简单地等待特朗普出来,希望他离任后生活能回到以前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然而,在伦敦和巴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情况不可能是这样--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和永久性的转变。
那些与我交谈的人含蓄或明确地将他们的担忧分为特朗普造成的担忧和他加剧的担忧-在他们看来,特朗普总统任期内可以纠正的具体问题,以及那些结构性的、更难解决的问题。与我交谈的几乎每个人都同意,特朗普担任总统不仅是美国的分水岭,也是世界本身的分水岭:这是不可挽回的事情。说过的话不能不说,看得见的形象不能看不见。
对于我采访的许多人来说,最直接的担忧是美国能力的明显空心化。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战争研究教授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告诉我,美国权力机构本身已经“遭受重创”。卫生系统正在苦苦挣扎,市政当局财政拮据,除了警察和军队,几乎没有人关注国家本身的健康。最糟糕的是,他说,“他们不知道如何修复它。”
事实上,内部分歧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外国观察家现在担心,这正在影响华盛顿保护和投射其海外力量的能力。“会不会有一天,这些社会问题会影响到这个国家反弹和应对国际挑战的能力?”杜克洛说。“这现在是一个可以问的问题了。”
以即将于9月份举行的G7峰会的困惑为例。特朗普试图扩大这个群体,特别是包括俄罗斯和印度,我被告知,目的是建立一个反华大国协奏会。但这遭到了英国和加拿大的拒绝,默克尔在大流行期间拒绝亲自露面。(在幕后,法国一直试图修补关系-这不是超级大国应该被对待的方式。)。弗里德曼告诉我:“这将是(特朗普的)节目,人们只是不想与他联系在一起。”
然而,从大萧条到越南再到水门事件,美国以前也经历过这种情况,并显示出了反弹的能力。然而,在这些时刻,有声望的人占据了白宫-有缺陷的,有时是腐败的,有时甚至是犯罪的,但都确信美国在世界上的独特角色。
一位欧洲大使告诉我,特朗普本人就是美国衰落的表现。“选择特朗普是一种不能很成功地适应全球化世界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