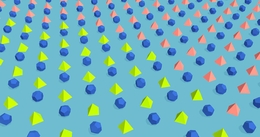新冠肺炎与注意力经济圆桌会议
在过去的十年里,“关注”作为一个紧迫的重要问题脱颖而出--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新的经济和技术正在如何改变我们的关注机制。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史无前例的新冠肺炎大流行产生了全新的注意力条件:新的屏幕时间;新的社会调解形式;新的孤立与团结的整合。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能做什么?
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史教授D·格雷厄姆·伯内特(D.Graham Burnett)致力于注意力史的研究。自从大流行封锁开始以来,他每周召开一次Zoom聚会,思考关注的问题和我们史无前例的时刻。这些会议产生了这次圆桌讨论。它是在5月的第三周远程进行的-还为时过早,无法考虑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残忍杀害后激起美国(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反响)的戏剧性事件。投稿人添加了简短的后记,简要介绍了这些非凡的发展。
与会者是:旧金山哲学家卡洛斯·蒙泰马约(Carlos Montemayor),东京和贝鲁特文学学者凯瑟琳·汉森(Catherine Hansen),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编辑兼翻译家约瑟芬娜·马索特(Josefina Massot)。最初的问题是由伦敦的独立策展人兼文化制片人加布里埃拉·沃伦-史密斯(Gabriella Warren-Smith)提出的。
自二战以来,人类第一次因为一场需要我们共同努力的危机而在全球范围内联系在一起。尽管我们经历了许多相同的剧烈变化,但我们都专注于冠状病毒这一主题。它即将出现,主导了我们的谈话、思想和不眠之夜--当我们都适应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时,它统一了我们的注意力。当我们转向集体形式的行为和思维时,注意力是如何转移的?
卡洛斯·蒙泰马约尔:我认为COVID危机潜在地提供了一种“无聊”,可以用来促进一种审美的、集体的共同关注体验。这一努力将依赖于在我们的“舒适区”之外的重新配置的环境中对新奇事物的独特开放。由于必要性和恐惧,我们突然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在这场大流行上,希望这将引发一场更大范围的对话,讨论在要求较低和危险的时代培养我们的注意力能力的迫切需要-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现在学到的任何教训。首先,整个地球突然被提醒,人类有非常相似的基本需求。
格雷厄姆·伯内特:我明白你的意思,卡洛斯,但我想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对于那些身患疾病,或正处于恐惧的阵痛中的人来说,他们正在照顾亲人,面临经济崩溃,或担心感染,“无聊”可能不会近在咫尺。因此,我们也必须考虑恐惧。关于恐惧是一种提高关注度的方式-当然,是这样的。没有什么比死亡和对死亡的恐惧更能聚焦心灵--有某种基本的、深刻的、根本的东西将注意力和痛苦联系在一起。
凯瑟琳·汉森:我的感觉是,虽然这场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普遍的”,但我们对我们所关注的事情的体验并不是:一个物体或故事的内在体验与人一样多。但集体谈话的全部目的是使这些体验一致--对它们进行校准。与人类一样,表达和校准内心事件的技术也由来已久,也许始于在洞口围着火朗诵的口述史诗;艺术品也有一种“校准”的效果。这就把我带到了当前的大流行:虽然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感到害怕和悲伤,因此倾向于用完全不同的波长进行交流,但我们都对同样的事情感到害怕和悲伤。COVID危机(和任何其他危机一样)集体校准了我们内心的注意力事件。
Josefina MASSOT:我在这一点上必须有所不同,…。COVID危机可能培养了一种“情感”交流的感觉,但我认为团结并没有在实际(最终是“关注”)的层面上实现。换句话说,我不认为我们都在发现相似的基本需求,经历同样的剧烈变化,或适应同样的新生活方式-因此,我们并没有真正走向更集体的行为和思维形式。
这主要归结为阶级:由于大流行,社会经济鸿沟大幅扩大,这催生(或加剧)了注意力鸿沟。“注意”这个词(来自拉丁语的Attendere)中嵌入了等待的行为,我们都被要求“等待”,直到这件事过去。问题是,只有相对富裕的人才能负担得起;较不享有特权的人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努力地维持收支平衡,而且他们必须立即这样做。因此,注意力状态会随着阶级界限的不同而不同。富裕的人有空余的时间,而供应过剩会滋生无聊,无聊会导致分心。弱势群体只能考虑生存,引发了一种高度集中的焦虑。这两种相反的注意力状态同样有缺陷,因为它们是极端的:前者过于混杂;后者过于狭隘。格雷厄姆,在这一点上,我想进一步强调一下你关于恐惧聚焦或提高注意力的说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正确的,但现实是,恐惧也会贬低、甚至抹杀注意力。
查克:你提到了社会经济和注意力差距,这很好,因为我一直在问自己,我们在为谁或谁的利益思考这些问题。会不会是这个大流行的时刻正在向我们表明,仅仅因为我们可能(或曾经)幸运地拥有的自我时间和孤独,我们中的一些人就可以获得并熟悉(可以说)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情感和敏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通过注意力对经验的集体校准应该以移情为指导,一种对他人需求的细心关怀-特别是那些没有丰富特权(和机会,以及社区)的人,以及这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悠闲的内部体验或悠闲的分心。
JM:我非常同意。为了让我所说的分心和过度集中的焦虑更接近真正注意力的“黄金平均数”,富人应该把他们目前分散的注意力集中到不幸的人身上,这反过来又会让后者(潜在地,部分地)扩大他们的注意力范围,包括非紧急的事情。正如你所说,这将是一种校准-一种注意力的重新分配,以匹配同样必要的经济重新分配。
CM:我认为另一种道德的、集体的注意力转移可能不仅涉及人,还涉及整个世界:对我们的环境开放和慷慨,对其他物种和环境的细心关爱。如果说我一直听到一个信息,那就是大自然现在正在“复苏”--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就是病毒,这是一个改变我们方式的机会。老实说,我觉得这种信息可能是由恐惧、悲伤和焦虑的无聊所引导的;它可能不是来自真正的注意力重新定位,而是来自困惑。尽管如此,也许即使是误入歧途的重新定位也比一切照旧要好!
DGB:我认为西蒙·韦尔(Simon Weil)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关注的“伦理”,这是一种神学上的反省,就像她深情地写道:“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患者身上是一件非常罕见和困难的事情。”她认为这是如此罕见,以至于认为这是一个“奇迹”-即使她把这种关注放在了我们对彼此的道德义务的绝对基础上。
在一个永不停歇的世界里,寻找“属于自己的时间”会让人感觉像是一种奢侈品。但是,突然之间,我们沉浸在一个持续自我时间的新时区,这也许给了一个人发展个人技能、思考和拓展创造力的不同寻常的机会。注意力已经变得自我导向,身体上和情感上都由一个人的内心环境决定。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时代,如何才能出现新的自我模式呢?
CM: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被训练成一心多用,因此它的自主性被剥夺了。新的COVID时区应该允许恢复我们的个人时间,这反过来应该有助于恢复健康的、自主的注意力。不幸的是,大流行造成的那种自我关注是疲劳和恐惧的来源,因为它与社交媒体、全天候新闻周期和各种商业利益同步前进。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注意力重新定位,从根本上远离娱乐、社会恐惧和焦虑,以及为了在社交媒体上受欢迎而不断地以自我为导向的表演。一种健康的自我关注会尽可能忽略这些焦虑源;只有这样,它才是真正的自我导向。
JM:坦率地说,我担心对于我们这些确实有足够时间在孤立中自我反省的人来说,会出现一种更自私的自我模式(因为同样,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弱势群体不会这样做,年幼孩子的父母、医生等也是如此)。无论如何,这种自私的模式不仅会因为孤立而萌芽,而且会因为对另一个-船尾的恐惧而萌芽。
问:现在身处个人或公众“前线”的人,或处于突然的妄自尊大的境地,可能会问自己:“当我们停止做(或不能做)平时做的事时,我们能发现自己的什麽?”更幸运的人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然后,出于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的背景下,这两个人,幸运的和不幸的,都会问:“那么我们能用我们所发现的关于自己的东西做什么呢?我们能为别人做些什么呢?“。我认为这是避免自私的自我模式的关键。
JM:当然,你刚刚让我想到了一种更乐观的模式:一种更多地基于存在而不是行为的模式,这当然与西方社会是如此背道而驰。话又说回来,大流行给了我们许多人一个通行证,让我们在等待的过程中只是一种“存在”。你会问,当我们停止做(或不能做)我们通常会做的事情时,我们能发现什么呢?也许这就是教训:我们不仅是我们所做的,而且是我们自己。是的,“虔诚的我”和“我是谁”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复的和疲惫的,但同义反复是必然的,陈词滥调几乎总是由经验决定的。无论“做”什么,都必须立志为他人服务,否则,我们又回到了伪装得更漂亮的自私状态。
DGB:这里的注意力语言非常有趣。关于“注意力”的话语,最有力的历史论据之一恰恰是它以其独特的现代形式出现(以对我们个人和社会生活中注意力和分心的平衡的强烈关注为标志),这一时期见证了“经典”主题的崩溃。这是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在“感知的暂停”一书中的观点:在一系列不稳定的转变之后(例如,发现眼睛和大脑根本不是类似“相机遮挡”的设备,而是渗出的、分布式的和不可靠的系统),强烈的注意力话语出现了,这是在一系列不稳定的转变之后重建某种单一主体的努力的一部分。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没有/没有特权或主权的“场所”可以证明人格存在的背景下,“注意”的语言提供了一种重新表述主观性的意志、动因、连贯核心的方式。至少在原则上是这样。当然,这是行不通的。但我们继承了这种语言--将“注意力”与“存在”的核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语言。现在的问题是:在真正的危机时期,我们如何才能有效地使用这种语言?概念意义上的主体危机--物质意义上的主体危机,也是具体化意义上的主体危机吗?
从历史上看,各种技术都因其对大脑和身体的危险影响--对一个人的思考和反思能力--而令人担忧。在新冠肺炎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独特的情况:随着我们越来越依赖这种与外界的联系,在线参与度飙升;工作和娱乐的界限在许多情况下已经被打破,起居室变成了办公室,在家的时间变成了一种无缝的、不间断的“约定”。在许多情况下,工作和娱乐的界限已经被打破,客厅变成了办公室,在家的时间成为一种无缝的、不间断的“约定”。随着我们专注于明确、明确的任务的能力减弱,对未来活动的计划可能会感觉实际上是徒劳的,我们的方向感如何改变,注意力如何变得更加分散?
CM:一种“修道院式的”或仪式化的注意力套路,涉及我们的审美和道德能力,应该取代工作和网络媒体所利用的典型的认知能力和偏好最大化能力。这将促进真正的注意力重新定位,目标是自主,这将消除你所说的那种“不间断的参与”。注意力不集中(或注意力抑制)可能是重新定位的优点,而不是无聊或焦虑的缺点。COVID危机将带来的创伤和社会恐惧将提供一个扩大这些努力的机会,不仅治愈经济和社会焦虑,而且治愈注意力本身。
dgb:作为抵抗计划的一部分,我也同情新种类的动物-修道院的“仪式”:抵抗大流行的迫在眉睫的危机,但也抵制由超级资本主义的疯狂动力造成的人类注意力能力的“水力压裂”正在发生的危机。我的乌托邦希望依靠不同类型的意向社区的崛起,正式致力于非货币化关注的纪律,并努力开发将这些承诺编入索引的新方法。我相信艺术至少在这里起到了潜在的关键作用。例如,像川原或谢清海这样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创造了“身体向前”居住时间的新方式,无论是单独的还是与他人一起的。现在工作的艺术家和干涉主义者(我想从托马斯·赫肖恩到米里亚姆·莱夫科维茨或乔纳森·范·戴克)都在同一个空间工作。我本人对所谓的“第三只鸟勋章”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个集体也可以
CM:我们与信息的关系将绝对改变--它正在改变。如前所述,人脑具有强大的同理心、不感兴趣的关注能力,但商业化的社交媒体、智能手机、计算机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利用我们的奖励系统和认知信息最大化能力。我们必须将我们的注意力从这些令人上瘾的认知媒介上移开,否则我们将错过在大流行期间注意力重新定向所提供的任何教训。
JM:有趣的是,你提出了“令人上瘾的媒介”,因为我认为这种技术的发展会加剧网瘾。它有几个诊断标准,但大流行将至少影响三个标准。首先,我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使用互联网作为一种缓解特定烦躁情绪(特别是焦虑)的方式,因为它是我们关于当前危险的主要数据来源和随后的缓解。其次,与此相关的是,当我们不使用互联网时,我们往往会比以前更焦虑。第三,我们上网的时间会更长,因为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时间和更少的注意力,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媒体节目/浏览新闻/参与社交媒体和其他不需要注意的活动。大流行持续的时间越长,这些特征就会得到更多的强化。当然,上瘾会直接影响注意力,因为(回到我的第一个答案)它同时会导致分心和过度专注的焦虑:它让我们既分散了脑筋,又痴迷于我们选择的药物。
CM:是的,上瘾可能会加剧假新闻、持续不断的TikTok和Instagram满足感、推特上准施虐的匿名欺凌,以及恐惧、社会竞争、理性沟通标准被侵蚀等各种形式的注意力扭曲所产生的精神衰弱。我们不仅面临精神衰弱的风险,而且还面临关注审美和道德价值的能力退化的风险。
DGB:我觉得“关注之友”作为一个集体所做的一些工作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我想,例如,“注意力十二论”,它表现出对注意力自由的强烈(也许是违反直觉的)承诺,本质上在于被他人铺设的注意力路径所约束的“自由”。这里是艾丽斯·默多克在“善的庄严”中对西蒙妮·韦尔的解读。但也担心将阿伦德式的“创造世界”的想法与抵制蒂姆·吴(Tim Wu)所称的“注意力商人”(Attense Merchants)的想法联系起来。如果没有这一点,关注自由似乎无非就是容易受到持续的恳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詹姆斯·威廉姆斯在他令人不安的“站在我们的光之外”一书中的诊断。
JM:我同意我们参赛能力的下降正是问题所在。至于技术调解是否会影响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我的答案也是肯定的。首先是潜在的好消息:由于每家媒体基本上都在处理相同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大量样本,可以从中挑选、比较和对比我们的消息来源。这给了我们一个独特的机会来磨练我们的注意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也许可以学习更有效地辨别假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