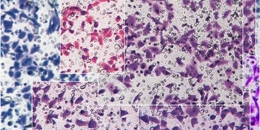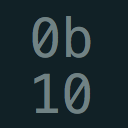关于注销文化的10篇论文
取消文化正在摧毁自由主义。不,取消文化不存在。不,它一直存在;还记得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取消尤利乌斯·凯撒的事吗?不,它是存在的,但它只是一群有钱的名流抱怨说,人们终于可以在Twitter上和他们顶嘴了。不,它不存在,除非它是好的,被取消的人配得上它。实际上,它确实存在,但是-嗯,听着,我不能向你解释,除非你读过至少四封关于这个主题的公开信。
这些只是几个答案,你会得到一个简单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取消文化是什么?”--如果你愚蠢到把它像朋友一样扔进互联网的沸水中去的话。它们是矛盾的,因为这一现象很复杂-但还没有复杂到足以阻止我就这个问题提出10个概括性的主张。
1.恰当地理解,取消是指一群坚定的批评家根据被指控为可耻和丧失资格的意见或行动,对某人的就业和声誉进行的攻击。
“声誉”和“就业”是这里的关键术语。如果你只是被质问或侮辱-如果有人在互联网上将你描述为白痴、法西斯主义者或某种亵渎的替代品-无论质问变得多么生动和具有威胁性,你都不会被取消。然而,如果你的批评者呼吁你被撤职、解雇或停业,特别是如果电话是从公司内部打来的-来自你的专业社区内部,来自同事或员工或潜在客户或同事,来自专业留言板或Slake,或者一些特定兴趣的社交媒体片段,那么你肯定有被取消的风险。
2.所有的文化都取消了;问题是为了什么,范围有多广,通过什么方式。
在人类社会中,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说或做任何事情,并期望保住你的声誉和工作。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笔下的女主人公的头上笼罩着声誉取消的阴影;专业的声誉取消笼罩着莱尼·布鲁斯(Lenny Bruce)等20世纪的人物。今天,几乎所有对取消文化持批评态度的人都有自己的底线,有些人--通常是种族主义者或反犹太主义者--他们也会取消。尤其是,批评取消文化的社会保守派不得不承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不同意今天值得取消的罪过清单。
3.取消并不完全是关于言论自由,但理论上,一个自由社会应该比它的竞争对手更少取消。
被取消的个人并没有失去第一修正案的任何权利,因为宪法上没有特定工作或名誉的权利。同时,在自身的理解下,自由主义理应比其他政治制度有更广阔的辩论空间,允许更广泛的个人表达。因此,你会期待一个自由的社会更慢地取消,更倾向于将个人和专业(或意识形态和艺术)分开,更快地提供重新获得声誉和重新开始职业生活的机会。
“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美国人吹嘘道,即使它不违反宪法,取消也会违背这一承诺-这就是为什么关于取消文化的争论经常变成关于自由主义本身的争论的原因之一。
4.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取消的方式,扩大了取消的范围。
另一方面,怀疑论者可能会说,使美国成为自由国家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空间和距离--用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老话来说,你总是可以通过“为领土点灯”来逃避当地墨守成规的专制。但在互联网的统治下,村子是不能离开的: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每次都是一样的。如果你在一群完全陌生的人中说了一些话,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上传了视频,或者如果你碰巧在社交媒体上说了一个错误的笑话,或者如果互联网还记得你很久以前说过或做过的事情,你可能会被取消。你不一定要显赫或有政治色彩才会被公开羞辱和永久标记: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度过特别糟糕的一天,而后果可能会持续到谷歌一样长的时间。
5.互联网也让人们更难弄清楚言论是变得更自由了还是变得更不自由了。
当取消文化的批评者担心网络时代潜在的言论寒意时,有一种反驳是,你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比1990年左右的杂志和日报样本中更多的想法-既有激进的,也有有害的-比你在1990年左右的杂志和日报样本中找到的要多得多。与以前的印刷媒体相比,现在在你的智能手机上更容易遇到意识形态的极端,也更容易遇到仇恨的言论。
但与此同时,互联网加速了文化机构的整合,使得纽约时报、常春藤盟校和其他庞然大物的影响力比30年前更大,而且可以说,它增加了城市、地区和整个行业的统一性。而关于取消规范的斗争反映了这两个变化:对于想要取消的人来说,互联网的混乱让建立严格的新规范显得更加重要,以免在线种族主义者赢得…。但对于那些受到取消威胁的人来说,他们感觉自己面临着被越来越整合的新闻或学术市场拒之门外的风险,或者是无视每个董事会和人力资源部都接受的共识。
6.名人是最容易成为目标的人,但实际上最难取消。
取消文化的一个例子是活动家苏伊·帕克(Suey Park)2014年发起的#取消科尔伯特(#CancelColbert)的标签运动,原因是他在Twitter账号“科尔伯特报告”(The Colbert Report)上发布了一条讽刺推文。六年后,斯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仍然没有被取消。戴夫·查佩尔(Dave Cappelle)、J·K·罗琳(J.K.Rowling)和一长串知名流行文化人物也是如此,他们曾面对网络暴徒,活着讲述、销售和表演。
他们的坚韧不拔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认为取消活动只是名人对他们的批评者的抱怨而不屑一顾。如果某人有足够大的名字或粉丝基础,实际取消的门槛相当高,这位名人甚至可能有机会-就像2016年竞选活动中的某个真人秀电视明星-利用对潜在取消者的仇恨来确认粉丝或巩固追随者。
7.取消文化对那些在他们的领域还在上升的人最有效,它影响了许多实际上没有被取消的人。
取消的最终目的是为大多数人建立规范,而不是把星星带回地球。因此,取消的氛围可以成功地改变人们的谈话、辩论和行为方式,即使它不能成功地摧毁它所针对的一些名人的职业生涯。如果你能取消那个站在罗琳一边的不太知名的小说家,你就不需要取消罗琳;如果你能阻止年龄只有一半的人说出他们的想法,你就不需要除掉上周在哈珀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签名抨击取消文化的著名学者。这样做的目的不是惩罚每个人,甚至不是惩罚很多人,而是羞辱或吓唬足够多的人,让其他人都服从。
8、左右派都取消了,只是今天的右派力量太弱,做不好。
当保守派试图让大学教授因反美主义而受到纪律处分,或者批评以色列的人因反犹太主义而下台时,是不是取消了文化?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Dixie Chicks(抱歉,以前被称为Dixie Chicks的艺人)被电台和巡演场馆抛弃时取消了文化,还是当比尔·马赫(Bill Maher)的“政治不正确”因为违反爱国正确而被字面上取消了?绝对一点儿没错。
但正如后几个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右翼文化力量的最后一个高峰是9·11之后的爱国正确氛围。11,过去的文化世代。今天,最害怕右翼取消文化的人通常在特朗普时代的专业保守主义内部工作。(即使对他们来说,作为一名专业的NeverTrumper,也经常会有新的生活在等待着他们。)。右翼的取消企图大多是为了争夺对日益缩小的地形的控制权,偶尔会对红州学者和反特朗普的名人发起攻击。与此同时,左翼的取消斗士想象他们征服了整个非福克斯新闻地图。
9.取消文化辩论的激烈程度反映了互联网作为取消的媒介与左翼道德规范日益增长的力量作为取消的理由的交集。
这不仅仅是技术或意识形态的问题,换句话说,两者兼而有之。年轻的新兴左翼希望将当前反对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禁忌作为更广泛限制的典范--对什么是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同性恋恐惧症有更宽泛的定义,对什么样的言论和行为会带来“伤害”的更全面的理论,以及更精确的语言礼仪,供受人尊敬的专业人士遵循。而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无论是机构外部还是内部,都是这种推动的关键机制。
这些新的左翼规范是否会是狭隘的,或者它们是否会简单地向自由主义注入新的道德来取代旧的新教共识,这是值得商榷的。与限制曾经主流的、现在的“恐惧症”观点相比,他们是否会为以前被边缘化的声音拓展更多的空间,这是值得商榷的。但毫无疑问,与10年前或20年前相比,违反紧急规范的人更容易被取消。
10.如果你反对左翼取消文化,光靠自由主义和言论自由是不够的。
我刚才说过,关于取消的争论也不可避免地是关于自由主义及其限度的争论。但是,要在这些争论中捍卫自由主义立场,你需要的不仅仅是抽象地捍卫言论自由;你需要为了一些重要的、真实的想法而捍卫言论自由。一般原则固然很好,但如果你不能根据其本身的优点来捍卫有争议的想法,那么仅仅是为了给它们一个平台的程序性论点,就不会在热情的、道德上自信的攻击中维持下去。
因此,害怕左翼对取消法案热情的自由主义者或中间派人士需要一种反驳,而不仅仅是建立在正确到错误的原则上。他们需要找出他们认为新的左翼规范不仅太过吹毛求疵,而且完全错误的地方,并在那里进行斗争,既要有实质内容,也要有自由原则。
否则,他们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只可能为他们赢得最后被取消自己想法的特权。
“泰晤士报”致力于向编辑发表各种信件。我们想听听您对这篇文章或我们的任何一篇文章的看法。这里有一些小贴士。这是我们的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
关注“纽约时报”在Facebook、Twitter(@nytopinion)和Instagram上的评论栏目,加入Facebook政治讨论组“女性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