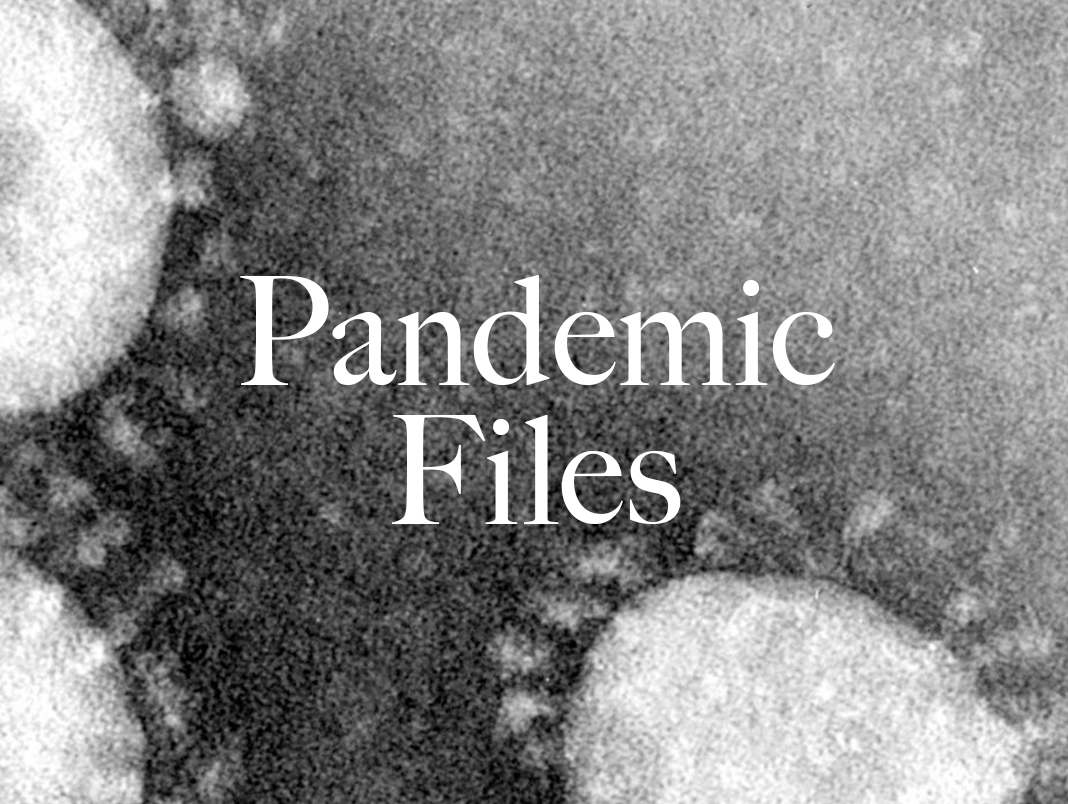气味和身份之间的联系
作为一名住院医生,我每天都会记录新冠肺炎剥离的东西。首先是呼吸-感染患者的锯齿状吸入,呼吸机供应有限,通过口罩和管子发出的氧气嘶嘶声。第二种是致命的血块聚集,也就是脓毒症的搏动血管。第三是身体本身的活力--延长的恢复期,虚弱的体力,疲惫的肌肉。最后,也是最奇怪的,气味。最近,“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嗅觉丧失是新冠肺炎最好的预测指标,而不是我们预期的症状-发烧、咳嗽、呼吸急促。
嗅觉丧失--“嗅觉丧失”--听起来是无害的:比起呼吸困难或颤抖,它的威胁性或内脏要小得多。但我对嗅觉丧失的了解足以让我认识到它窃取我们最珍爱的东西的能力。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怀孕了,我的女儿已经34周了,而且还在成长。没有亲自工作,我以一种我从未想象过的方式想念鼻孔里的医院-锐利的消毒剂,汗水,消毒的空气。怀孕期间,家里不断传来气味:奶酪的辛辣,泡菜的酸味,我邻居水仙花床上刚翻过的覆盖物。垃圾桶的气味太难闻了。我恳求我的丈夫把它赶走;他不断地把软弱无力、装满了一半的沉重的袋子拖到楼下的垃圾箱里。相反,附近的鲜花或新鲜出炉的香蕉面包是一种享受。这些天,我以鼻子为先周游世界。
作为波士顿一家医院的一名怀孕医生,我的任务是远程护理患有轻微症状的年轻患者或患有一长串慢性病的老年患者。我们一致希望避免去医院,因为我们对病毒可能如何监禁我们的身体感到困惑。在虚拟访问中,我与正在从我们都认为是冠状病毒感染中恢复的患者交谈。他们告诉我,他们的课程很温和,所以,建议他们在家休养,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测试。但他们的病症剧本-发烧,胸口轻度紧绷,长期疲惫,失去嗅觉和味觉-听起来肯定像新冠肺炎。
一位女士告诉我,她已经虚弱好几个月了。所有的东西都是无味的;她和她的男朋友在他们的小公寓里一起隔离,轮流用微波炉加热方便面和用勺子把面条放进对方的嘴里。他们没有进食的动力。自3月以来,一位曾因血管疾病接受过多次手术的绅士一直在马萨诸塞州北部进行隔离,但在此之前,他与其他退伍军人住在一所拥挤的房子里。他看不到任何人,整天带着他的狗沿着一条废弃的小溪散步。他告诉我,每样东西尝起来都像罐头面包在他嘴里变成了金属,那是他在军队里的时候豆子罐头的叮当作响的味道。
当我18岁时,一个新宣布的医科预科学生,我母亲失去了嗅觉。突然间,这位每晚都住在借来的书和烹调的小茴香咖喱作为晚餐的麝香书页里的图书管理员下船了。
那年夏天,我母亲成了我的第一个病人。几周前,我刚从大学毕业回到家,从波士顿的冬天脸色苍白,准备去德克萨斯州90度的夏天,在游泳池里泡个澡。一家实验室聘请我做研究人员,我开始了与生物学的幽会。每天,我都会看幻灯片上的唾液样本,点击绿色查看正常染色体对的细胞,点击红色查看额外的拷贝。我们正在寻求一种早期发现肺癌的检测方法。我斜靠在显微镜的猫头鹰眼睛里,把我带到了另一个地方--星空,街机游戏。但这感觉不像是医生的世界;没有诊所,急切的病人就在外面排着长队等待。没有布满皮疹的身体需要破译,没有肿块需要触诊。没有痛苦或胜利的故事。
在国内,一个不同的故事展开了。我母亲提到,在做她最拿手的咖喱鸡肉时,她闻不到烤辣椒、大蒜和西红柿混合的令人兴奋的味道。我觉得很奇怪--她从来没有打开过菜谱,而且总是用鼻子做饭。她甚至不用量就能闻到菜里有盐的味道。下午,母亲在院子里照料着她最喜欢的玫瑰花丛,探身想闻一闻令人兴奋的香味,但什么也没有找到。那天晚上,为了准备在朋友家参加晚宴,她用让·保罗·高蒂埃(Jean Paul Gaultier)设计的分类型香水结束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但香水没有任何效果。
我们都知道有些不对劲。我仔细阅读了祖父的旧内特解剖学地图集。我了解到,嗅觉始于头部和颈部的第一根神经。神经将其卷须埋在粉红色的鼻衬里;从那里,它蜿蜒穿过将鼻子和大脑分开的筛状筛板,越过筛骨窥视,到达大脑的表面。然后,它的纤维缠绕在两个灯泡周围,沿着一条长长的隧道将信息发送到感觉心房。当一个讨厌的颗粒到达鼻子时,它会与鼻孔中跳舞的指状突起相互作用。颗粒与感受器的结合会引发一种冲动,这种冲动会向大脑传播,并发出一种气味。正是在这里,柑橘类水果的一滴液体被揭示为令人愉悦的柠檬气味,或者从垃圾桶发出的恶臭被登记为恶臭。味道也是气味。虽然舌头起着辅助作用,但味道很大程度上来自我们咀嚼和咀嚼时食物的气味。
气味也是记忆。我本可以在几个研究中找到证实这一点的证据,但我却查阅了我的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斯旺的路”,重读了这段话,在这段话中,叙述者心不在焉地咬了一口蘸着茶的黄油马德琳,突然想起了他童年时期的那个星期天下午,他的姑姑,康布雷的灰色屋顶:“当从很久以前就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味觉和嗅觉,更脆弱但更持久,更非物质,更执着,更忠诚,久久不变,就像灵魂一样。“。
那天晚上,我学到了行医的第一条真理:了解你病人的痛苦状况。嗅觉丧失(嗅觉丧失)和她的堂兄味觉障碍(味觉改变)拆除了构成生活的脚手架。我母亲的反应是坚定地回忆起她过去的气味:孟加拉季风过后潮湿的土地,湖边市场摊位上飘来的新鲜煮好的咖啡,茉莉花挂在她的歌唱教练的辫子上。她哼唱了泰戈尔一首老歌中的一句台词:Phuler Gondhye Chomok Lac uthecche mon mete(我们得到的最好的礼物就是被路边花朵的芳香唤醒。)。
但是回忆是不够的。我母亲被气味抛弃了,她害怕煤气泄漏和烤焦的面包。她停止了园艺和烹饪。她失去了打扮的乐趣。派对前,她在锁骨上喷上古驰香水,然后悄悄走向我父亲:贡卓墨西哥薄饼?他亲切地笑了笑,说:“你闻起来像女王!”但她的表情依然冷漠。当我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时,我母亲的身份被不知不觉地从她身边夺走了。
在几年的医学培训中,我把母亲嗅觉障碍的教训藏了起来,同时也掩盖了一个令人烦恼的事实,即我无法给她带来安慰或解脱。在2月份的一个下午的诊所里,就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来袭之前,它重新浮出水面,现在我感觉这是正常的最后记忆。那天我的第三位病人是琳达,一位身材苗条的73岁妇女。琳达曾在许多基金会的董事会任职,戴着精美的项链。与我早些时候见过的病人相比,她的健康水平令人羡慕-一名电车操作员每次偏头痛时左侧就会变得软弱无力,一名病人护理助理在糖尿病侵蚀她的左脚趾时仍在上夜班。然而,她却很沮丧。“我闻不到味道,”她说。“我甚至不能品尝我的食物。我在上面浇上柠檬:什么都没有。“。我找到了第二次机会。
琳达在六年前的春天失去了她的气味,没有特别的疾病或挑衅。那是在她离婚很久之后,甚至在她戒烟之后更久。慢慢地,在门多西诺海岸探望女儿时,她意识到自己闻不到花香。这并不是说她以前的嗅觉特别灵敏,而是她曾经认为理所当然的一小部分现在已经消退了。一个自称“美食家”的人,随着她的气味消失了她生活中的大部分诱惑力。
我列举了许多年前我没有为母亲考虑的可能性:过敏、病毒感染、肿瘤、中风、特发性(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头绪)。当我进行考试时,琳达坐在考台上,双腿晃来晃去。我拿着咖啡(一种强烈的气味),然后用酒精棉签(一种有害的刺激物)在她的左鼻孔前面,然后是她的右鼻孔。我轻拍她的鼻窦,窥视她的耳道,测试她面部肌肉的力量,检查她的舌头是否对称。这项研究没有任何暗示。
她很谨慎。一连串的医生对她的病情轻描淡写或不屑一顾,我知道我必须认识到她失去了身份,并提供安慰,即使没有完美的诊断可以找到,也没有我们可以归因于这种感觉被盗的病变或肿块。所以我默默地敬畏地给出了“嗅觉丧失”这个词,解释说她的痛苦是真实的,尽管是神秘的。啊,真灵。慢慢地,我获得了她的信任。我给琳达开了鼻腔类固醇泡芙,以防这能减少可能阻塞感觉器的肿胀。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呆了30分钟后,我搜索了她的电子病历--她的病情和身体档案--寻找过去的会诊记录。在过去的一年里,琳达因为各种问题进进出出诊所-背部疼痛,耳垢,喋喋不休的咳嗽。每一次,她都会提醒她的医生和护士注意嗅觉的丧失。“我愿意尝试任何事情,”她告诉一位医生,这位医生转诊了一位心身药物。一周后,琳达发现自己脸朝上躺在一位针灸师的桌子上,当针头轻轻刺进她的额头时,她闭上了眼睛。
我发现一位耳鼻喉外科医生用简洁的散文写着一张进度条:“她最想念柠檬了。”我想象着琳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童年,和她的姐妹们在院子里的柠檬树周围跑来跑去,在她的街区搭建柠檬水摊-她对这项贸易的特殊天赋,预示着她作为一名女商人的未来成功-然后回到家,口渴而上气不接下气,被祖母做饭的气味所鼓舞,太平洋鲑鱼鱼片闪闪发光,点缀着柠檬片和迷迭香,用薄荷冰茶追赶着,紧随其后的是桃子馅饼和香草。想象是医生的任务吗?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知道你病人的悲伤是什么样子,我告诉自己。
我好奇地看着她的鼻咽镜检查的描述:一个光纤摄像机穿过她的鼻孔,延伸到她的鼻子后面,医生在那里可以看到她的舌头、会厌和声带。下鼻甲正常,无水肿。中间无质量块。中肉未闭,无脓性。鼻中隔偏右。舌根对称。没有囊肿的瓦莱丘拉。环状软骨后水肿。左右声带均呈弓形。鼻子和所有奇特的结构:湿润的口袋,气道,薄薄的软骨板和左右分开的骨头。镜头进入粉红色、蓬松的未知世界,就像爱丽丝从兔子洞跌入仙境一样。然而,尽管有一连串的词语,但解释可以总结为一个词:“正常”。她在开始的地方结束了,失去了亲人。
治疗的工作让琳达忙得不可开交。她尝试了高渗盐水漱口水-将超级盐水沿着一个鼻孔往上流,然后沿着另一个鼻孔往下流,让它在她的鼻窦里刺痛和灼烧,希望能把它们清除掉-然后每天的前两个小时都用来漱口鼻涕。她吞下了元素锌药片,建议这会让她的味道更辣。
一个月后,她回来了,一如既往地优雅,她的嗅觉没有真正的改变。“我能尝到强烈的香料,”她说,“但还是没有柠檬或香草。”琳达在钱包里随身带着辣酱。然而,即使是最强烈的味道也感觉很遥远,就好像它们是从隔壁的房间飘进来的。我已经到了清单的尽头,开始摸索新的选择,提供先进的测试和专家。她重访了耳鼻喉科诊所。预约过敏症检查。得到了她大脑和鼻窦的CT扫描,每个脑室、脑叶和脑沟的详细示意图。与此同时,我建议她通过强调食物的温度和质地来欺骗她的舌头。也许她会在吃烤箱里热着的薯片、嘴唇上粘着盐,或者涂满奶油哈里萨的冰凉脆脆的生菜时找到一些安慰?
然后大流行来袭了。照顾琳达是我在诊所里,检查病人,听亲身故事的最后记忆之一,回到新冠肺炎成为不变的重复之前。琳达和我母亲教会了我如何理解和想象嗅觉障碍;她们还教会了我为什么嗅觉很重要。
我们的身体是惊人的神经束,习惯于惊人地丧失。只有一块肌肉摇摇欲坠,其他几块肌肉则共同承担这一重任。左眼结巴,右眼介入。即使我们的大脑被一分为二,其中一方也会为它无法理解的概念找借口,这个过程被称为虚构--这是一个花哨的词,指的是让我们维持完整的错觉的诡计。但气味的能力是独一无二的:它携带着我们走过的世界的“短暂痕迹”,用哲学家米歇尔·塞雷斯(Michel Serres)的话说,“气味与专一性相对应。”气味不能在屏幕上找到;它必须活着:通过混乱、暴露、接近。它也是通向以前版本的我们的通行证--通向那些让我们高兴、感动我们、灌输我们的价值观、记录我们的怪癖的场景。然而,它的损失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们看起来完全健康,没有受到疾病的破坏,而且我们偷偷地护理着一种奇怪的损失。嗅觉障碍是反复无常的。我不能说气味是否以及何时会为那些失去气味的人恢复,无论是新冠肺炎的幸存者还是像琳达这样的患者。
没有复苏之路的医生就像没有指南针的航海;然而,在实践中,我们总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航行。琳达还没有康复,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康复。她会让卡尔
在我上次拜访琳达时,我告诉她我母亲的事。她忍受了七年的嗅觉障碍,然后,在没有任何大张旗鼓的情况下,嗅觉障碍慢慢消退了。一天早上,她在走进厨房之前发现咖啡在煮。另一天晚上,炒洋葱的焦糖味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尽量不宣布这件事--“它回来了!我能闻到!“--怕再次失去轻飘飘的感觉。在厨房柜台上,一堆装满香水样品的目录和时尚杂志等待回收利用。我母亲把每一个都剥开,露出一个样品,深深地闻了闻花香、麝香、柑橘、檀香、薰衣草和绿茶。即使是现在,有几天我也会抓住她,她的鼻子埋在光滑的书页之间,像新生儿第一次呼吸尘世的气息一样呼吸着香水。
Amrapali Maitra是马萨诸塞州波士顿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的内科医生和医学人类学家。她写的是关爱、文化和人类的医学体验。她的论文曾发表在《麦克斯威尼杂志》、《弹弓》、《纽约时报》和《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她在Twitter@amrapalimaitra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