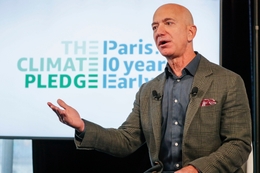慢性躁狂和持续的愉悦状态
让我澄清一下,我不是指任何复杂意义上的“幸福”。我不是指幸福、幸福、生活满足感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我的意思是心情好--比好还好,“兴奋”,精神饱满,热情高涨。
在精神病学文献中,他们称这种状态为“欣快感”或“兴高采烈”。它可以由娱乐药物产生,或者通过在大脑的某些位置放置电极,或者通过一些脑损伤,或者通过神经或精神障碍产生。这在躁狂和轻度躁狂发作中很常见。当然,这也是一种正常的情绪,健康清醒的人也可以进入。
但大多数愉悦状态都是短暂的,而且大多数刻意诱导愉悦的方法都不起作用。例如,吗啡可以产生快感,但不是一次持续几个月;你会对药物产生耐受性,直到产生快感的剂量和致命剂量相交。而像中奖这样运气好的人不会永远保持兴奋-他们最初感觉很好,但后来适应了变化的环境。
所以,你可能会问,大脑中是否有某种负反馈循环,使得欣喜总是暂时的?连续几个月或几年一直感觉很棒,真的是不可能的吗?
有一种叫做慢性躁狂的东西,正如它听起来的那样:一种躁狂状态,包括欣喜/欣喜,持续超过6个月,有时是永远的。
19世纪的精神病学家埃米尔·克拉佩林(Emil Kraepelin)是第一个对慢性躁狂症进行临床描述的人,尽管一些现代神经学家认为,今天这些患者会被诊断为额颞部痴呆[1],而在他那个时代,慢性躁狂症是患者被送往精神病院的第二大常见原因。
除了病程长短外,慢性躁狂症患者与躁郁症患者还有几个系统的不同之处。慢性躁狂症通常不会与抑郁交替出现,而且比双相躁狂症更有可能伴随着“兴高采烈的情绪”而来。与双相躁狂相比,慢性躁狂更有可能伴随着妄想,特别是浮夸的妄想,而双相躁狂更可能伴随着精神运动激动的症状,如紧张、言语压力、失眠和性欲增强。[2]慢性躁狂更有可能开始于40岁以后。
从案例研究来看,典型的模式似乎是一个人过去可能有过短暂的躁狂发作,“陷入”一种慢性躁狂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们通常是欣喜的,但与现实脱节,从事鲁莽、不恰当或令人厌恶的行为,直到当邻居或亲戚把他们带到医院时,他们才引起精神病学家的注意。
“只有吃喝抽烟吸鼻烟这些粗俗的享受,才能在他们心中唤起鲜活的感情,进一步满足他们个人的愿望和愿望…。[他们]夸夸其谈,大摇大摆,试图为自己赢得一切可能的小优势。“[1]。
“他们把口袋里所有可能的垃圾都收集起来,把它们弄得乱七八糟,摩擦和擦拭东西,用破布和丝带碎片装饰自己。”
精神病学家Frederic Wertham在1929年撰文描述了符合总体模式的慢性躁狂症病例。[4]在所有7个病例中,慢性躁狂症开始于30岁以后(晚于双相情感障碍的典型发病),并且所有病例都持续了几年。在几个病例中,患者以前有过短暂的躁狂发作。
Wertham描述了诸如“活动压力大,社交能力强,缺乏疲倦,幽默感”,“吵闹和健谈”,“愉快”和“兴高采烈”的情绪,“疯狂的计划”和错觉(不切实际的商业交易,宗教启示,百万美元遗产),“开玩笑和嬉戏,开玩笑和大笑”,“粗俗和亵渎”的语言以及对护士的性侵犯。
像克拉佩林的病人一样,韦尔瑟姆的一位病人收集无用的物品并装饰自己--她“头发上戴着鲜花,纽扣上系着一些彩色羊毛”…。继续用小物件装饰自己。“。
沃瑟姆注意到一些模式:慢性躁狂症患者在发病时往往是中年,甚至在患病前就倾向于高度社交和活跃的性格,没有认知能力下降的迹象(正如你在痴呆症中所预期的那样),而且往往体格魁梧。
类似的特征也出现在最近的慢性躁狂症的案例研究中:高龄、囤积、妄想、放纵行为。
一位68岁的妇女30年来一直处于“情绪高涨”的状态,在此期间,她越来越多地囤积物品,生活在越来越肮脏的环境中,拒绝一切帮助。她在接受测试时没有痴呆症或记忆力丧失的迹象,也没有药物滥用史。在生病之前,她曾在丈夫去世后经历过一次抑郁发作,在此之前,她曾是一名“相当开朗的女校长”-就像韦瑟姆的病人一样,她的基线性格是开朗的。她在接受锂治疗后康复了。
一位65岁的印度男子患有躁狂症已有48年之久,12岁时开始发烧。他“开朗、乐观、健谈、外向、过于自信”,并参与了政治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他也有鲁莽的行为,不付车费就坐火车穿越印度,偷东西送穷人。他“经常把自己描述为上帝的使者,拥有特殊的能力,声称上帝创造他是为了穷人的福祉”。他找不到工作,离过两次婚,但他的情绪“总是开朗或易怒”。他最终因邻居和亲戚的投诉而住院,并在接受抗精神病药物的临时疗程后康复。
一位狂躁了17年的33岁妇女“表现出浮夸的信念和欣喜的情绪”,由于她“过于熟悉”的行为而无法保住工作。她从未滥用过毒品。“她的父母形容她病前的性格大体上和蔼可亲、合作、富有创造力,但偶尔也很强势和固执。”
一名年轻女性从小就有躁狂症状(行为问题、躁动、健谈、情绪不稳定和放荡不羁,青春期开始有性挑衅行为),经放射检查发现小脑严重退化。
另一名患者是两年前因被电线缠住而触电的一名年轻男子,他出现了狂躁症状,表现为浮夸而受迫害的妄想、幻觉、判断力差和食欲增加。
一名55岁的男子变得易怒,非常爱交际,花钱大手大脚,他被发现患有少突胶质瘤,这是一种位于左侧颞顶叶的大脑瘤,手术后他的症状有所改善。
一位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八岁小孩,性格有了明显的改变,“他开始过度说话,唱歌跳舞。他一回到家,症状就变得更严重了。他开始与亲戚、邻居和陌生人交谈,交谈的内容是他将如何在电影中表演,他将如何建造一座大房子,他将娶一位美丽的女士,等等。他唱着电影歌曲,即将离开家,过去很难找到他并将他带回家。他的食欲增加了,睡眠受到了干扰。大多数时候,他都是非常快乐和开朗的。“[11]。
据报道,一名中风患者损害了下丘脑的脑室周围区,出现了“持续的欣快感”,而在另一例下丘脑脑外科手术中,“每次外科医生轻轻擦拭脑室底部的凝血时,患者都会放声大笑,吹口哨,讲笑话,并发表淫秽言论。”[12]。
一位81岁的女性右侧丘脑中风“变得越来越兴奋和健谈,并有浮夸的妄想症…。她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并开了不恰当的玩笑。她还报告说,睡眠需求减少了。“。经过一个临时疗程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后,她恢复了健康,但仍然“有轻微的欣快感”[13]。
在66名连续接受头部创伤治疗的患者中,6名(9%)发展为躁狂症[14]。唯一与躁狂症显著相关的病变部位是颞极(p=0.0005),这也是额颞痴呆和阿尔茨海默病最早受损的区域之一。
与脑损伤后发展为双相情感障碍的患者相比,仅在脑损伤后出现躁狂的患者明显更有可能出现皮质损害(特别是。眼眶额叶皮质和右侧基底颞叶皮质。)[15]。
另一项研究发现,脑损伤后的躁狂症“主要与右半球的眶额叶、大脑、尾状核和基底颞叶病变有关”[16]。
卒中后躁狂症患者最常见的病变部位(74例)是右额叶和基底节区。在16例脑肿瘤后出现躁狂症的患者中,13例肿瘤位于额叶、颞叶或皮质下边缘结构,2例(12.5%)患有慢性躁狂症。[17]。
据报道,多发性硬化症的症状之一是欣快感,或称“硬化性欣快症”,一种不同寻常的愉悦、乐观和缺乏对身体残疾的意识。
在一项对44名MS患者和22名健康对照的研究中,13%的MS患者有欣快感,13%的MS患者有去抑制,而对照组没有。在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欣快感程度和MRI上观察到的额颞部退行性变的严重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p<;0.01)。[18]。
1873年,夏科特对多发性硬化症的最初定义将“愚蠢的无缘无故的大笑”描述为症状之一;布朗和戴维斯在1926年对100例患者进行的调查中报告说,63%的患者欣喜若狂。在1986年对76名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研究中,48%的患者被发现是快乐的,并且快乐的患者比非快乐的患者更有可能有进行性的病程,有脑部受累,有更严重的身体和功能残疾[19]。
在没有精神病史的患者中,大脑损伤会导致躁狂,包括慢性躁狂,特别是额叶和颞叶的损伤。其他部位如小脑、丘脑和下丘脑的损伤也会导致躁狂。由于右脑受损,躁狂症似乎也有变得更加普遍的趋势。
额叶和颞叶参与自我约束和适当的行为,所以它们的受损会导致躁狂的一些去抑制和强迫方面也就不足为奇了。显然,大脑损伤也会导致持续的愉悦状态。
我认为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人类有可能连续数月或数年保持一种愉悦的状态。(在这些案例研究中,欣喜通常会被易怒打断,但不会出现悲伤或沮丧的情绪。)。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这些长时间愉悦状态的大多数例子都是不受欢迎的。它们通常伴随着鲁莽或有害的行为、妄想和认知障碍。
它们也是不可预测的--一些但不是所有中风、肿瘤或这些脑区受伤的人会变得躁狂或欣喜若狂。
但持续愉悦状态的存在表明,原则上有可能故意诱导一种长期的高涨情绪,而不会产生一些有问题的副作用。
一个普遍的发现是,大脑深层刺激伏隔核或丘脑底核会引起短暂的欣快感,有时会导致彻底的躁狂发作。然而,这里有一种耐受效应--如果连续刺激一年,最初导致欣快感的同一种刺激在12个月时不会产生可察觉的效果。这种类型的电刺激的某些变体可以产生长期的影响,这并不是不可能的。[29]这种类型的电刺激的某些变体可以产生长期的影响,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在连续刺激一年的情况下,最初引起欣快感的刺激在12个月时不会产生可察觉的效果。[29]这种类型的电刺激的某些变体可以产生长期的影响,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对开发一种形式的“做对了电线”的前景很感兴趣。
[1]Gumbergi,Leandro Boson等人。“Kraepelin对慢性躁狂症的描述:一张符合行为变异型额颞叶痴呆表型的临床图片。”Arquivos de Neuro-Psiquitria 74.9(2016):775-777。
[2]Perugi、Giulio等人。“慢性躁狂症。”“英国精神病学杂志”1998年(173.6):第514-518页。
[4]Wertham,F.I.。一组良性慢性精神病:持续躁狂兴奋:2000年躁狂发作的年龄、持续时间和频率的统计研究。“美国精神病学杂志”86.1(1929):17-78。
[5]Fond,G.,F.Jollant和M.Abbar。在第欧根尼综合征(肮脏综合征)的情况下,需要考虑情绪障碍,特别是慢性躁狂症。“国际心理老年病学”23.3(2011):505。
[6]Mendhekar,D.N.等人。“慢性但不耐药的躁狂症:一例病例报告。”“斯堪的纳维亚精神病学学报”109.2(2004年):第147-149页。
[7]Marhi,G.S.,P.B.Mitchell和G.B.Parker。“重新发现慢性躁狂症。”“斯堪的纳维亚精神病学学报”104.2(2001年):第153-156页。
[8]Cutting,J.C.。“儿童期慢性躁狂症:可能与小脑疾病的放射学图像有关的病例报告。”“心理医学6.4”(1977):635-642。
[9]Ameen,Shahul,Siddhartha duta和Vinod Kumar Sinha。“电击所致慢性躁狂症患者的脑电图改变及丙戊酸钠对其改善作用。”双相情感障碍5.3(2003):228-229。
[10]Rahul,S.A.H.A.和Kiran Jakhar。“少突胶质瘤表现为慢性躁狂症。”上海精神医学档案27.3(2015):183。
[11]Subrahmanya,B.和Shivolrakash HS Narayana。“多发性头髓炎后慢性躁狂症--1例报告”“印度精神病学杂志”23.3(1981):266。
[12]Barbosa,Daniel An等人。“处于精神病理学和神经外科的十字路口的下丘脑。”神经外科焦点43.3(2017):E15。
[13]Kulisevsky、Jaime、Marcelo L.Berthier和Jesús Pujol。“右侧丘脑梗塞后出现偏瘫和继发性躁狂。”神经病学43.7(1993):1422-1422。
[14]Jorge,Ricardo E.等人。“创伤性脑损伤后的继发性躁狂症。”“美国精神病学杂志”第150期(1993):916-916。
[15]Starkstein,Sergio E.等人。“脑部损伤后的躁狂抑郁和纯粹的躁狂状态。”生物精神病学29.2(1991):149-158。
[16]Robinson,Robert G.等人。“脑损伤后躁狂症和抑郁症的比较:原因因素。”“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45.2”(1988年):第172-178页。
[17]莎泽、大卫和大卫·J·邦德。“继发于局灶性脑损伤的躁狂症:对理解双相情感障碍的功能神经解剖学的启示。”双相情感障碍18.3(2016):205-220。
[18]Diaz-Olatarrieta,Claudia等人。“多发性硬化症的神经精神表现。”神经精神病学和临床神经科学杂志11.1(1999):51-57。
[19]拉宾斯,彼得五世。“多发性硬化症的欣快感。”多发性硬化症的神经行为方面(1990):180-185。
[20]Mosley,Philip E.等人。“在丘脑深部刺激后停止刺激后持续躁狂症。”神经精神病学和临床神经科学杂志30.3(2018):246-249。
[21]Synofzik、Matthis、Thomas E.Schlaepfer和Joseph J.Fins。“幸福到什么程度才算太幸福呢?精神愉悦、神经伦理学和伏隔核深部脑刺激。“。Ajob神经科学3.1(2012):30-36。
[22]HAQ,Ihtsham大学等人。“强迫症患者的微笑和大笑诱导和术中对脑深部刺激反应的预测指标。”神经影像54(2011):S247-S255。
[23]安德森、凯伦·E和杰克·穆林斯。“与帕金森氏症脑深部刺激手术相关的行为改变。”当代神经学和神经科学报告3.4(2003):306-313。
[24]Greenberg,Benjamin D.等人。“深度脑刺激治疗高度抵抗型强迫症的三年结果。”神经精神药理学31.11(2006):2384-239。
[25]Kuhn,Jens等人。“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双侧伏隔核和内囊脑深部电刺激后出现短暂躁狂样发作。”神经调节:神经接口技术11.2(2008):128-131。
[26]Mosley,Philip E.等人。“丘脑深部刺激后停止刺激后躁狂症的持续性。”_神经精神病学和临床神经科学杂志_30.3。
[27]Chopra,Amit等人。“帕金森病患者丘脑底核深部电刺激后电压依赖性躁狂:1例报告。”生物精神病学70.2(2011):E5-E7。
[28]蔡新基等人。“难治性强迫症患者双侧腹侧被膜刺激后的低躁狂症。”生物精神病学68.2(2010):E7-E8。
[29]Springer,Utaka S.,et al.。“通过大脑深层刺激使微笑反应长期习惯化。”Neurocase 12.3(2006):191-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