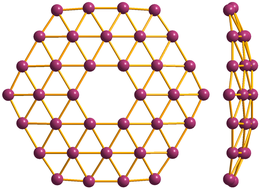超越曼特尔:历史小说
从弗朗西斯·斯普福德到莎拉·沃特斯,当代作家给历史小说带来了新的复杂性和趣味性。
读完“狼厅”和“带起身体”的读者可以毫无疑问地知道,希拉里·曼特尔的历史三部曲(请看第12页评论)的最后一卷“镜子与光明”将把他们带到哪里去。1540年7月28日,托马斯·克伦威尔将在塔山被斩首。但是,尽管我们知道克伦威尔要去哪里,他却不知道。曼特尔巧妙地利用了历史小说的宿命。它活跃在读者的知识和主人公的不确定性之间的鸿沟中。她的特殊成就是恢复了历史的临时性--运气、意外、惊喜。在曼特尔非凡的现在式叙述中,历史在我们面前展开。克伦威尔,这位小说家的代理人,是一位敏锐的人类分析家,但永远不能确定他们下一步会做什么。
这就是历史小说开始的地方。当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在1814年与韦弗利(Waverley)一起发明了这一体裁时,他的同名英雄是一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卷入了1745年雅各布派(Jacobite)对乔治二世的叛乱。(读者知道叛乱将会失败。)。19世纪,在司各特的觉醒下,历史小说具有很高的地位。现在很少有人阅读的作品-萨克雷的“亨利·埃斯蒙德·埃斯克的历史”,乔治·艾略特的“罗莫拉”,哈代的“小号大调”-曾经被认为是他们作者的最高成就。
到了下个世纪,历史小说已经没落了。现代主义使历史看起来像是逃避现实,小说家们对此避而不谈。随着20世纪中叶的临近,历史小说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但明显带有民粹主义色彩。大名鼎鼎的作家有乔治特·海耶(Georgette Heyer)和让·普莱迪(Jean Plaidy)(多产的埃莉诺·希伯特(Eleanor Hibbert)的笔名)。他们热爱他们的历史。特别是海耶,她的研究很严谨,她的摄政时期的小说有时会凝结着时代的细节。当今最成功、最多产的历史小说家菲利帕·格雷戈里同样为自己的准确性感到自豪。你可以对伯纳德·康威(Bernard Cornwe)的夏普系列或帕特里克·奥布赖恩(Patrick O‘Brian)的拿破仑航海小说说同样的话。
然而,有时历史背景并不意味着时期细节的积累,而是恰恰相反。一些小说家回到过去,以摆脱现代世界的干扰。这里的典范是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在他1964年的小说《尖顶》(The Spire)和《到地球尽头》(To The Ends Of The Earth)中,这是他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三部曲,故事发生在19世纪初一艘载着英国移民前往澳大利亚的。戈尔丁用想象中的过去来提炼人类的基本欲望和冲突。在尖顶,建造中世纪的英国大教堂尖顶是院长乔斯林的基督教使命,但他和那些为他工作的人被欲望或恐惧的黑暗灵魂所附身。
更近的一本书,如吉姆·克雷斯(Jim Crace)的《黑暗的田园收割》,故事发生在一个偏远的英国村庄,当时土地被强迫包围(日期尚不确定),属于同样的历史小说类别。在过去,社会秩序很难保护人们免受某种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的影响。一个可比的例子是萨曼莎·哈维(Samantha Harvey)2018年的小说《西风》(The Western Wind),它把我们带到了15世纪一个与世隔绝的萨默塞特村。它由一位聪明、疲惫的教区牧师讲述,要求我们想象宗教信仰在信仰的时代可能是什么样子。(这是许多近期历史小说的兴趣所在。)。行动发生在四天内,按相反的时间顺序进行,就好像时间在把我们拉回过去一样。有一个神秘的情节-村里最富有和最聪明的人失踪了,可能淹死了-但为了找到解决方案,我们回到了叙述者一直知道的事情上。它揭示的历史是一段社区暴力的历史。奇怪的是,背景和主人公与罗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2019年的新历史小说《第二次睡眠》有一些相似之处。虽然这是从宣布它的事件发生在1468年开始的,但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进入了一个遥远未来的黑暗时代,在经历了一些灾难之后,历史被重写了。这也是一部讲述一小群人可以攻击另一小群人的杀戮暴力的小说。
一部以几个世纪前为背景的小说拥有一种被剥夺的自由,而小说的自由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回到我们仍然有记录甚至记忆的时代。一些当代小说家显然认为历史距离是一种解放。安德鲁·米勒的“现在我们将完全自由”(2018年)以1809年为背景,讲述了一名饱受创伤的军官从半岛战争中归来的故事,他逃离了战争的恐怖,但却被一个复仇的恶棍追捕。小说乐趣的关键在于疏远的时代细节-我们探索摄政时期的枪店,参观纺织厂,或者对当时的外科医生的工作退缩。(米勒一直对早期不完整的医学和科学知识着迷)。然而,这些句子
近年来,戏谑和模仿悄悄进入了历史小说。一个巧妙的例子是弗朗西斯·斯普福德(Francis Spufford)的“金山”(Golden Hill),故事发生在17世纪40年代的纽约,本身就是对18世纪小说的模仿。斯普福德把他的书称为“约瑟夫·安德鲁斯或大卫·简朴的殖民地版”,分别由亨利和莎拉·菲尔丁的兄妹写于18世纪40年代的畅销小说。两者都雇佣了朴实无华的英雄,在一个狡猾的世界里释放出来。金山的主人公从伦敦来到这个危险的小镇,看起来是个无辜的人,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斯普福德用18世纪的场景娱乐我们:纸牌游戏,暴徒,监禁,决斗,戏剧(你可以在菲尔丁的小说中找到所有这些)。从崔斯特瑞姆·尚迪到“米德尔马契”,“金山”充满了戏仿的繁华,并不合时宜地改编了著名英语小说中的台词。它也有一种在最近的小说中并不陌生的后现代转折,在小说的结尾,我们发现了关于我们一直在读的叙事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真相。这本18世纪的模拟书对它是如何制作的提供了自己的描述。自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的“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ance中尉‘s Women)以来,历史小说就允许这种普遍的嬉戏。你可以在莎拉·沃特斯(Sarah Waters)的新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给天鹅绒和指匠小费”或查尔斯·帕利瑟(Charles Palliser)的小说中找到这一点。写遥远的过去意味着重写你正在重温的那个时期的小说。
曼特尔并不是唯一一个给历史小说带来新的文学复杂性的人。然而,她做了一些奇特的事情。她不仅给了我们环境的准确性(衣服,食物,举止),还给了我们挑剔的叙述精确性。几乎每一个被命名的角色都是我们所知道的存在于那个时间和地点的人。每一集都符合历史记录。学术历史学家可能不喜欢她对托马斯爵士的看法-一个在狼厅里冷酷的狂热分子-但他们与她争执不下,就像与一位专家同行争执一样。她使历史小说不再居高临下,但也开创了一个严酷的先例。这似乎是一种不可能效仿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