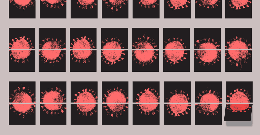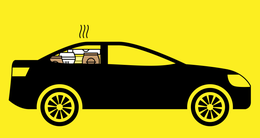“失去地球:我们几乎阻止了气候变化的十年”(2018)
纳撒尼尔·里奇(Nathaniel Rich)的这篇叙述是一部历史著作,讲述了从1979年到1989年的10年时间:人类首次广泛理解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危险的决定性的10年。与文本相辅相成的是一系列航拍照片和视频,这些照片和视频都是乔治·斯坦梅茨(George Steinmetz)在过去一年拍摄的。在普利策中心的支持下,这篇由两部分组成的文章基于18个月的报道和100多次采访。它追踪了一小群美国科学家、活动家和政治家为拉响警报和避免灾难所做的努力。对于许多读者来说,这将是一个启示-一个令人痛苦的启示-理解他们对问题的把握有多彻底,以及他们离解决问题有多近。杰克·西尔弗斯坦。
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温度已经上升了1摄氏度以上。巴黎气候协议-2016年地球日签署的不具约束力、不可强制执行、已经被忽视的条约-希望将变暖限制在2摄氏度以内。根据最近一项基于当前排放趋势的研究,成功的几率是20分之一。如果我们能奇迹般地将变暖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我们只需就世界热带珊瑚礁的灭绝、海平面上升几米和放弃波斯湾进行谈判。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称2摄氏度的变暖是“长期灾难的药方”。长期灾难现在是最好的情况。3摄氏度的变暖是短期灾难的药方:北极的森林和大多数沿海城市的损失。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前主任罗伯特·沃森(Robert Watson)认为,3摄氏度的变暖是现实中的最低要求。4摄氏度:欧洲处于永久干旱中;中国、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大片地区被沙漠宣称拥有主权;波利尼西亚被海洋吞没;科罗拉多河变薄为涓涓细流;美国西南部基本上不适合居住。全球变暖5摄氏度的前景促使一些世界领先的气候学家警告人类文明的终结。
知道我们本可以避免这一切,这是一种安慰还是一种诅咒?
因为在从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里,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解决气候危机。世界主要大国在几个签名的范围内就签署了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框架来减少碳排放-这比我们自那以后达成的协议要近得多。在那些年里,成功的条件是再有利不过的了。我们指责我们目前无所作为的障碍还没有出现。几乎没有什么能挡住我们的路--除了我们自己。
我们对全球变暖的几乎所有了解都是在1979年被理解的。到了那一年,自1957年以来收集的数据证实了20世纪之交之前就已经知道的事情:人类通过不分青红皂白地燃烧化石燃料改变了地球的大气。主要的科学问题得到了毋庸置疑的解决,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开始,人们的注意力从问题的诊断转向了对预测结果的改进。与弦论和基因工程相比,“温室效应”--一个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比喻--已经是古老的历史了,在“生物学导论”的任何教科书中都有描述。基础科学也不是特别复杂。这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公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越多,地球就越暖和。每年,人类通过燃烧煤、石油和天然气,向大气中排放越来越多的令人作呕的二氧化碳。
我们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呢?今天一个常见的恶人是化石燃料行业,近几十年来,该行业一直致力于扮演漫画书中虚张声势的恶棍角色。气候文献的一个完整的子领域记录了行业游说者的阴谋,科学家的腐败,以及宣传活动,即使在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放弃了否认的愚蠢表演很久之后,这些宣传活动至今仍在继续贬低政治辩论。但是,直到1989年底,联合起来迷惑公众的努力才真正开始。在过去的十年里,包括埃克森美孚和壳牌在内的一些最大的石油公司真诚地努力了解危机的范围,并努力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案。
共和党也不能受到指责。今天,只有42%的共和党人知道“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全球变暖正在发生”,而且这一比例正在下降。但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知名的共和党人加入了民主党人的行列,认为气候问题是一个罕见的政治赢家:无党派的,风险最高的。呼吁采取紧急、立即和影响深远的气候政策的人包括参议员约翰·查菲(John Chafee)、罗伯特·斯塔福德(Robert Stafford)和大卫·杜伦伯格(David Durenberger),EPA局长威廉·K·赖利(William K.Reilly),以及在竞选总统期间
广泛的国际共识已经确定了一个解决方案:一项遏制碳排放的全球条约。早在1979年2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届世界气候大会上,来自50个国家的科学家一致认为“迫切需要”采取行动,这一想法就开始凝聚在一起。四个月后,在东京举行的七国集团(G7)会议上,世界上最富有的七个国家的领导人签署了一份声明,决心减少碳排放。十年后,第一次批准具有约束力的条约框架的重大外交会议在荷兰召开。来自6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目标是在大约一年后举行一次全球峰会。在科学家和世界领导人中,观点是一致的:必须采取行动,美国需要发挥带头作用。但事实并非如此。
气候变化传奇的开篇篇章已经结束。在那一章--称之为担忧--我们确定了威胁及其后果。我们带着越来越大的紧迫感和自欺欺人的心情,谈到了战胜重重困难的前景。但我们没有认真考虑失败的前景。我们理解失败对全球气温、海岸线、农业产量、移民模式和世界经济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没有允许自己理解失败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它将如何改变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如何记忆过去,如何想象未来?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这些问题将成为气候变化第二章的主题--称之为“清算”。如果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有机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了解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困境。
作为一个文明,我们如此接近于打破我们与化石燃料的自杀协定,这要归功于一小撮人的努力,其中包括一名过度活跃的游说者和一名朴实的大气物理学家,他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试图警告人类即将发生的事情。他们冒着职业生涯的风险进行了一场痛苦的、不断升级的运动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通过科学报告,后来是通过传统的政治说服途径,最后是通过公开羞辱的策略。他们的努力精明、热情、有力。但他们失败了。接下来是他们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
向雷夫·波美朗斯提出的第一个建议是,人类正在破坏自身生存所必需的条件,这一建议出现在政府出版物EPA-600/7-78-019的第66页。这是一份关于煤炭的技术报告,封面为煤黑色,印有米色字母--波美朗斯位于国会山联排别墅一楼、没有窗户的办公室周围堆满了许多这样的报告,其中一份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70年代末,这里曾是“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在华盛顿的总部。在关于环境监管的一章的最后一段中,煤炭报告的作者们指出,在二三十年内,化石燃料的持续使用可能会给全球大气带来“重大的、破坏性的”变化。
波美朗斯吃惊地停顿了一下,听了那段孤儿的话。它似乎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他重读了一遍。这对他来说毫无意义。波美兰斯不是一名科学家;他11年前从康奈尔大学毕业,获得了历史学学位。他有一个营养不良的博士生在黎明时分从书架上走出来的样子。他戴着角框眼镜,留着浓密的胡子,嘴角不赞成地枯萎了,尽管他的特征是不必要的身高,6英尺4英寸,这似乎让他很尴尬;他弯下腰来容纳他的对话者。他有一张活跃的脸,容易露出灿烂甚至疯狂的笑容,但却很镇定,就像他读煤炭小册子时那样,它显示出他的担忧。他在技术报告上苦苦挣扎。他以历史学家的能力继续进行:小心翼翼,仔细研究原始材料,解读字里行间的意思。当失败时,他打了电话,通常是给报告的作者,他们往往会惊讶地接到他的电话。他发现,科学家没有回答政治说客提问的习惯。他们没有思考政治的习惯。
波梅兰斯对煤炭报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烧煤、烧油、烧天然气会招致全球性灾难,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呢?如果说华盛顿的任何人--如果是美国的任何人--应该意识到这样的危险,那就是波美朗斯。作为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的副立法主任,波美朗斯是美国人脉最广的环保活动人士之一。地球之友是大卫·布劳尔(David Brower)十年前从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辞职后帮助创建的狡猾、好斗的非营利组织。他在德克森参议院办公大楼的大厅里像在地球日集会上一样容易被接受,这可能与他是一名
阿格尔指出了一篇关于一位名叫戈登·麦克唐纳(Gordon MacDonald)的著名地球物理学家的文章,他当时正与他所属的神秘精英科学家小圈子贾森(Jasons)一起进行一项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波美兰斯没有听说过麦克唐纳,但他对贾森夫妇了如指掌。他们就像那些力量互补的超级英雄团队中的一员,在银河系危机时期联合起来。包括中央情报局(CIA)在内的联邦机构将他们召集在一起,为国家安全问题设计科学解决方案:如何探测来袭的导弹;如何预测核弹的尘埃;如何开发非常规武器,如鼠疫出没的老鼠。在五角大楼的文件公布之前,贾森夫妇的活动一直是一个秘密,文件揭露了他们计划在胡志明小径上安装运动传感器,向轰炸机发出信号。在随之而来的愤怒之后-抗议者放火焚烧了麦克唐纳的车库-贾森夫妇开始将他们的力量用于和平,而不是战争。
麦克唐纳认为,有一个紧迫的问题需要他们关注,因为人类文明面临着生存危机。麦克唐纳在担任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科学顾问期间于196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如何破坏环境”(How To Wreck The Environment)中预测,在不久的将来,“核武器将被有效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成为环境灾难的武器。”他认为,最具潜在破坏性的此类武器之一是我们每次呼吸时呼出的气体:二氧化碳。通过大幅增加碳排放,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可能会改变天气模式,造成饥荒、干旱和经济崩溃。
在那之后的十年里,麦克唐纳看到人类开始认真地将天气武器化,这让他感到震惊-不是出于恶意,而是无意中。1977年春天和1978年夏天,贾森夫妇开会决定,一旦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比工业革命前的水平翻了一番,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个随意的里程碑,翻了一番,但也是一个有用的里程碑,因为它的必然性是毋庸置疑的;到2035年,门槛很可能会被突破。贾森夫妇在提交给能源部的报告“大气二氧化碳对气候的长期影响”(The Long-Term Impact Of Climate)中,语气低调,只会强化其噩梦般的发现:全球气温将平均上升2至3摄氏度;沙尘暴条件将“威胁北美、亚洲和非洲的大片地区”;饮用水和农业生产的可获得性将下降,引发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移民。然而,“也许最不祥的特征”是气候变化对两极的影响。即使是轻微的变暖,也“可能导致”西南极冰盖的“迅速融化”。冰盖所含的水足以使海平面上升16英尺。
贾森夫妇将这份报告发送给了美国国内外的数十名科学家、国家煤炭协会(National Coal Association)和电力研究所(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等行业组织,以及政府内部的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商务部、EPA、NASA、五角大楼、NSA、军方各部门、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和白宫。
波美朗斯在震惊的状态下读到了关于大气危机的报道,这一震惊迅速激起了愤怒。“这,”他告诉贝齐·阿格尔,“就是整根香蕉。”
戈登·麦克唐纳(Gordon MacDonald)曾在联邦资助的米特公司(Mitre Corporation)工作,这是一家与政府各机构合作的智囊团。他的头衔是高级研究分析师,这是国家情报界高级科学顾问的另一种说法。打了一个电话后,前越战抗议者和良心反对者波梅兰斯在环城公路上驱车几英里,来到一群匿名的白色办公楼前,这些办公楼更像是一家地区性银行的总部,而不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太阳能神经丛。他被带进了一位健壮、说话柔和的男子的办公室,他穿着结实的角质边框,伸出一只手,就像熊的爪子一样。
“我很高兴你对此感兴趣,”麦克唐纳一边打量着这位年轻的活动家一边说。
“我怎么可能不是呢?”波美朗斯说。“怎么会有人不是呢?”
麦克唐纳解释说,他第一次研究二氧化碳问题是在波美朗斯差不多大的时候--1961年,当时他是约翰·F·肯尼迪的顾问。波美朗斯拼凑出麦克唐纳在年轻时是个神童:20多岁时,他为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提供太空探索方面的建议;32岁时,他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院士;40岁时,他被任命为首届环境质量委员会(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成员,在那里他就燃煤对环境的危害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提供建议。他一直在监测二氧化碳问题,越来越警惕。
麦克唐纳讲了两个小时。波美朗斯大吃一惊。“如果我在国会山与一些人举行简报会,”他问麦克唐纳,“你会告诉他们你刚刚告诉我的事情吗?”
戈登和雷夫的二氧化碳路演就这样开始了。从1979年春天开始,波美兰斯安排了与EPA、国家安全委员会、“纽约时报”、环境质量委员会和能源部的非正式简报会。波美兰斯了解到,在麦克唐纳的敦促下,能源部在两年前成立了二氧化碳影响办公室(Office Of CO2 Effects)。男人们习惯了日常生活,麦克唐纳解释了科学,波美朗斯加了感叹号。他们惊讶地发现,很少有高级官员熟悉贾森夫妇的发现,更不用说了解全球变暖的后果了。最后,两人在联邦层级中一路向上爬后,去见了总统的首席科学家弗兰克·普莱斯(Frank Press)。
新闻媒体的办公室位于旧行政办公楼,这座矗立在白宫地面上的花岗岩堡垒距离白宫西翼只有几步之遥。出于对麦克唐纳的尊重,普赖斯召集了总统科技政策办公室的所有高级工作人员参加会议-官员们就能源和国家安全的每一个关键问题进行了咨询。波美兰斯原本预计的又一次非正式简报,具有高级别国家安全会议的性质。他决定让麦克唐纳负责所有的谈话。没有必要向普赖斯和他的副手们强调,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国家意义的问题。办公室里平静的气氛告诉他,这一点已经被理解了。
为了解释二氧化碳问题对未来意味着什么,麦克唐纳会从一个多世纪前的约翰·廷德尔(John Tyndall)开始他的演讲。约翰·廷德尔是一位爱尔兰物理学家,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工作的早期拥护者,在被妻子意外毒死后去世。1859年,廷德尔发现二氧化碳吸收热量,大气成分的变化会造成气候变化。这些发现启发了瑞典化学家、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斯万特·阿雷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在1896年推断,煤炭和石油的燃烧可能会提高全球气温。阿雷尼乌斯计算出,这种变暖将在几个世纪后变得明显,或者更早,如果消耗化石燃料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