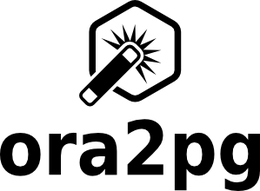我们不安的先知
2020年3月,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封信,信中据称是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在西班牙流感爆发期间于1920年在法国南部被隔离”,并迅速在社交媒体上疯传。开篇描述了“晴朗沉闷的一天,就像一颗沉闷的星星挂在篮子里”,然后叹了口气,说这是。
令人心酸的避开公共场所。甚至是酒吧,就像我告诉海明威的那样,但他一拳打在我的肚子上,我问他有没有洗手。他没有。他更否认这一点。为什么,他认为这种病毒只是一种流感。
这封信带有可疑的话题和故意的拙劣,在2020年的头几个月恶搞了大流行的言论。它的作者甚至认为它是一种恶搞,但这个谎言在真相穿上靴子之前就已经传遍了世界,就像马克·吐温从来没有说过的那样。
事实上,菲茨杰拉德在他的写作中几乎没有提到西班牙流感,就像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尽管它造成的美国人死亡人数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他自己也感染了它。他的情况很轻微,1919年在流感的前三波中的最后一波感染;他让安东尼·帕奇在《美丽与诅咒》中忍受了一场类似的比赛,三句话都被判了。但是,数以千计的人屈服于它所嘲弄的假设: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总是为咆哮的20年代代言,历史是循环的,这一点对成千上万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笑话。
20世纪20年代持久的神秘感给它的百年历史增添了一种独特的怀旧魅力。尽管20世纪20年代的万神殿中还有其他传奇人物-海明威在巴黎咖啡馆喝着上好的卡奥尔葡萄酒,多萝西·帕克在阿尔冈昆酒店胡言乱语地品尝杜松子酒,格特鲁德·斯坦(Gertrude Stein)在弗洛鲁斯街分发卷心和eau-de-vie-尽管他仍然是万神殿的使者,在某种程度上会让他既感到不安,又感到高兴。特别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它有着黄色的鸡尾酒音乐、蓝色的花园和比手指碗还大的香槟酒杯,它代表了我们对爵士乐时代的集体看法。在世界各地,盖茨比主题的除夕夜晚会迎来了2020年:从伦敦到墨尔本,从亚特兰大到旧金山,各家豪宅闪耀着光芒,迎接一千名宾客。
但是,这幅讽刺菲茨杰拉德轻浮、狂想曲的漫画掩盖了他讽刺的令人振奋的酸楚和他智慧的冷静之眼。菲茨杰拉德描绘现代美国的迷人词汇仍然蒙蔽了我们,让我们看不到他对现代美国的评判是多么严厉。“那是一个讽刺的时代,”他写道,但我们认为,这位既代表了爵士乐时代,又认为讽刺是其本质特征的作家自己从未使用过讽刺。菲茨杰拉德冷嘲热讽的幽默和不安--他后来写道,“生活本质上是一场骗局,它的条件是失败的”--赋予了他最好的作品道德现实主义和庄严,为他的散文飞行奠定了基础。所有那些参加新年派对的人似乎都忘了,狂欢的结局是盖茨比死在游泳池里,一个肮脏的字眼潦草地写在他荒谬的房子的门廊上。盖茨比是一个关于误读历史后果的警示故事,而它的政党则描绘了一个失控的社会。爵士乐时代在这部小说中的结局并不好,这本应该让它听起来很有趣。
然而,它的开始也不是很好。我们应该重新审视1920年,不是因为百年诞辰具有神奇的特性,而是因为菲茨杰拉德极其灵敏的内耳帮助他在几乎所有人之前就意识到了美国开始失去平衡,并将其眩晕称为“爵士乐”。爵士乐与俚语“pep”有关,其最早的记录用来表示活泼的用法和音乐一样频繁。1爵士乐很快在语义上变得如此反复无常,到了1915年,它本身就表示波动性;不久,它就代表着暴政。不可预测性就是爵士乐,正如他们所说:当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引力定律时,据说他发现了“爵士乐分子”。
菲茨杰拉德在他1931年的文章“爵士乐时代的回响”(Echeles Of The Jazz Age)中,讲述了1929年底刚刚“一飞冲天”的十年。他回忆说,他之所以取得早期的成功,仅仅是因为他告诉同时代的人,“他和他们一样觉得,必须用战争中储存的、没有花掉的所有紧张能量来做一些事情。”他补充说,爵士乐就是这种能量;它“与紧张刺激的状态联系在一起,与战线后面的大城市没有什么不同。”多亏了一场全球大流行,读者们出人意料地一下子进入了我们这个焦虑的时代,也许突然之间就能更好地理解这种状态。1920年的爵士乐精神并不是无忧无虑的:它是险些失手的歇斯底里,是对幸存灾难的过度反应,是一个因为不知道还能去哪里而变得疯狂的社会。
1920年初,没有人听说过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直到1924年左右,“咆哮的二十几岁”这个标签才被贴上(最初它描述的是年轻人在安顿下来之前享受着“咆哮的二十几岁”)。但即使在当时,美国人也认为他们正在进入一个“爵士乐时代”。爵士乐的时代“像流感一样”蔓延,“一种音乐病毒”从堪萨斯州(“这个爵士乐的狂野时代”)传播到密苏里州(“这个爵士乐和令人厌恶的时代”)再到阿拉巴马州(“我们生活在爵士乐的时代”)。内布拉斯加州的一篇社论“在这个爵士乐时代”得到了当地老式拼写比赛的安慰,暗示“年轻一代终究不会堕落”。费城的一位部长开始哀叹:美国人生活在“爵士乐时代”,“一个一切都在发展的时代,”他补充说,“气氛中弥漫着爵士乐,甚至道德结构也充满爵士乐。”保守的美国白人发现爵士乐极具威胁性,尤其是因为爵士乐带有野性、暴力和放任的种族色彩:他们称之为“丛林爵士乐”。在菲茨杰拉德的记忆中,爵士乐-可能与“jism”同源,尽管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意思是性优先,甚至在它意味着音乐之前。2个。
我们知道菲茨杰拉德将这种“神经刺激状态”归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我们没有领会他的观点:战争“没有消耗”美国的神经能量(他写道,他的这一代人“预见到了死亡,并得到了缓刑”),而这个国家则在努力适应。与此同时,流感大流行刚刚导致近70万美国人死亡,直到1919年秋季才平息下来。报纸报道了1920年头几个月的统计数据:“一周内23个州新增了27,000例流感病例”,一个紧张的标题宣布。在经历了三波疫情之后,每个人都在寻找第四波疫情的迹象。与此同时,国会通过了第十八和第十九修正案,这些修正案将于1920年生效,并在不同的政治方向上给国家带来转折,一个走向本土主义威权主义(禁止),另一个走向自由多元化(妇女选举权)。
繁荣也还没有开始:1920年初,美国进入了持续18个月的严重通缩衰退。1919年,劳工和种族骚乱,以及政治不确定性,引发了骚乱和所谓的红色之夏,导致了一场严厉的镇压,最终以1920年1月的帕尔默突袭告终,在那次行动中,至少有3000人被捕,其中几乎所有人都是移民,被控为左翼分子。赫斯特报纸头版的标题为“突袭驱使‘红色’掩护‘”的文章报道说,数百名“外星人”和“激进分子”被草率地驱逐出境,报头上写着“美国优先!”这句口号主导了1916年的总统竞选,帮助说服美国投票反对加入国际联盟,并一直很受欢迎,以至于沃伦·G·哈丁(Warren G.Harding)在1920年11月骑着它入主白宫。
投票支持“美国优先”的团体与支持禁酒令的团体大体上是重叠的:本土主义的白人新教美国人试图将他们认为可疑的外国、城市和颓废的习俗定为刑事犯罪,特别是将酒精与新爱尔兰、意大利和德国移民联系在一起。哈莱姆文艺复兴即将蓬勃发展,但三K党正在集结,准备将美国黑人夷为平地。美国的命运不再显而易见,引发了人们对其将采取何种形式的普遍焦虑。爵士乐对所有这些不安都说了一句话。
正当“爵士乐时代”的想法传遍全国时,一位24岁的雄心勃勃的作家正大踏步前进。在191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菲茨杰拉德一直在努力卖出任何故事-但随着这十年的过去,他的财富也是如此。美国最受欢迎的杂志“周六晚报”(The星期六Evening Post)开始购买他的小说,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时尚引领者H·L·门肯(H.L.Mencken)和乔治·让·内森(George Jean Nathan)主编的文学期刊“聪明集”(The Smart Set)也开始购买他的小说。1919年秋至1920年夏,菲茨杰拉德在全国知名媒体发表了16篇故事,其中3篇被好莱坞抢购一空,并在当年内变成了无声的“图片化”发行;其中大部分讽刺现代美国。他最早的作品之一,1920年2月出版的“达里姆普出了问题”,讽刺了美国的成功故事,讲述了一个入室窃贼成为州参议员的故事。就像他之后的杰伊·盖茨比(Jay Gatsby)一样,达里姆普尔是一名老兵,在战后的美国,当被剥夺机会时,他会转向犯罪。菲茨杰拉德笔下的大多数年轻主人公都嘲笑传统道德;同年2月出版的“本笃”(Benediction)中的女主人公思考通奸问题,并与身为僧侣的哥哥讨论避孕问题,告诉他“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一切”。这些都是大胆的故事,挑衅地问美国是否准备好了爵士乐。
那个问题得到了公关人员的回答。
事实上,阿莫里和菲茨杰拉德本人一样,是教科书上的香槟社会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情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有限的,尽管他总是认同“农民对富人的阴燃仇恨”。菲茨杰拉德看到了金钱的作用,但从未将其与意义混为一谈。“即使在美国,金钱也不是唯一能激发出男人身上最好的东西的刺激因素,”阿莫里坚持说。正如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所写的那样,他对社会主义的半心半意的拥护是对“过时的制度”的一种“无限期反抗的姿态”。小说以一夜成名的台词结束,主人公调查了“新一代比上一代更专注于对贫穷的恐惧和对成功的崇拜;长大后发现所有的神都死了,所有的战争都打了,人类的所有信仰都动摇了。”菲茨杰拉德找到了他的主题:现代美国的道德困惑。
然而,菲茨杰拉德的“第一封大信”并不是寄到天堂的这一边;他说,这封信是在他收到“成百上千封关于一个女孩剪短发的故事的信”时寄来的。虽然舞蹈家艾琳·卡塞尔(Irene Castle)帮助推广了短发,随着女性加入战争,短发的吸引力也在蔓延,但当1920年5月“伯妮丝·波布斯她的头发”(BerniceBobs Her Hair)出现时,短发在美国小镇仍然是一种叛逆的选择。这个故事讽刺地颠倒了“小妇人”中的场景,乔牺牲了她的“一个美丽”,高贵地剪了头发,以帮助支付她母亲拯救生病父亲的路费。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现代女孩断然拒绝这种维多利亚时代的父权孝道理想。“噢,请不要引用‘小妇人’!”人气颇高的玛乔丽对她老派的表妹伯妮丝大发雷霆。“那是不合时宜的…。。什么样的现代女孩能像那些空虚的女性那样生活?“。奥尔科特笔下的小女人们必须学到的核心一课是压抑她们的愤怒,而“伯妮丝”则是关于释放女性的愤怒。玛乔丽和柏妮丝不是忠诚的姐妹,而是竞争对手;当柏妮丝的受欢迎程度威胁到让玛乔丽黯然失色时,她强迫柏妮斯公开表示打算剪短她的头发,称她是虚张声势。公开羞辱的伯妮斯进行了报复,在玛乔丽睡觉时偷偷剪掉了她长长的金发,然后狂笑着跑到了深夜。
“伯妮丝·波布斯她的头发”被认为是一个关于女性自恋的故事,被认为是一个不屑一顾的故事,但伯妮斯勇敢面对公众挑战的决定中蕴含着勇气。玛乔丽的挑战是一次挑战,伯妮斯遇到了“她体育精神的最高考验”。菲茨杰拉德向我们展示了花花公子的诞生:害羞,通常是虚荣的,但却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和信守诺言的女人。这是简·奥斯汀拿着刀-或剪刀-出来,一部礼仪喜剧,变成了一场决斗。菲茨杰拉德写道,伯妮斯在故事的结尾“剥了”马乔里的头皮,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发展了一个早期的暗示,即伯妮斯可能有美洲原住民的血统。今天,这一细节让读者感到不安,但对于菲茨杰拉德这一代人来说,这是一种标准的形象,即野蛮被讽刺地应用于被宠坏的初出茅庐的人。他的观点是,柏妮丝发现她身上有一种凶猛和自由的气质。
在等待“天堂的这一边”出版期间,菲茨杰拉德完成了“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战后故事”,可能是从一部被遗弃的第二部小说中抢救出来的。它冗长,杂乱无章,相当冷酷;没有一家商业杂志会接受它,但Smart Set在1920年7月出版了它。他说,许多学者认为菲茨杰拉德的第一部杰作“五月天”是根据1919年春天“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三件事”改编的。“在生活中,他们是没有关系的,”他在1922年修改故事时解释说,“除了开启爵士时代的那个春天的普遍歇斯底里,”但在菲茨杰拉德的想象中,他们融合成了一个故事。对他来说,是1919年五一暴乱“开启”了爵士乐时代:不是聚会、音乐、浴缸杜松子酒或繁荣的股市,而是阶级冲突的暴力。
1919年初,菲茨杰拉德住在纽约,身无分文,濒临绝望,担心职业失败,而他的富有的大学朋友们则聚集在镀金时代精英的专属餐厅德尔莫尼科(Delmonico)参加奢华的交谊会,或者参加“郁郁葱葱、流畅的花园派对”。菲茨杰拉德后来回忆说,即使他“在比尔特莫尔酒吧和普林斯顿人喝醉了”,“我的另一种生活也总是困扰着我”,“我破旧的西装,我的贫穷。”那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六,菲茨杰拉德和一位有钱的朋友在德尔莫尼科百货公司(Delmonico‘s)参加舞会时喝得酩酊大醉。他们从衣帽间把牌子挂在脖子上,介绍对方为“进来先生”和“外出先生”,然后去了第59街的Child’s通宵餐厅,菲茨杰拉德试图在那里解释说,哥伦布圆环并不是真的弯曲,只是因为他喝醉了。他们在Biltmore吃完早餐,周日早上在惊慌失措的教堂常客面前砸碎了香槟酒瓶。
尽管菲茨杰拉德享受着这种愚蠢的放荡,
在Delmonico‘s,有钱的年轻人“像有尊严的黑飞蛾”在香水初次登台的女郎中间飞来飞去;一位有抱负的艺术家因酗酒和肮脏的风流韵事毁了自己,希望他的有钱朋友能救他;两名士兵偷偷从街上溜进来,试图乞讨一些酒。外面,暴徒们哈哈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