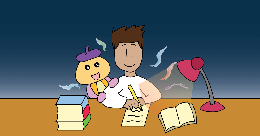创意的兴起与崛起
创造力没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牛津英语词典”只记录了这个词在17世纪的一次用法,而且是宗教用法:“在创造中,我们有上帝和他的创造力。”然后,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几乎什么都没有-哲学家A·N·怀特黑德(AN Whitehead)的准宗教祈祷。因此,创造力,被认为是属于个人的一种力量--无论是神圣的还是凡人的--不会永远回去。形容词“创造性”(创造性的、富有想象力的、有独创性的想法)也没有,尽管这个词在现代早期出现的频率要比名词高得多。上帝是造物主,在17世纪和18世纪,创造力,就像很少使用的“创造力”一样,被理解为神圣的。想象艺术中世俗创造力的概念直到浪漫主义时代才出现,当时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对画家兼评论家本杰明·海登说:“Creative Art…。需要思想和心灵的服务。
这一切都在20世纪中叶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俗化的创造力概念突显出来。Google Ngram的图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急剧向上弯曲,并持续上升到今天。但直到1970年,实用主义作家虽然承认创造力是有价值的,需要鼓励,但还是反思了这个概念的新颖性,指出早在几十年前,一些标准词典就没有这个概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直接后果之前,创造力的历史似乎缺乏它的对象-这个词在流通中并不多。这一点不一定要迂腐。你可能会说,我们所说的创造力能力后来被其他概念有力地挑出来了,比如天才,或者原创性,或者生产力,甚至智力-或者任何人们认为能够让人们思考被认为是新的和有价值的想法的能力。在战后时期,许多评论家确实对新兴创造力和其他长期认可的智力之间的假设差异感到疑惑。20世纪中叶的创造力纠缠在这些预先存在的概念中,但其定义和应用的环境是新的。
考虑到这些定义上的考虑,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人们对原创性思维和生产性思维等分散范畴的性质和环境的看法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越来越多地,这些类别被重新指定为平凡的,作为普通能力的变化和表现,甚至可能属于一个实体而不是一个特殊而神秘的天赋个体的能力。
天才的概念--真正出类拔萃的心智能力--从世俗的角度或作为上级送来的莫名其妙的礼物--仍然存在,但对于那些做出了非常创新的事情、有着非常新的想法的人来说,它变得既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也是谨慎的,他们鄙视天才的称谓,否认自己拥有独特的智力禀赋。你应该明白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在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物种起源”(1859)出版的同一年,苏格兰作家塞缪尔·斯迈尔斯的一本名为“自助”的书卖出了更多的书。自助是企业家通过辛勤工作获得成功的一种指南,斯迈尔斯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天才和有纪律的应用在创造新知识方面的相对重要性的看法。斯迈尔斯写道,天才是存在的,但它的作用被系统地夸大了:“命运通常站在勤劳的人一边”;需要的是“常识、关注、应用和毅力”。
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 Ope)告诉我们,流利的小说写作只不过是每一刻钟250字,每天早餐前加起来就是2500字,这与天才保持着距离。当达尔文本人被问到他是否有什么特殊才能时,他回答说他没有,只是他非常有条不紊。他说,我有相当一部分的发明创造和常识或判断力,这是每个相当成功的律师或医生都必须具备的,但我相信不会比这更高了。
这些民主情绪正迅速走向常态。1854年,法国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驳斥了科学原创性是一种特殊礼物的观点:“命运眷顾有准备的人。”在正确的地方,经过正确的培训,你也可以有重要的新想法。大约在1903年左右,美国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给了我们一个至今仍很流行的公式,即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而20世纪最著名的科学思想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认为,把神秘的天赋归因于天才在智力和道德上都是错误的。
到了20世纪初,科学上的原创工作无论如何都被搬出了曾经虔诚的象牙塔修道院,进入了商业世界,这也鼓励了人们对相关智力的情绪。首先,伟大的德国-然后是英国和美国-化学、制药和电气公司都在投资于应用和基础研究,雇佣了大量受过学术培训的科学家,他们的理念是创新是商业成功的关键,科学理所当然地属于商业组织。旧的盈利方式是垄断控制,新的方式据说是不断创新。
当时更广泛的文化认为,教授和利润的结合是一个奇怪的组合-学术上的古怪和对自治的要求可能会与公司规范发生冲突-而且经过深思熟虑和实际的思考,安排环境将使公司能够获得创新人员,允许他们做创新事情,并提高他们的创新产出,同时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在正确的创新上,那些可能产生企业利润的创新。
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关的类别仍然不是创造力,而是一组松散联系的能力,有时被指定为原创性,有时被指定为生产力,更多的时候没有特别阐述或定义。无论这些能力是什么,它们都是科学工作者受雇的结果背后的原因。雇主倾向于从具体的结果中推断出能力。然而,有一个关于工人能力的概念,公司经理们希望将他们自己与之分开-那就是天才。不同的公司对科学工作者的能力有不同的看法,但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和伊士曼·柯达(Eastman Kodak)等公司的新研究实验室出现的一种回应是,创造性和生产性工作与雇佣笨拙的天才无关,而是要找到让拥有平凡天赋的人取得非凡成就的组织形式。
1920年,伊士曼柯达(Eastman Kodak)一位深思熟虑的工业研究主管承认了天才的现实和价值,尽管他怀疑任何一家公司都不能指望获得足够的如此杰出的人才供应。不要紧:训练有素、积极进取的科学工作者可以做出有价值的贡献,即使他们“完全不受任何可能被视为天才之火”的影响。在本世纪中叶,企业和官僚雇主对于培养天才的组织困难是否值得忍受,意见不一;一些人坚持认为值得;另一些人认为,天才造成的破坏代价太大,无法付出;还有一些人认为,一个由中等能力的人组成的组织得当的团队可能构成“一个非常好的天才替代品”。
组织的设计应该是吸引来自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专注于一个共同的项目;让他们在与本国学术学科保持联系的同时保持交谈;让他们专注于与商业相关的项目,同时允许他们有足够的自由“凝视窗外”和思考“蓝天”思想。如果你想要利润,那么-这是被广泛承认的-你付出的一个代价是相当大的知识自由,允许科学工作者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至少在某些时候是这样。每周一天免费思想的概念并不是谷歌最近发明的;它几乎永远存在于工业研究实验室,它的合理性总是坚定不移的。
战后,曼哈顿计划经常被誉为有效组织所能取得的成就的光辉典范。诚然,制造核弹的许多科学家被认为是天才,但许多人不是,大量的设计、测试工作和同位素制造是由具有普通资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军团完成的。J·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因其管理天才和科学才华而备受赞誉,尽管洛斯阿拉莫斯和同位素生产基地的大部分组织结构都是从西屋电气(Westinghouse Electric)等公司改编而来的。曼哈顿计划证明了,毕竟,你可以“放牧猫”,组织天才,实现新的和重要的事情-任何单独的天才或随机的天才集合都做不到的事情。
原子弹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冷战的开始。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创造力得到了后来评论家的大量赞誉,但并不是在紧随其后的情况下:“创造力”这个词并没有出现在1945年关于该项目的官方史密斯报告(Smyth Report)中。天才概念的唯一引用就是通货紧缩
“创造力”不能再留给天才的偶然出现,也不能留在完全神秘和不可触及的领域。男人必须能够为此做些什么;创造力必须是许多人的财产;它必须是可识别的东西;它必须服从于获得更多创造力的努力。
有人建议科学人力委员会安排科学人员的持续供应,并以增强“创造性工作”的方式组织他们。数量很重要,科学人员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确定有潜力成为生产性技术工人的年轻人群体。质量也非常重要:在拥有适当智力的人中,确定他们中的哪些人可能会变得“有创造力”是很有用的。这种心理能力可以被识别出来,从其他心理特征中分离出来,进行测量吗?
正是这种能力越来越多地被称为创造力,有许多消费者希望对创造力进行稳定和可靠的表征,并寻求对其进行评估的方法。关注技术人员供应的政府部门--无论是军方还是文职部门--想要更少的机会,更可靠的方式来识别各种人才;军方想要的是发现能够主动、即兴发挥和想象新战争形式的军官的技术-美国军事战略家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在肯尼迪时代鼓励人们考虑战斗并在热核战争中幸存下来:“想一想不可想象的事情”。企业和政府官僚机构想要有能力找到适应能力强的管理者;教育机构想要选择富有想象力的教师;新成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想要更好的方法来决定哪些拨款申请者最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当然,与艺术和人文有关的机构也想要类似的东西,尽管这些不太实用的担忧在创意的冷战历史上并不像战争、利润和技术知识的产生那样重要。
当然,定义和测量心智能力并将结果提供给机构客户的专业人类科学实践在战前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是,就创造力而言,新的军事和企业需求刺激了新的学术供给,而这种自给自足的新学术供给鼓励了更多的需求。1950年,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哀叹,当时的专业文学中只有一小部分与创造力有关;在这十年里,一场自觉的风格和精心支持的“创造力运动”发展起来。出版了书目,赋予了该领域一个独特的身份;召开了会议;创办了期刊;在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和商业公司举办了关于“创意工程”的有影响力的研讨会,询问什么是创意,为什么它很重要,什么因素影响它,以及应该如何部署它;美军所有军种的人事部门都密切参与了冷战创意研究。
提供了创造力的定义;设计了测试;在教育、招聘、选拔、晋升和奖励的过程中将测试做法制度化。创造力日益成为创造力测验的特定心理能力。对于特定的定义是否正确,或者特定的测试是否可靠地确定了所需的能力,从来没有压倒性的共识,但人们的情绪围绕着创造力和发散思维概念之间的实质性联系而定。人们说,如果一个人能够扩展,想象出一系列可能的问题答案,并偏离稳定和被接受的智慧,而聚合思维则顺畅地朝着“唯一正确的答案”前进,那么他们就是有创造力的。例如,当被问及一把椅子有多少用途时,发散的思想家可能会想出很多种;趋同的思想家只说你坐在上面。趋同思维和发散思维是对立的,就像从众和创造是对立的一样。
在促进群体团结的能力和扰乱集体认识、判断和行动方式的能力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不仅来自于识别智力的实际方法,也来自于嵌入了创造力和一致性的道德和意识形态领域。对于创造性运动中的人类科学专家和他们的客户来说,从众不仅对科学不利,而且在道德上也是有害的;创造力对科学有利,在道德上也是有益的。
历史学家杰米·科恩-科尔(Jamie Cohen-Cole)描述了冷战时期围绕着所谓的创造力和从众之间的冲突的道德和工具情感的结合。创意
从1955年到1971年,NSF在犹他大学赞助了一系列关于科学创造力的会议,部分资金也来自空军。他们由创意运动中的领先心理学家主持,美国教育、政府、军事和商业(包括通用电气、波音、陶氏化学公司、Aerojet-General和埃索研究中心)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所有从事创意研究及其应用的人都在那里。在1959年6月举行的犹他州第三次会议上,年轻的哈佛大学物理学家出身的历史学家托马斯·S·库恩(Thomas S Kuhn)出席了会议。他对会议过程的贡献始于一种困惑的表情:他认为自己也关心创造力,但在会议过程中听取心理学家的意见后,他想知道为什么会邀请他,不确定“我们有多少话要说,甚至应该说多少”。
库恩对创造力和发散思维之间的基本认同深表怀疑。他注意到心理学家反复描述的科学家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不断拒绝传统,不断拥抱新奇;他想知道,作为基础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灵活性和开放性”是否没有被过分强调;他建议,“类似”收敛思维“的东西”更好地被说成是科学进步的必要因素,而不是障碍。库恩提出的,以及他在几年后发表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可以说是一种没有心理学家创造力范畴的科学创造力理论。
“正常科学”-范式下的科学-是解谜的一种形式,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