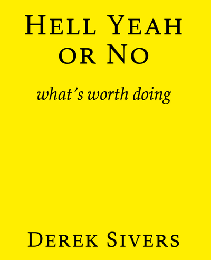为什么她如此遭人憎恨:玛丽·安托瓦内特是如何试图拯救君主制的?
把她锁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仅把她关起来,还砍下了她的头。女王被逮捕、审判和公开处决的情况并不常见。亨利八世斩首了他的两位妻子,一位是经过审判后斩首的,另一位是通过追捕法案斩首的,但他们的处决都是在伦敦塔的私密环境中进行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问题不是她的丈夫路易斯十六世,他在1793年1月因叛国罪被审判并处决。九个月后,在她自己受审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成为了一个成立一年的共和国的前女王。尽管革命者在法律和政治上可以证明起诉国王是正当的,但对他的王后的诉讼引起了更多的质疑,因为在法国,女性永远不能凭自己的权利登上王位。
玛丽-安托瓦内特之所以遭遇命运,是因为她被誉为肆无忌惮地挥霍公款,幕后操纵部长,反革命阴谋家,尤其是肆无忌惮的放荡。她几乎从1770年作为哈布斯堡皇后玛丽亚·特蕾莎(Maria Theresa)14岁的女儿踏足法国的那一刻起就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因为奥地利人哈布斯堡长期以来一直是法国的死敌。七年战争(1756-1763)期间发生的外交和军事调整,法国和奥地利是盟友,并没有让法国宫廷中的每个人都满意,那些反对它的人毫不犹豫地助长了针对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谣言。后来,革命者只需要动员这些经常是色情的小册子就可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她死后,对一些人来说,她成了那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的殉道者,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她成了贵族傲慢的应受谴责的象征,就像虚构的一句话所传达的那样:“让他们吃蛋糕”(当时没有面包)。随着时间的推移,女王可能最终获得了发言权,因为她获得了一位经久不衰的名人,作为年轻、优雅和品味的化身。*。
这位最有影响力的烈士形象提供者在她去世前整整四年都有先见之明地写下了她的故事。盎格鲁-爱尔兰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对1789年10月的起义做出了愤怒的反应。在起义中,数千名巴黎市场妇女冒雨踏足凡尔赛,与加入他们的男子一起袭击城堡,并将王室拖到巴黎。为了避免被杀,女王被迫通过一条秘密通道逃离她的私人房间。她的两名保镖被砍倒了。伯克怀旧地回忆起当玛丽-安托瓦内特还是一个年轻的妻子还没有成为女王的时候,她本人的情景:“我看到她就在地平线上方,装饰着她刚刚开始进入的高空,为她刚刚开始进入的高空欢呼--就像晨星一样闪闪发光,充满了活力、壮丽和欢乐。”1789年10月,他预计会有一万把剑跃起为她辩护,“我做梦也没想到,在一个英勇的国家里,我会活着看到这样的灾难降临到她身上。”
女王的堕落--“那个升迁,那个堕落!”--促使伯克阐述了他的保守主义学说,在这一学说中,他为君主制、宗教和传统辩护,认为它们对良好的秩序至关重要。从她遭遇逆境的场面看,他得出的结论是。
骑士精神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诡辩者、经济学家和计算器的时代取代了…。。我们再也看不到那种对等级和性别的慷慨忠诚,那种骄傲的顺从,那种庄严的服从,那种内心的从属,即使在奴役的时候,它也保持着崇高自由的精神。
多亏了“新的征服光明和理性的帝国”,他哀叹道,“所有体面的生活面纱都将被粗暴地撕下。”王室的后果已经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只是一个男人;王后只是一个女人;女人只是一只动物;而且不是最高等级的动物。”伯克不会对1791年6月王室试图逃离巴黎的拙劣尝试感到惊讶,因为随着谷仓里的动物被送回马厩,国王和王后的粗糙形象被传播开来。
在伯克站的另一端是威尔·巴希尔,这从他的书“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世界:凡尔赛的阴谋、不忠和通奸”的副标题中可见一斑。不幸的是,这是两位作家之间唯一可以进行比较的地方,因为当伯克受到女王命运的启发,深入思考执政的社会和情感基础时,巴肖尔只是试图提供刺激。追随一长串批评者的脚步,他将她的垮台归咎于她自己的“轻率、幻想驱动和臭名昭著的滑稽行为”。他复制了大量针对她的色情小册子,并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解释完全是投机性的假设,即她患有性传播疾病。对她的笔迹和占星图的分析掩盖了她生活中为数不多的事实。
尽管巴肖尔承认女王发
约翰·哈德曼(John Hardman)在这一系列观点中处于中间地位,但他的立场不仅仅是中间路线。玛丽-安托瓦内特:法国皇后的制作不仅仅是一个象征,它的意义在她的旁观者的眼睛里。按照哈德曼的说法,她既不是殉道者,也不是色狼,而是一个严肃的政治参与者。尽管玛丽-安托瓦内特缺乏教育,但她很快就学会了在法国宫廷的不同派系中走自己的路,哈德曼声称,从1787年开始,她在部长的选择和政策的决定方面越来越成功地进行了干预。她之所以能以这种方式行事,是因为面对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以及法院和特别召开的贵族大会坚决拒绝同意他的改革计划,国王失去了勇气。然而,故事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791年,当时女王与来自格勒诺布尔的一位才华横溢的29岁律师、革命领袖安托万·巴纳夫(Antoine Barnave)达成了一项不太可能的联盟。
巴纳夫是当年6月王室试图逃亡后被派往陪同王室返回巴黎的三名国民议会委员之一。哈德曼在“肮脏”的八天后才返回的令人回味的页面为随后的事情奠定了基础,他称之为Duumvirate,这是1791年底女王和巴纳夫在关键的四个月里共同统治的实验。太阳落山时,不祥的沉默的人群聚集在载有王室的马车旁,另一名委员一边与国王的妹妹调情,一边嘲弄女王,说她可能与瑞典贵族阿克塞尔·冯·费尔森(Axel Von Fersen)有染,正是他组织了这场命运多舛的飞行。相比之下,巴尔纳夫表现出了对这家人的真正关心,并逐渐赢得了女王的信任。回到巴黎后,尽管官方虚构王室被绑架,但国王和王后仍受到严密监视,使得巴纳夫无法公开探望他们。所以他和女王用简单的人名密码交换了秘密信件。(巴纳夫因名字前两个字母的字母顺序被称为“2:1”。)。
这项协议的假定目标是加强君主立宪制。国王会同意接受一部宪法,因为他相信巴尔纳夫可以促成有利于君主的变化。女王会让她的哥哥、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通过更新两国之间的联盟来表明他的默许,而这种承认将促使国王的两个兄弟和其他重要的移民返回法国,停止煽动反革命。战争将被避免,秩序将被恢复,巴纳夫希望,革命将在保证根本变革的情况下结束,但君主制仍然存在。
这些计划都没有实现,尽管它们并不比当时正在考虑的其他选择更离奇。在一个由几个世纪的君主制统治塑造的国家里,对大多数人来说,包括国民议会的大多数人来说,即使在国王和王后逃离之后,共和国仍然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当战争威胁要彻底摧毁革命时,它才成为一个可行的选择;共和国直到1792年9月才宣布成立。
然而,事实证明,君主主义者没有能力形成一个统一的立场,更不用说一个统一的政府了。极端保皇派希望与奥地利开战,因为这将为挤在边境对面的移民贵族提供击败革命者并夺回旧政权所需的军队。立宪君主主义者旨在避免战争,起初他们的优势是,尽管利奥波德的妹妹经历了痛苦,但他们更愿意看到法国受到国内动荡的困扰,这会让它全神贯注于国内,而不是冒险出国。皇帝说服自己,仅仅是报复的威胁就会迫使革命者让步,如果战争到来-战争确实发生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回应他和普鲁士的恐吓企图-战争将是短暂的,完全对他有利,特别是在他在1792年2月与他的死敌普鲁士缔结秘密联盟之后。
战争最终被证明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在巴尔纳夫和其他人采取的举措未能支撑君主制之后。1792年4月,国王本人提议向奥地利宣战,因为他梦想这最终会带来决议。要么法国在几个月内就会失败,要么如果法国军队设法取得胜利,贵族指挥官们就会把他们的军队转回巴黎,把越来越傲慢的共和党人赶走。事实证明,这些预测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预测一样是虚幻的。入侵的威胁和随后的现实激励了巴黎人民,并使那些当选为新一届立法议会的代表变得激进起来。
我有理由对…相当满意。[Adrien]Duport,[Alexandre de]Lameth和Barnave。现在我和最后两个人有一种通信,没有人知道,甚至他们的朋友也不知道。我必须公正地对待他们。尽管他们总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我总是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巨大的开放性、力量和恢复秩序以及随后恢复王室权威的真实愿望。
哈德曼很少注意到拉姆斯,他也是一名副手,但这可能只是反映了历史的偶然。他和巴纳夫都不想让人知道他们与王室的秘密联系,巴纳夫与女王的通信直到19世纪末才公之于众,当时他们的信件在属于费尔森姐姐家族的一座城堡里被发现。玛丽-安托瓦内特把她与巴纳夫的信件交给费森保管,尽管他对巴纳夫对女王的感情感到不满。
面对持续不断的传言,巴纳夫在回到巴黎后一再否认与王室有任何商业往来。1792年8月在国王的报纸上发现的一份文件决定了他的命运。这份“与M·M·巴纳夫和拉姆斯安排的部长级委员会计划”似乎证明了这两位代表一直在与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商量。巴尔纳夫立即在格勒诺布尔被捕,在那里他在监狱里度过了15个月,写了一篇关于革命和他参与革命的报道。在这些页面中,以及在审判期间,他再次坚称,在女王或王室返回巴黎后,他没有与他们有任何私人接触。他的审判在女王审判一个月后在巴黎进行,并导致了同样的结果:被断头台处决。拉姆斯已经流亡海外,巴纳夫也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住在瑞士边境附近-他徒劳地引用了这一事实为自己辩护。
巴纳夫的插曲很引人入胜,但最终它只占据了玛丽-安托瓦内特多事之秋、争论不休和悲剧人生中的一小段时间。称他们的联盟为双面派,赋予了它更多的分量,而不是它的价值。他们可以齐心协力取得他们认为势在必行的结果,但他们的声音本身并不具有权威性。他们必须通过部长们工作,而部长们可以追求自己的倡议,而这些倡议与女王和巴尔纳夫的倡议背道而驰。他们亲手挑选的战争部长路易斯·德·纳尔邦伯爵(Comte De Narbonne)希望与奥地利开战,因为他认为这会加强君主制,他错误地认为自己可以确保普鲁士的中立。当巴纳夫看到战争党正在势不可挡地取得进展时,他放弃了与女王的合作关系。
在1793年10月的审判中,玛丽-安托瓦内特面临三项主要指控:在国王的兄弟和大臣的纵容下,她挥霍了国家的财政;她将战争计划告知了法国的敌人;她在共和国的不同地区煽动了内战。她不能不感到内疚,因为她是共和国的保皇派,她自己的未来取决于推翻那个共和国。尽管她名不虚传,但王国的财政问题远不止她在钻石和凡尔赛翻修上的奢侈支出,她给宠儿的礼物,甚至她向她的哥哥皇帝提供资金(革命者从未听说过如果普鲁士人入侵,她会向他们支付报酬的承诺)。她确实向奥地利人出卖了法国的竞选计划,她的存在可能帮助挑起了内战,但前者对战争过程没有实际影响,1792年8月之后在监狱里,她几乎没有与任何人共谋的地位。
在她的审判中提出的一系列其他指控清楚地表明,除了这位前女王的有罪或无辜之外,还有更多的事情岌岌可危。公诉人在开庭陈词结束时进行了粗俗的抨击,反映了所有那些声称详细描述女王乱交的地下小册子的影响:
最后,寡妇卡佩特,在各个方面都不道德,新的阿格里皮娜,是如此反常,如此熟悉每一种罪行,以至于忘记了她母亲的品质和自然法则施加的限制,她没有脸红,(和路易斯·卡佩特[她8岁的儿子]以及他自己承认的)投身于猥亵行为,这些猥亵行为的名字本身就让人不寒而栗。
在她受审前的三个月里,她的儿子一直与她分开。他一再纠缠要告发他的母亲,最后他签署了一份声明,说她教会了他手淫,结果他的睾丸肿胀,需要治疗。当被追问这一指控时,这位前女王拒绝以“母亲回应这样的指控是违反自然的”为由作出回应。
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庭审中为自己精力充沛地辩护,证实了哈德曼对她的描述是聪明、博学的,而且相当有能力为自己的利益挺身而出。他看到了矛盾品质的混合:她是一个慈爱的母亲,一个爱管闲事的妻子,一个对错误报仇的人,一个高赌注的赌徒,至少在1789年之前,她是一个无法拥有足够的钻石、裙子、帽子或马的强迫症寻欢者。然而,即使是哈德曼,也很难回答任何读到一点点关于女王的废话的人都会面临的纠缠不休的问题:为什么她如此令人憎恨?他考虑了当时和此后列举的所有原因-她试图从王位背后统治,她的奢侈,她愿意为她最喜欢的人做任何事情-但他发现这些理由不足以解释她明显引发的厌恶程度。
这个问题的令人满意的答案需要比哈德曼想要娱乐的更多的猜测。它的一部分是常年存在的。很难抗拒与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相提并论,尽管她受过教育,衣着冷静,智力不可靠,但同样被拖入泥潭,因为她是一位与权力关系密切,甚至可能真正掌权的女性。有些人,女性和男性一样,认为女性掌权的想法很可怕,因此会相信她们的任何事情。然而,部分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8世纪90年代的事件和特殊人物。从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君主制政体中塑造一个共和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最坚定的共和党人坚持认为国王是确保过渡的重要牺牲品,尽管他们不会这样说。如果国王在被聚集的国家代表审判后被处决,那么一个新的秩序就可以建立起来。结果,国王成了一个不令人满意的受害者;他除了爱他的人民之外,从来没有表达过任何东西,而且他温和的态度,即使在审判时,他也很难看起来是一个值得根除的邪恶的化身。女王,“奥地利婊子”,以国王永远做不到的方式符合条件。杀死她,在她头上受到各种形式的羞辱之后,是一种仪式上的净化行为。它没有奏效,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死亡。女王最终因为她的年轻而被人们铭记,而不是作为一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白发女人,她的目光一直盯着她在走向断头台的路上经过的建筑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