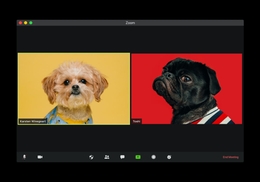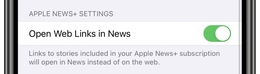我从“拦截”中辞职
今天,我发出辞呈,打算辞去2013年与杰里米·斯卡希尔(Jeremy Scahill)和劳拉·普瓦特拉斯(Laura Poitras)共同创立的新闻媒体The Intercept及其母公司First Look Media的职务。
最后一个迫在眉睫的原因是,“拦截”的编辑违反了我的编辑自由合同权利,审查了我本周写的一篇文章,拒绝发表它,除非我删除所有批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Joe Biden)的部分,他是一位候选人,得到了参与这一压制努力的所有纽约“拦截”编辑的强烈支持。
这篇被审查的文章基于最近披露的电子邮件和目击者证词,对拜登的行为提出了批评问题。这些拦截编辑并不满足于简单地阻止我与人共同创立的媒体发表这篇文章,他们还要求我不要行使单独的合同权利,将这篇文章与任何其他出版物一起发表。
我不反对他们不同意我对拜登证据所显示的观点的看法:作为避免被审查的最后一搏,我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文章,批评我的观点,让读者决定谁是正确的,就像任何自信、健康的媒体所做的那样。这是避免被审查的最后一次尝试。但现代媒体不会宣扬异议,而是会予以压制。因此,对我的文章进行审查,而不是参与其中,是这些支持拜登的编辑选择的道路。
这篇被审查的文章很快就会发表在这一页上。我的辞职意向书今天早上寄给first lookMedia的总裁迈克尔·布鲁姆(Michael Bloom),下面公布了我的辞职意向书。
从现在起,我将在Substack上发布我的新闻,无数其他记者,包括我的好朋友、伟大的无畏记者马特·泰比(Matt Tybbi),已经来到这里,以摆脱席卷全国主流媒体的日益压抑的气氛,从事新闻工作。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我自愿牺牲了一家大型机构的支持和有保障的工资,除了相信有足够多的人相信独立新闻的优点和自由言论的需要,愿意通过订阅来支持我的工作之外,什么都没有。
像任何有年幼的孩子、有家庭、有很多责任的人一样,我这样做时有些害怕,但也坚信别无选择。我晚上睡不着觉,因为我知道我允许任何机构审查我想说和相信的东西-尤其是我与人共同创立的一家媒体机构,明确的目标是确保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在其他记者身上,更不用说我了,因为我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了一位在即将到来的全国大选中得到编辑强烈支持的强大的民主党政客。
但是,导致我被我自己的媒体审查的怪异场面的病态、非自由主义和压抑心态,并不是“拦截”所特有的。这些病毒几乎污染了每一个主流的中左翼政治组织、学术机构和新闻编辑室。15年前,我开始写关于政治的文章,目标是打击媒体的宣传和镇压,无论涉及到什么风险,我都无法接受任何情况,无论多么安全或有利可图,迫使我将我的新闻工作和言论自由权利置于其令人窒息的限制和教条的支配之下。
从2005年我开始写关于政治的文章开始,新闻自由和编辑独立对我来说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15年前,当我还是一名律师的时候,我在免费的Blogpot软件上创建了一个博客:没有任何作为记者开始新职业的希望或计划,只是作为一个关心我在反恐战争和公民自由方面看到的东西的公民,想要表达我认为需要被听到的东西。这是一种热爱的劳动,建立在事业和信念的精神基础上,依赖于对完全编辑自由的保证。
它之所以蓬勃发展,是因为我建立的读者群体知道,即使他们不同意我表达的特定观点,我也是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声音,不与任何派别结婚,不受任何人控制,努力尽可能诚实地对待我所看到的东西,并总是对以不同方式看待事物的智慧感到好奇。我为那个博客选择的标题是“无人认领的领土”,反映了从囚禁到任何固定的政治或智力教条或制度限制的解放精神。
2007年沙龙给了我一份专栏作家的工作,2012年“卫报”(The Guardian)又给了我一份专栏作家的工作,我接受了他们的邀请,条件是我有权在没有审查、高级编辑干预或任何其他允许或批准的情况下直接在互联网上发表我的文章和专栏,除非是在定义狭隘的情况下(比如可能给新闻机构带来法律责任的文章)。这两家媒体都对出版系统进行了改造,以适应这种情况,在我与他们共事的这些年里,他们总是信守这些承诺。
2013年,为了创建一个新的媒体渠道,我在斯诺登报道的高峰期离开了《卫报》(The Guardian),不用说,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对自己的新闻独立性施加更多的约束和限制。事实恰恰相反:“拦截”计划的核心创新,最重要的是创建一个新的媒体渠道,在那里,所有有才华、负责任的记者都将享有我一直为自己坚持的同样的编辑自由权利。就像我在2013年“纽约时报”的一次交流中告诉前“纽约时报”执行主编比尔·凯勒(Bill Keller)的那样,我们在“纽约时报”上谈到了我对主流新闻的批评,以及“拦截”背后的理念:“编辑应该在那里赋予力量,让强大、高度真实、咄咄逼人的对抗性新闻成为可能,而不是成为中立或压制新闻的障碍。”
当我们三人作为联合创始人很早就决定不试图管理新媒体的日常运营,以便我们可以专注于我们的新闻工作时,我们就高级编辑,特别是总编辑的审批权进行了谈判。拥有该头衔的人的主要责任是在与我们密切协商的情况下,实施我们创建这个新媒体渠道所依据的独特的新闻愿景和新闻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中最重要的是编辑自由,保护记者以诚实的声音说话的权利,以及公布而不是压制来自主流正统的异议,甚至是彼此之间的大学分歧。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确保记者一旦履行了事实准确性和新闻道德的首要职责,不仅被允许而且被鼓励表达背离主流正统和自己编辑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观点;用自己的激情和信念表达自己,而不是充斥在人工客观性的公司化、做作的语气中,最重要的是无所不能;完全不受其他任何人的教条信仰或意识形态议程的影响-包括三位联合创始人的教条信仰或意识形态议程。
与最初的设想相比,当前的“拦截”迭代是完全无法辨认的。它不是为表达不同意见、边缘化的声音和不为人知的观点提供场所,而是迅速成为另一个拥有强制意识形态和党派忠诚、僵化和狭隘的允许观点范围(从建制派到建制派)的媒体渠道。
因此,当主流选区不受欢迎的激进自由撰稿人的声音被刊登在The Intercept上时,这确实是一件罕见的事情。没有声称主流可接受性的记者或作家-正是我们试图放大的人-几乎没有机会被发表。对于The Intercept来说,发表内容不太适合至少12份或更多类似规模的中左翼出版物的情况甚至更少见,这些出版物在成立之前就已经成立,从琼斯母亲到Vox,甚至是MSNBC。
越界是需要勇气的,质疑和抨击那些在自己所处环境中最神圣的虔诚是需要勇气的,但担心疏远自由派正统观念的卫士,特别是在Twitter上,这是“拦截”驻纽约编辑领导团队的主要特征。因此,“拦截”几乎放弃了挑战和抨击,而不是安抚和安慰其文化和政治圈子中最有权势的机构和守护者的核心使命。
雪上加霜的是,The Intercept虽然逐渐将联合创始人排除在其编辑使命或方向的任何角色之外,并一个接一个地做出选择,我曾口头反对这些选择,认为这背叛了我们的核心使命-但为了筹集资金,它继续公开利用我的名字,为它知道我不支持的新闻事业筹集资金。它故意让人们认为我是该报新闻错误的责任人,以确保这些错误的责任落在我身上,而不是那些巩固控制并对这些错误负责的编辑身上。
利用我的名字来逃避责任的最骇人听闻的例子,但绝不是唯一的,就是现实中的赢家溃败。正如“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最近报道的那样,这是一个我没有任何参与的故事。在巴西工作期间,我从未被要求处理Winner发送给我们纽约新闻编辑部的文件,也没有要求任何特定的记者对这些文件进行处理。直到那份文件出版前不久,我才知道它的存在。监督、编辑和控制这篇报道的人是贝齐·里德(Betsy Reed),这就是为什么应该考虑到这篇报道的规模和复杂性,以及她作为主编的地位。
是“拦截”杂志的编辑向这篇报道的记者施压,要求他们迅速将这些文件提交给政府进行认证-因为他们急于向主流媒体和知名自由派证明,“拦截”杂志愿意登上俄罗斯之门的火车。他们想要反击这样一种看法,即我的文章对那起丑闻的核心主张表示怀疑,认为拦截行动在一个对美国自由主义甚至左翼具有高度重要性的故事上越界了。我的文章表达了对这起丑闻的核心主张的怀疑。这种渴望-获得我们着手对抗的非常主流媒体的批准-是处理Winner的文件速度和鲁莽的根本原因。
但直到今天,The Intercept一直拒绝提供任何关于真人秀获胜者故事中发生的事情的公开解释:解释谁是犯了错误的编辑,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错误。正如《纽约时报》的文章所表明的那样,尽管我、斯卡希尔、劳拉·普瓦特拉斯(Laura Poitras)和其他人直言不讳地要求窃听机构作为一个要求他人透明的机构,有义务为自己提供透明度,但这种拒绝一直持续到今天。
这种沉默和掩盖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向公众解释真人秀获胜者的故事发生了什么,将会揭示谁是真正的编辑,谁应该为那次令人深感尴尬的新闻编辑部失败负责,这将否定他们继续躲在我身后的能力,让公众继续假设我是报道过程的罪魁祸首,而我从一开始就被完全排除在报道过程之外。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了让编辑部在方便的时候利用我的名字、工作和信誉,同时越来越多地剥夺我影响其新闻使命和编辑方向的机会,同时又追求一项我认为完全令人憎恶的编辑使命,这只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两难境地。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想离开“拦截”号。随着它的恶化和放弃了最初的使命,我对自己说--也许是理所当然的--只要“拦截”至少继续为我提供资源,让我亲自做我相信的新闻工作,而且永远不干预或阻碍我的编辑自由,我就可以吞下其他一切。
但是,本周我的文章遭到了残酷的审查--关于亨特·拜登(Hunter Biden)的材料,乔·拜登(Joe Biden)在乌克兰和中国问题上的行为,以及我对媒体试图与硅谷和“情报界”结成极其邪恶的联盟,试图压制其爆料的关闭排名的批评--侵蚀了我能坚持的最后一个留下来的理由。这意味着,这个媒体不仅没有像我7年前所希望的那样,给其他记者提供编辑自由,而且现在甚至不再给我提供了。在总统选举即将到来的日子里,不知何故,我不愿表达任何纽约随机编辑认为不受欢迎的观点,现在我不得不以某种方式调整我的写作和报道,以迎合他们对选举特定候选人的党派愿望和渴望。
说这样的审查制度对我来说是一条红线,这种情况我是不会不惜一切代价接受的,这是轻描淡写的。我自己的媒体渠道对乔·拜登保持沉默,这对我来说是令人惊讶的,但也反映了我们目前的话语和狭隘的媒体环境。
许多其他事件也是我决定离开的原因之一:现实制胜者掩盖事实;当一名同事试图公开、毫无根据地反复给李方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试图破坏他的声誉时,他决定将李方吊死,甚至迫使他道歉;拒绝报道阿桑奇引渡听证会的日常程序,因为这名做得出色的自由撰稿人的支持者在政治上令人反感;。当涉及到迎合其自由派基础信仰的观点或报道时,它完全缺乏编辑标准(The Intercept发表了一些对极大主义俄罗斯门疯狂的最轻信和最虚假的肯定,令人震惊的是,它率先错误地将亨特·拜登(Hunter Biden)的档案贴上了“俄罗斯虚假信息”的标签,轻率而不加批判地引用了前中央情报局(CIA)官员的一封信,这封信包含了这种毫无根据的含沙射影的内容)。“截击报”(The Intercept)发表了一些最轻信、最虚假的断言,称亨特·拜登(Hunter Biden)的档案为“俄罗斯的虚假信息”。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陈词滥调,但是--即使经历了所有的挫折和失败--我还是要离开,带着真正的悲伤,而不是愤怒,写下这篇文章。这个新闻媒体是我和许多亲密的朋友和同事在建筑上倾注了我们大量的时间、精力、激情和爱的东西。
“拦截”号做了很好的工作。该报的编辑领导和First Look的经理们坚定不移地支持我去年与我勇敢的年轻同事在“拦截巴西”(Intercept Brasil)进行的艰难而危险的报道,揭露博尔索纳罗政府最高层的腐败,并在我们忍受死亡和监禁威胁时站在我们身后。
它继续聘用我的一些最亲密的朋友,杰出的记者,他们的工作-当它克服编辑阻力-只会让我产生最高的钦佩:杰里米·斯卡希尔(Jeremy Scahill)、李方(Lee Fang)、穆尔塔扎·侯赛因(Murtaza Hussain)、内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瑞安·格林(Ryan Grim。我对那里的任何人都没有个人敌意,也没有想要损害它作为一个机构的愿望。贝齐·里德是一位非常聪明的编辑,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我和他建立了亲密而宝贵的友谊。皮埃尔·奥米迪亚,First Look的最初资助人和出版人,总是信守他个人的承诺,永远不会干预我们的编辑过程,即使我发表的文章与他的强烈观点直接相左,甚至当我攻击他资助的其他机构时也是如此。我离开不是出于复仇或个人冲突,而是出于信念和事业。
我所说的关于拦截的批评都不是它独有的。相反,这是在每个主要的文化、政治和新闻机构内部激烈的关于言论自由和持不同政见者权利的激烈斗争。这就是新闻业,乃至更广泛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所面临的危机。我们的话语越来越不能容忍不同的观点,我们的文化要求越来越多地屈服于自封的真理和正义垄断者强加的主流正统观念,并以网络执法暴徒大军为后盾。
没有什么比新闻业更严重地受到这一趋势的破坏,它最重要的是要求记者有能力冒犯和激怒权力中心,质疑或拒绝神圣的虔诚,挖掘甚至对最受爱戴和最有权势的人物也有负面影响的事实,并突出腐败,无论腐败在哪里发现,无论谁因曝光而受益或受伤。
在本周被我自己的新闻机构审查的非同寻常的经历之前,我已经在探索创建一个新媒体的可能性。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与各个政治派别的一些最有趣、最独立、最有活力的记者、作家和评论员积极讨论为一个旨在对抗这些趋势的新渠道获得资金的可行性。我们工作文件的前两段内容如下:
美国媒体陷入了一场两极分化的文化战争,迫使新闻业遵循部落、集体思维的叙述,这些叙述往往与事实背道而驰,迎合的是不能反映更广泛公众的观点,而是少数超级党派精英。遵守高度限制性、人为的文化叙事和党派身份的需要,创造了一种压抑和狭隘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大量的新闻和报道要么没有发生,要么通过最歪曲和最脱离现实的镜头呈现。
随着几乎所有的主要媒体机构都在某种程度上被这种动态所俘虏,人们迫切需要不受束缚和自由的媒体超越这场两极分化的文化战争的边界,满足公众的需求,因为公众渴望的媒体不是为某一方服务,而是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追求报道、思想和调查的路线,而不必担心违反文化虔诚或精英正统。
我绝对没有放弃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能够实现的希望。从理论上讲,我本可以在“拦截”网站呆到那时,通过听从新审查员的指令来保证我的家人有稳定和安全的收入。
但如果我这样做,我会深感羞愧,并相信我会背叛我自己的原则和信念,我敦促其他人遵循这些原则和信念。因此,在此期间,我决定追随无数其他作家和记者的脚步,他们因各种形式的异端和异见而被逐出日益镇压的新闻区,并在这里寻求庇护。
我希望利用这个新平台提供的自由,不仅可以继续发表我的读者所期待的独立的、有冲击力的调查性新闻、坦率的分析和观点写作,而且还可以开发一个播客,继续YouTube的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