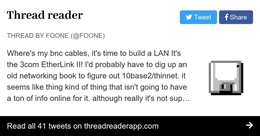为什么我们生活在历史小说的黄金时代?(2019年)
在2013年的一次采访中,作家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的小说被誉为当代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画窗”。当他承认自己抵制历史小说时,他表达了许多读者的感受,解释说他被那些“致力于让自己的生活和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世界有意义”的作家所吸引,这些作家明显参与了这场游戏。这是一种很难不同意的观点--把过去当作现成的寓言,把它当做一面方便的镜子来看待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未来,难道不是欺骗吗?
但在我们即将步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回顾过去的冲动感觉有所不同:要想理解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发现自己所处的深不可测的世界,就有必要理解之前发生的事情-澄清这场游戏及其利害关系,以及它的规则和立场。一种新的历史小说已经演变成告诉我们,过去不再仅仅是序幕,而是故事本身,塑造了我们关于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是谁的日益支离破碎的童话故事。在争取社会进步的战斗中,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战斗过并取得了胜利,随处可见时间的停泊。在媒体时代,历史不只是学者们记录的一连串事实,而是一个复杂的叙事,被政党和Facebook的虚假信息运动所利用,以表达我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我们继承的过去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在向我们诉说,但共同的主线,更不用说对现实的共识看法,感觉越来越难获得。
[今春晚些时候即将到来:T List时事通讯,每周一次综述T杂志编辑们正在注意和垂涎的东西。请在此处注册。]。
在不确定的时期,我们期待文学的朦胧镜子投射到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前提是这些愿景实际上不会成为现实。但是,当我们开始在对未来过去的憧憬中认出自己时,它会唤起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似曾相识的形式肯定值得用法语来形容,它传达了一种特殊的恐惧,那就是看着我们自己的警示故事变成现实。我们衰落的伟大预言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正在拍摄“女仆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的续集,这并不令人惊讶。这部原著写于1984年宗教右翼崛起期间,当时“家庭价值观”成了不宽容的委婉说法,原著小说让人联想到一种厌恶女性的父权制,今天这种父权制已经正常化和立法,达到了当时几乎没有人认为可能的程度。现在读它,感觉就像把手放进抽屉,一遍又一遍地砰的一声。
面对当下,对未来的憧憬日益失灵,文学作家们越来越多地回首往事,不是用已知的过去来安慰我们,甚至不是简单地对现在进行寓言,而是在一种线索收集的驱使下,寻找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是这样的人,我们是如何来到这里的,以及火车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脱轨的。作家,包括科尔森·怀特黑德(Colson Whitehead)和乔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安娜·伯恩斯(Anna Burns)和马龙·詹姆斯(Marlon James),吉娜·阿波斯托尔(Gina Apostol)和雅雅·加西(Yaa Gyasi)等等,一直在澄清混乱,不是给我们答案,而是捕捉历史塑造我们、伤害我们和牵连我们的方式。当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诺瓦利斯(Novalis)写道“小说从历史的缺陷中崛起”时,他无法预见,几个世纪后,这些缺陷会变得更像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太多的人长期被排除在外,真正的权力架构被隐藏起来。他们的小说揭示了旧故事的空洞,破坏了我们对历史的看法,而不是肯定了它们-这毕竟是文学小说的一个目的。在我们这个标语和杜撰推特的时代,这也是一种抵抗形式。
历史小说产生于一种想要连续地看到人类计划的愿望,源于这样一种信念,即有可能讲述与当下有关的过去消失的故事,这些故事是在档案结束和作者想象开始的地方锻造的。正如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在他最后完成的手稿“关于历史哲学的论文”(Teses on the Philosic of History,1940)中所说,按下暂停按钮的愿望--“唤醒死者,让破碎的东西变得完整”--是朱莉·奥林格(Julie Orringer)的新小说“飞行公文集”(The Flight Portfolio)的基础。这部小说讲述了瓦里安·弗莱(Varian Fry)的故事,他是一位鲜为人知的美国记者,曾帮助数千名艺术家从纳粹欧洲走私出来。弗莱获救的艺术家包括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和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但还有一些作家,他们将塑造我们对20世纪的理解,包括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德国小说家兼剧作家狮子·费赫特温格(Lion Feuchtwanger)。这部小说以法国维希为背景,寻求一种补救:在历史的广阔全景中,恢复法西斯主义边缘生活的细粒度感觉。法希,我们在一个聚会上看到了安德烈·布列顿
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在2009年出版了“狼厅”(Wolf Hall),2012年出版了续集“举起身体”(Bring Up The Body)(曼特尔正在写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镜子与光明”(The Mirror And The Light)),被誉为一个颠覆体裁的时刻:这是一部彻底的当代文学小说,有非古老的对白,碰巧是和都铎一起出演的。曼特尔对一段深入人心、略显陈旧的历史的天才,让都铎王朝莫名其妙地引人入胜,近在咫尺。但即使在曼特尔之前,历史小说和文学小说之间的界限就已经出现了裂痕。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像A.S.拜厄特(A.S.Byatt)和彼得·凯里(Peter Carey),以及后来的莎拉·沃特斯(Sarah Waters)和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这样的作家,对我们访问和重塑过去的方式着迷,提升了这一体裁的地位,让这部小说的同理心技巧变得更加神奇:有多少读书俱乐部的女主妇发现自己被沃特斯维多利亚时代的女同性恋爱情故事惊呆了?
当然,曼特尔做的最激进的事情是让安妮·博林(Anne Boleyn)发声,她是宗教改革之母,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和随后几个世纪的英国历史。在曼特尔看来,博林聪明、精力充沛、母性强、时髦,容易发脾气和专横,而且--致命的--对自己地位的稳定性过于自信。在“举起身体”的后记中,曼特尔解释了她的记录是多么的单薄。她的审判记录没有一份幸存下来:与历史上如此多的女性一半一样,她的审判是一个尴尬的抹去的故事。
如果我们没有从历史中学到其他东西,那就是我们无法逃避历史,而从历史中走出来需要一些诚实和真相。提出前进方向的书是2018年阅读量较少的书之一,阿波斯托的“保险”(Insurrecto),这是一本关于努力做到这一点的历史小说。故事从现在开始,菲律宾作家兼翻译家马格萨林(Magsalin)同意帮助时尚、年轻的索菲亚·科波拉(Sofia Coppola)风格的美国导演基亚拉(Chiara),基亚拉正在拍摄一部关于1901年被遗忘的暴行的电影,在那次暴行中,美国占领者对菲律宾起义进行了报复。在玛格萨林读完基亚拉的剧本后,她自己写了一个,很快我们就会读到两个相互竞争的历史事件版本-一个是从美国白人社会名流摄影师的角度,另一个是从菲律宾学校教师的角度。最后,马格萨林和基亚拉都认为他们没有对这一事件进行真实的描述-但Apostol没有。正如她所说,美国可能已经“制造了如何看待世界的方式”,但现在情况正在改变,因为新一代作家、电影制作人和艺术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游戏中的旧故事:对历史和记忆的反叛。按照定义,记忆的过程是一种想象和创造的行为,最难讲的故事已经变成了我们最需要的故事,那些没有推特外卖的故事-只有看不见的死人,潜伏着等待的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