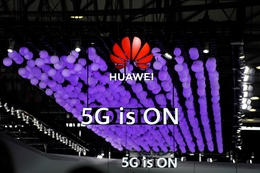大卫·肖尔的美国政治统一论
大卫·肖尔因被解雇而成名。5月下旬,在针对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谋杀的广泛抗议活动中,这位28岁的数据科学家在Twitter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1968年的非暴力示威活动比“骚乱”更有效地推动舆论和选民行为左倾。许多推特用户以及(据报道)Shor的一些同事和Civis Analytics数据公司的客户认为这篇帖子不敏感。一天后,肖尔为他的推文公开道歉。两周后,他丢掉了西维斯政治数据科学负责人的工作,成为所谓取消文化过度行为的代名词。(由于保密协议,肖尔没有公开讨论他被解雇的问题,他被解雇的细节仍未披露)。
但在肖尔不可思议地转变为塞莱布雷(Célèbre)事业之前,他是民主党政坛最有影响力的数据专家之一--20岁时,他是一个神童,在2012年奥巴马竞选团队内部担任内特·西尔弗(Nate Silver),负责编写白宫用来判断竞选形势的预测模型。
这种意识形态背景、就业经验和专业知识的独特结合,给肖尔提供了一个关于美国政治的独特视角。他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坚持大额捐赠者将民主党拉向左翼。他是列宁主义先锋主义和中间选民定理的拥护者。在我认识他的三年里,我想我没有发现一个关于美国政治的问题,他至少参考了三项同行评议的研究来回答。
肖尔仍在为民主党政治提供咨询服务,但他不再为一家限制他公开发表意见的自由的公司工作。“情报员”最近与他谈到了民主党的实际运作方式,为什么未来十年对美国右翼来说会是一个伟大的十年,抗议活动如何影响公众舆论,左翼在选举政治上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是否会连任等问题。
让你的名字成为文化战争争议的速记是什么感觉?我不能对周围的任何事情发表评论。
我觉得很沉默,但没关系。那么让我们从这里开始吧:自从你第一次在奥巴马竞选团队工作以来,你对选举政治运作方式的概念做出了哪些最大的修改?
我认为,进入政坛,我高估了那些在竞选活动中为决策而工作的人的个人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这是高估人们做出决策的程度的更广泛现象的一部分。在2012年,我会看到进步的博客发表这样的故事,“白宫正在举办气候周。这肯定是因为他们的民调显示,气候是共和党人的一个弱点。“。一旦你认识了办公室里的人,你就会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只是在一个尴尬的办公室会议上,就像是,“哦,伙计,我们这周要做什么?嗯,我们可以做气候方面的工作。“。党内几乎没有长期的战略规划,因为没有人有动力去做。因此,竞选活动的行动,虽然不是随机的,但比我意识到的更具随机性。
我也倾向于顾问的变革理论--或者类似于变革的过程论。所以很多左翼人士会说,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团队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经济问题,并在社会问题上加倍努力,因为为她工作的人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支持进步经济政策的竞选活动会威胁到她捐赠者的物质利益。
但事实并非如此。真正的机械原因是,克林顿竞选团队聘请了民意调查人员来测试一系列不同的信息,由于无聊的机械原因,社会信任度较低的工薪阶层比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士更不可能回答这些电话民意调查。因此,所有这些世界性的、社会自由的信息在他们的电话民意调查中都表现得非常好,尽管这最终让她损失了很多选票。但问题是机械的,而不是所有参与者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利益。
一位有品味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庸俗”的反义词是什么)可能会反驳说,阶级偏见与那个机械错误有关--世界性的、中上阶层的民调人员和操作员急于看到他们的世界观得到肯定,这导致他们忽略了他们的调查遭受系统性抽样错误的可能性。
完全正确。竞选团队确实希望获胜。但在竞选活动中工作的人往往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动机,因此,超级容易说服自己做一些战略上愚蠢的事情。我告诉人们的,或者我的团队(在Civis)告诉人们的,实际上都没有那么聪明。你知道,我们会做所有这些计算,其中一些相当酷,但从更高的层面来看,我们的意思是:“你应该把钱投入接近选举的州的廉价媒体市场,你应该谈论流行的问题,而不是谈论不受欢迎的问题。”我们会使用机器学习来规模化运作。
正确的政治策略实际上并不清楚。但克林顿竞选团队中的许多人欺骗自己,认为他们不必安抚种族主义白人的社会观点。
啊,对。人们在推特上对我大喊大叫。因此,工人阶级白人拥有巨大的政治权力,他们倾向于共和党。如果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民主党人接受了新自由主义,那在意识形态上会很方便。但很明显,这不是真的。
我认为赢回这些选民很重要。因此,如果我竞选公职,我肯定会说,这些选民转而反对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民主党人没有接受经济民粹主义。我认为这是合理的政治信息。但就实际驱动因素而言,数字相当清楚。从理论上来说,可以想象一个选民一生都投票给民主党,然后出于对奥巴马医改或贸易或其他任何事情的失望而投票给特朗普。我相信有很多这样的选民,但他们没有代表性。
当你看一下2012年和2016年的选举结果,以及民主党选票份额的模式变化时,你会发现,个人层面上最大的选票转换预测因素是教育;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倾向于民主党人,而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倾向于共和党人。但是,如果你问一系列“种族怨恨”的问题,比如,“你认为有很多白人很难找到工作,因为非白人都在找工作吗?”或者,“你认为白人对这个国家的治理方式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吗?”--然后控制以种族仇恨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的倾向,教育不再是相关变量:2016年,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种族怨恨程度较低的白人倾向于我们,而受过大学教育、种族怨恨程度很高的白人则转而反对我们。
你可以说,“哦,你知道,政治学家衡量种族怨恨的方式是一个阶级标志,因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知道他们不应该说政治上不正确的话。”但是当你看到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的支持率时,它与呃<foreign language=“English”>…</foreign>有相当高的相关性。充满种族色彩的…。谷歌搜索词。所以有这样一位政治家,他的竞选平台是反移民和反政治的正确立场。然后,他赢得了一大群摇摆不定的选民的选票,选票转换与各种个人层面的种族怨恨指标高度相关-在地理层面上,与种族主义搜索词相关。在某种程度上,你不得不说,哦,实际上,这些人的动机是种族主义。这只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事实。
我认为人们从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2016年大选后,我在推特上看到的一场斗争是一群人说,奥巴马对特朗普的选民是种族主义者,是不可挽回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把重点放在郊区。然后有左派人士说,“实际上,这些工人阶级白人被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背叛了,我们只需要拥抱社会主义,赢回他们,我们不能相信郊区的人。”我认为这些观点的真正综合是奥巴马对特朗普选民的动机是种族主义。但他们在选举中真的很重要,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让他们投票给我们。
所以有一大堆问题。密切关注政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之所以与其他人不同,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观点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要高得多。
如果你决定创建一张调查记分卡,在每一个问题上-选择、枪支、工会、医疗保健等-你给人们一分,让他们在两个政策选项中选择更自由的一个,然后让1000名美国人填写它,你会发现民主党当选的官员比90%到95%的人都偏左。
原因是,虽然选民在一些问题上可能比乔·拜登有更多的左翼观点,但他们的观点并不一致。有很多反堕胎的人想要更高的税收,等等。政治学家大卫·布鲁克曼(David Broockman)的一篇论文非常著名地提出了这一点--“温和派”选民没有温和的观点,只有意识形态上不一致的观点。一些人对媒体对那份报告的报道回应说,“哦,人们只是随机回答这些调查,问题并不重要。”但这实际上并不是报纸所显示的。在另一个单独的部分,他们通过向选民展示假想的候选人对决来测试问题的相关性-这里有一位政治家站在这个位置,另一位政治家站在相反的位置-他们发现,问题一致性实际上对预测人们投票给谁非常重要。
因此,这表明有大量选民在一些问题上与我们意见一致,在其他问题上与我们意见不同。每当我们谈论一个特定的问题时,这就增加了选民根据这个问题投票的程度。
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以及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然而,一群人改变了他们的投票。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各种问题的突出程度发生了变化。双方都谈到了更多关于移民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人们对移民的偏好和人们投票给哪位候选人之间的关联度上升了。2012年,双方都谈到了医疗保健。在2016年,他们没有这样做。因此,人们对医疗保健的看法和人们投票给哪位候选人之间的相关性下降了。
这意味着每次你开口说话,你都会遇到一个复杂的最优化问题,你说的话会让你赢得一些选民,同时也会让你失去其他选民。但这实际上很酷,因为竞选团队对他们谈论的问题有很大的控制权。
平均而言,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对移民的看法非常保守,而且总体上持保守的种族态度。但他们在经济问题上持中间偏左的观点;他们支持全民医保和提高最低工资。因此,我认为民主党人需要谈论他们与我们意见一致的问题,并努力不谈论我们存在分歧的问题。实际上,这意味着不谈论移民问题。
听起来你是在说舆论是一个固定的实体,竞选活动几乎没有能力重塑它。我认为许多进步人士对这一观点提出异议。在他们看来,“种族主义白人的社会观点”并不是既定的。右翼媒体向公众提供了一个将他们的利益与移民的利益对立起来的故事。但是,如果民主党人对企业利益如何利用种族分歧来分裂和征服劳动人民提出了相反的说法,或许他们可以改变什么是“受欢迎的”,什么不是“受欢迎的”。为什么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呢?
关于机制的精确描述是值得的。诚然,政党对其党派的观点拥有巨大的控制权。大约有20%的选民非常信任民主党精英。如果党让他们这样做,他们会立即转变观点。这就是如何让废除洲际交易所从10%的问题变成30%的问题。如果你是一名意识形态活动家,那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如果你说服强大的党派采纳你的观点,那么当该党上台时,强大的党派最终会组成那个政府,然后你就可以在政策上取得进展。
问题是摇摆不定的选民不信任任何一个政党。因此,如果你让民主党人支持废除ICE,那不会得到温和派、种族主义的白人的支持,只会把他们变成共和党人。所以这就是权衡。当你接受不受欢迎的东西时,你会变得更不受边缘选民的欢迎,但也会让相当大一部分公众改变他们的观点。而后者有时会产生长期的变化。
但这是一个艰难的权衡。我认为从来没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失去总统职位对我们来说是一笔很好的交易,因为我们提高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通常不是人们想要的。他们不想让一个不受欢迎的问题从7%的支持率上升到30%的支持率。他们想要像同性婚姻或大麻合法化那样的事情,你把一个问题从30%上升到70%。如果你看一下这些事情的历史,就会发现竞选活动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如果你看看支持同性婚姻的长期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它开始逐年线性增长。但是,就在2004年竞选期间,就在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的时候,它突然变成了党派之争,支持率下降了。在它不再是竞选问题后,支持又回到了趋势。
竞选活动就是不能影响这些长期的变化。他们可以将信息引导给信任他们的党派人士,他们可以通过发出与他们在问题上达成一致的信号来讨好边缘选民。但是,没有太大的空间来改变边缘选民的想法。
在过去几周的事件中,随着乔·拜登(Joe Biden)领先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种族歧视警察的重要性增加,你如何看待这一分析?显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变数。但我们看到,对“黑人生命也是命”运动和警察改革的支持激增。我们看到拜登在哪位候选人最能处理种族关系的问题上比特朗普拥有更大的优势-与此同时,进步活动人士一直将左翼与取消对警察的资助这一异常不受欢迎的概念联系在一起。
嗯。我不会假装我已经预测到它会是这样摇晃出来的。但我确实认为这与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内容是一致的。
考虑选举的重要性和提高特定问题的显著性的影响的一种方式是,看看选民在特定问题上信任哪个政党,而不仅仅是他们声明的政策偏好是什么。因此,如果你做一个关于枪支的普遍背景调查的民意调查,你会发现它们超级受欢迎。但随后,依靠背景调查参选的政客往往会输。同样,如果你对全面移民改革进行民意调查,它会超级受欢迎,甚至在共和党人中也是如此。但然后共和党人就可以在反移民的平台上竞选并获胜。那么你怎么把那个圆圈平方呢?
一种方法是记住,这些民意调查给我们提供的信息环境非常有限。你只需向人们抛出一个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句子长的想法,然后人们就会对此做出反应。因此,它告诉你,在没有任何党派背景的情况下,人们会如何对一项政策做出第一次反应。但最终,当人们听到双方的意见时,他们会回到某种党派基线。但这并不是虚无主义;不仅仅是倾向于民主党的选民会采纳民主党的立场,或者倾向共和党的选民会自动采纳共和党的立场。容易说服的选民在不同的问题上信任两党。
这里和其他国家都有一个非常基本的模式,选民认为中间偏左的政党是有同情心的。中左翼政党关心环境,减少贫困,改善种族关系。然后,你知道,中右翼政党被认为更“严肃”,或者说更像严厉的父亲之类的人物。他们在推动经济运行或降低失业率、税收、犯罪或移民方面做得更好。
如果你看看这在美国是如何分解的-盖洛普在2017年做了一些事情,我相信从那以后数字没有太大变化-你会看到同样的基本情况。但有一个有趣的转折。民主党人持续获得高度评价的一件事是改善种族关系。这也说明了种族仇恨的复杂性。在美国,种族指控问题通常是在犯罪的背景下提出的,这是一个非常受共和党人影响的问题(就中位数选民信任哪个政党而言)。或者是移民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共和党人的问题。因此,即使选民承认美国存在巨大的系统性不平等,对它们的讨论通常是在保守派可以假设与安全或所有这些人们信任共和党的其他事情进行权衡的背景下进行的。
非暴力抗议的强大之处在于,尤其是引起警方不成比例反应的非暴力抗议,它可以真正发自内心地将对话转移到这个问题空间中有利于民主党人和中左翼的那部分。这是对平等、社会正义、公平的追求-这些都是民主党人的概念-而不是在犯罪或公共安全方面进行权衡。所以我认为,非暴力抗议在政治上是有利的,无论是在改变公众对个别问题的看法方面,还是在选举同情左翼关切的政党方面,我认为这与相当广泛的、横截面的证据(我在某个时候显然在推特上发了一条证据)是一致的。
至于“废警”的说法,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基本上没有主流民选官员接受。最有说服力的选民从电视网的晚间新闻广播和CNN获得新闻。如果你看看他们是如何报道这些事情的,你会发现“废除警察”的概念并没有像它在推特和精英讨论中得到的那样多的发挥。就其被报道的程度而言,这篇报道的特色是著名的左翼政客大声谴责它。我认为这对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成功的故事。积极分子不仅能够戏剧性地改变围绕种族正义问题的辩论条件,而且能够以一种基本上是第二次大觉醒的方式改变警察正义的辩论条件。但由于民主党政客一直在追逐中位数选民,我们不得不兼得蛋糕和蛋糕。在不付出选举代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让公众舆论在这些问题上朝着我们的方向转变。
扮演起义者的代言人:抗议并不完全是非暴力的。有人可能会说,如果明尼阿波利斯没有发生骚乱,媒体的关注就会减少,因此非暴力抗议活动就会减少。那么,我们怎么知道非暴力抗议活动是这场运动政治效力的来源呢?为什么那些抗议活动边缘的暴力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