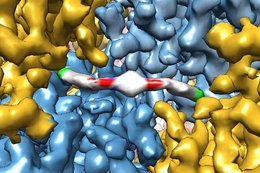认知偏差可以解释真相
我们内在的偏见有助于解释我们的后真理时代,即“替代事实”取代实际事实,并且感觉比证据更重要。
说事实在塑造我们对经验性问题的信念方面不如感觉重要,至少在美国政治中,这似乎是新的。在过去,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甚至是对真理本身的挑战,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公开地接受过这样的挑战,作为对现实进行政治从属的策略,这就是我所定义的“后真理”。在这里,“后”不是在时间上(而不是在“战后”中)表明我们是“过去”的真理,而是在说意识已经被诸如意识形态之类的次要事物所掩盖了。
后真理最深的根源之一是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因为它已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中与我们的大脑联系在一起:认知偏差。几十年来,心理学家一直在进行实验,这些实验表明我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理性。其中一些工作直接关系到我们面对意外或不舒服的事实时的反应。
人类心理学的中心概念是我们努力避免心理不适。认真思考自己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一些心理学家称这为“自我防御”(遵循弗洛伊德理论),但是无论我们是否在这种范式内对其进行构架,这一概念都很明确。对于我们来说,认为自己是聪明,有见识的,有能力的人比不拥有自己更聪明。当我们面对表明我们认为不真实的信息时会发生什么?它造成了心理上的紧张。我怎么能成为一个聪明的人却又相信虚假?在自我批评的残酷攻击下,只有最强大的自我才能站得很久:“我真是个傻瓜!答案一直都在我面前,但我从不费力看。我一定是个白痴。”因此,紧张感通常可以通过改变一种信念来解决。
然而,重要的是,哪些观念发生了变化。一个人想认为,应该总是被证明是错误的信念。如果我们对经验现实的问题错了-我们最终面对了证据-似乎最容易的是,通过改变我们现在有充分理由怀疑的信念,使我们的信念恢复和谐。但这并不总是会发生。调整信念集的方法有很多,有些是合理的,有些不是。
1957年,莱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出版了他的开创性著作《认知失调理论》,其中提出了这样的想法,即我们寻求信念,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和谐,并在失衡时经历心理不适。在寻求解决方案时,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保持我们的自我价值感。
在一个典型的实验中,费斯廷格给受试者一个非常无聊的任务,为他们付1美元,有些付20美元。完成任务后,要求受试者告诉执行任务的人他们觉得这很有趣。 Festinger发现,报酬为1美元的对象报告的任务比报酬为20美元的对象更加有趣。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自我受到威胁。什么样的人会花一美元去做一个毫无意义,毫无用处的任务,除非它真的很有趣?为了减少不和谐,他们改变了对这项工作很无聊的信念(而那些支付20美元的人对为什么这样做并不抱幻想。)在另一个实验中,费斯廷格让受试者持有抗议标志,理由是他们实际上不相信。这样做之后,受试者开始觉得原因实际上比他们最初认为的要有价值。
但是,当我们投入更多的资金而不只是执行无聊的任务或举着牌子时,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在某件事上采取公开立场,甚至奉献一生,后来才发现我们被骗了怎么办?费斯汀格在《末日崇拜》一书中对此现象进行了分析,他在其中报道了一个名为“寻求者”的组织的活动,该组织相信他们的领导人多萝西·马丁可以向即将救援的外星人传达信息。在世界于1954年12月21日终结之前。在卖掉所有财产后,他们在山顶上等着,才发现外星人从未露面(当然世界也没有终结)。认知失调一定是巨大的。他们是如何解决的?桃乐丝·马丁(Dorothy Martin)很快向他们发出了一个新信息:他们的信仰和祈祷是如此有力,以至于外星人决定取消他们的计划。寻求者拯救了世界!
从外面看,很容易将这些视为易受骗的傻瓜的信仰,但是在费斯廷格和其他人的进一步实验工作中,证明了我们所有人都在某种程度上遭受认知失调。当我们加入距离太远的健身俱乐部时,可以通过告诉我们的朋友锻炼非常紧张来证明购买的合理性,我们只需要每周进行一次;当我们未能达到想要的有机化学成绩时,我们告诉自己,我们并不是真的不想去医学院。但是,认知失调的另一方面也不应被低估,那就是当我们被其他相信我们所做的相同事情的人包围时,这种“非理性”的倾向会被强化。如果只有一个人相信“末日邪教”,那么他或她可能会自杀或躲藏起来。但是,当别人误解了信念时,有时即使是最不可思议的错误也可以被合理化。
所罗门·阿施(Solomon Asch)在其开创性的1955年论文“观点和社会压力”中,证明了信仰具有社会方面的内容,因此,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的信念与那些信念不和谐,我们甚至可以低估自己的感觉证据。在我们周围。简而言之,同伴压力有效。正如我们在自己的信念中寻求和谐一样,我们也在与周围的人的信念中寻求和谐。
在他的实验中,阿施(Asch)召集了七到九名受试者,除了一个人以外,所有其他人都是“同盟”(即他们“参与”了实验中会发生的欺骗)。唯一不在实验中的人是唯一的实验对象,他总是被摆在桌子的最后一席。实验涉及向受试者显示一张卡片上有一条线,然后显示另一张卡片上有三条线,其中一条的长度与另一张卡片上的长度相同。第二张卡上的其他两行的长度“基本上不同”。然后,实验者走到小组周围,让每个受试者大声报告第二张卡上的三行中的哪一行与第一张卡上的行相等。在最初的几次试验中,同盟国报告准确,实验对象当然也同意了。但是后来事情变得有趣了。联盟开始一致报告,一个明显错误的选择实际上等于第一张牌上的线的长度。当问题出现在实验对象上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心理张力。正如Asch所描述的:
他所处的位置是,尽管他实际上给出了正确的答案,但他却意外地发现自己只占少数,而就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而言,却遭到一致和任意多数的反对。我们在他身上施加了两种对立的力量:他的感官证据和一群同龄人的一致意见。
在宣布答案之前,几乎所有以不谐调为基础的受试者看起来都很惊讶,甚至令人难以置信。但是随后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其中的百分之三十七屈服于多数意见。他们低估了眼前的景象,以保持与团体的一致。
Peter Cathcart Wason在1960年完成了另一项关于人类非理性的关键实验工作。沃森(Wason)在他的论文“关于在概念任务中消除假设的失败”中采取了许多步骤中的第一步,以识别人类在推理中经常犯的逻辑错误和其他概念性错误。在第一篇论文中,他介绍了(后来又命名为)一种想法,在真相后的辩论中几乎每个人都可能听说过:确认偏差。
沃森的实验设计非常优雅。他为29名大学生提供了一项认知任务,根据经验证据,他们将被要求“发现规则”。沃森(Wason)用三个数字系列(例如2、4、6)向受检者展示了他们的任务,并说他们的任务是试图发现生成该规则所使用的规则。要求受试者写下自己的三个数字,然后实验者会说出他们的数字是否符合规则。受试者可以根据需要多次重复执行此任务,但被指示在尽可能少的试验中尝试发现该规则。对于可以提出的数字种类没有任何限制。当他们准备就绪时,受试者可以提出自己的规则。
结果令人震惊。在29个非常聪明的受试者中,只有6个提出了正确的规则,而没有任何先前的错误猜测。十三项提出了一个不正确的规则,九项提出了两个或更多不正确的规则。一个受试者根本无法提出任何规则。发生了什么?
根据Wason的报告,未能完成任务的受试者似乎不愿意提出任何数字来检验其假设规则的准确性,而只提出那些可以证实其假设的数字。例如,给定系列2、4、6,许多受试者首先写下8、10、12,然后被告知“是的,这遵循规则”。但是后来有些人只是继续按偶数以2的升序进行运算。他们并没有利用他们的机会来查看他们的“以两个为间隔增加”的直观规则是否不正确,而是继续只提出确认实例。当这些受试者宣布他们的规则时,他们震惊地得知这是不正确的,即使他们从未用任何可证明的实例对其进行过测试。
此后,有13位受试者开始检验他们的假设,并最终得出正确的答案,即“三个升序排列的数字”。一旦他们摆脱了“确认”的心态,他们便愿意接受这样的想法,即可能会有不止一种方法来获得原始的一系列数字。但是,这不能解释给出两个或更多错误规则的九个受试者,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们的提议是错误的,但仍然找不到正确的答案。他们为什么不猜到9、7、5?沃森(Wason)在这里推测:“他们可能不知道如何尝试自己伪造规则;或者他们可能知道如何做,但仍然发现它更简单,更确定或更放心,可以从实验者那里得到直接的答案。”换句话说,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认知偏见牢牢地抓住了他们,他们只能为正确的答案而ail惜。
所有这三个实验结果-(1)认知失调,(2)社会整合和(3)确认偏差-显然与事后真相相关,因此,如此多的人似乎倾向于在理性和道德规范之外形成自己的信念。良好的证据标准,支持他们自己或同伴的直觉。
然而,在1950年代甚至1960年代都没有出现真相。它等待着其他一些因素的完美风暴,例如极端的党派偏见和2000年代初期出现的社交媒体“孤岛”。同时,还有更多令人震惊的认知偏见证据,尤其是“逆火效应”和“邓宁-克鲁格效应”,两者都植根于这样一个观念,即我们希望成为真实的事物可能会使我们对实际上是真的-继续曝光。
在过去,也许我们与他人的互动减轻了我们的认知偏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当今的媒体泛滥中,与我们的祖先被迫在其部落,村庄或社区的其他成员之间生活和工作相比,我们可能与相反的观点更加孤立,而他们不得不相互影响以相互影响。获取信息。当我们彼此交谈时,我们会忍不住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观点。甚至有经验工作证明了这对于我们的推理可以具有的价值。
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他的《信息世界》一书中讨论了这样一个想法,即当人们互动时,有时他们可以达到一个结果,如果每个人单独行动,他们都会望而却步。称之为“整体大于其各个部分的总和”效果。桑斯坦称其为“互动团体效应”。
在一项研究中,J。C. Wason和他的同事们汇集了一组主题来解决逻辑难题。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很少有受试者能够独自完成。但是当问题后来交给小组来解决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人们开始质疑彼此的推理,并思考他们的假设错了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似乎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结果,研究人员发现,即使没有一个成员可以单独解决一个问题,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小组也可以解决问题。 (重要的是要注意,这不是由于“房间里最聪明的人”现象引起的,一个人想出了这一点,然后告诉小组的答案。而且,这不仅仅是“人群拥挤”的影响,依靠被动多数意见。只有在小组成员彼此互动时才能发现这种影响。)
对于Sunstein来说,这是关键。小组胜过个人。互动的协商小组胜过被动的小组。当我们开放想法进行小组审查时,这为我们提供了找到正确答案的最佳机会。当我们寻找真相时,批判性思维,怀疑态度以及让我们的思想受到其他人的审查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要好。
然而,如今,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选择性互动。无论我们的政治说服力如何,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可以生活在“新闻孤岛”中。如果我们不喜欢某人的评论,可以将其取消好友关系或将其隐藏在Facebook上。如果我们想了解阴谋理论,那么我们可能有一个广播电台。这些天来,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与已经同意我们的人在一起。一旦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就不会有更大的压力来调整我们的意见以适应这个群体吗?
所罗门·阿施(Solomon Asch)的工作已经证明了这是可能的。如果我们是自由主义者,如果我们在移民,同性婚姻和税收方面与大多数朋友达成协议,但我们对枪支管制不是很确定,我们可能会感到不自在。如果是这样,我们可能会付出可能改变我们观点的社会代价。在某种程度上,这并非是关键互动的结果,而是希望不冒犯我们的朋友,这可能不是一件好事。称之为互动小组效应的阴暗面,我们任何曾经担任陪审团成员的人都可以描述:当我们的观点与同胞的观点一致时,我们会感到更加自在。但是,当我们的同胞错了怎么办?不管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我们谁都没有对真理的垄断。
我在这里并不是在暗示我们接受错误的对等,或者说真相可能介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真理与错误之间的中间点仍然是错误。但是我建议,在某种程度上,所有意识形态都是发现真理的过程的敌人。研究人员也许认为是正确的,即与保守派相比,自由派对“认知的需求”更大,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派应该自鸣得意或者认为他们的政治本能是事实证据的代名词。在Festinger,Asch和其他人的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意识形态整合的危险。结果是,即使我们眼前的证据告诉我们,我们所有人都有内在的认知偏见来同意周围其他人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重视群体的接受,有时甚至超过现实本身。但是,如果我们关心真理,就必须与之抗争。为什么?因为认知偏见是后真理的理想先兆。
如果我们已经有动力去相信某些事情,那么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的心思就可以相信他们,特别是如果我们关心的其他人已经相信了。我们固有的认知偏见使我们有被议程推动的人操纵和利用的时机成熟,特别是如果他们可以抹黑所有其他信息来源的话。正如无法逃脱认知偏见一样,新闻孤岛也无法抵御后真理。危险在于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连接的。我们都信奉我们的信息来源。但是,当他们准确地告诉我们我们想听的内容时,我们尤其容易受到伤害。
李·麦金太尔(Lee McIntyre)是波士顿大学哲学与科学史中心的研究员。 他是几本书的作者,其中包括“黑暗时代:人类行为科学的案例”,“科学态度:从拒绝,欺诈和伪科学中捍卫科学”和“后真理”。 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