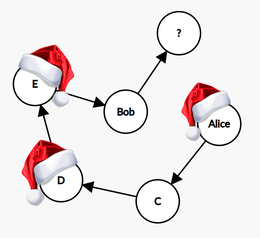Martin ScorseSeess认为将算法贬值贬值电影进入“内容”
在不间断运动中的相机是在一个年轻人的肩膀上,青少年迟到的,专注于繁忙的格林威治村通道。
在一只手臂下,他携带书籍。在他的另一只手中,村庄的声音。
他快速地走了,过去的男人在外套和帽子上,围巾的女性在他们的头上推动可折叠的购物车,夫妇握着手,诗人和喧嚣,音乐家和威斯威人,过去的药店,酒类商店,德利斯,公寓楼。
但这位年轻人在一件事上归零:艺术剧院的大面条,正在玩John Cassavetes的阴影和Chabrol的Les表兄弟。
他做了一个心理票据,然后穿过第五大道,一直走路,过去的书店和纪录商店和录音室和鞋店,直到他到达第8街游戏屋:起重机是飞行的,广岛和吉安娜·戈德德的飞行气喘吁吁即将推出!
我们留在他身上,因为他在第六大道左转,并冒着过时的用餐和更多的酒商店和报摊和一家雪茄店,并穿过街道,享受浪漫的马奎灰烬和钻石。
他在华盛顿广场南部的西区4号水壶削减了东边的东部,其中一个人穿着螺纹衣服的男人们发出了传单:乌龟·埃克伯格,而拉迪斯维塔在百老汇的合法剧院开口,在百老汇机票价格上有预留座位!
他沿着拉瓜迪亚广场(LaGuardia Place)步行到布莱克(Bleecker),经过村庄大门和痛苦之地(Bitter End)到达布莱克街电影院(Bleecker Street Cinema),这部电影通过《黑暗的玻璃杯》,《弹奏钢琴演奏家》和《二十岁的爱情》进行放映-拉诺特连续第三次举行月!
他排队观看《特鲁弗》电影,打开他的《电影配音》部分的电影副本,从页面上跳下来的聚宝盆和漩涡围绕着他-《冬季之光》。 。 。扒手。 。 。第三情人。 。 。陷阱中的手。 。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放映。 。 。猪和战舰。 。 。 Anthology电影档案馆的Kenneth Anger和Stan Brakhage。 。 。勒·杜洛斯(Le Doulos)。 。 。在这一切之中,隐约可见的比其他更大:约瑟夫e。 levine赠送了federico fallini的8½!
当他细细浏览页面时,摄像机在他和等待的人群中崛起,仿佛在他们激动的浪潮中。
随着电影艺术的价值被系统贬值,边缘化,贬低并缩小到最低的共同标准,即“内容”,闪到了今天。
直到15年前,人们才开始认真讨论电影时才听到“内容”一词,并且与“形式”进行对比和衡量。然后,逐渐地,接管媒体公司的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它,其中大多数人对艺术形式的历史一无所知,或者甚至足够关心以至于他们认为应该这样做。 “内容”成为所有运动图像的商业术语:戴维·利恩电影,猫录像带,超级碗广告,超级英雄续集,系列剧集。当然,它与剧院体验无关,而与家庭观看相关,而在亚马逊已经取代实体店的流媒体平台上,它已经超过了电影观影体验。一方面,这对电影制片人(包括我自己)来说是一件好事。另一方面,它造成了一种情况,即一切事物都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呈现给观看者,这听起来很民主,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根据您已经看过的内容通过算法“建议”进一步观看,而建议仅基于主题或体裁,那么这对电影艺术有什么作用?
策展不是非民主的或“精英主义”的,这一术语现在已经被广泛使用,以至于变得毫无意义。这是一种慷慨的举动,您可以分享自己的爱和激发您灵感的事物。 (最好的流媒体平台,例如Criterion Channel和MUBI,以及传统渠道,例如TCM,都是基于策展的-它们实际上是策展的。)根据定义,算法是基于将观看者视为消费者的计算,而不是任何东西别的。
六十年代格罗夫出版社(Grove Press)的发行商(例如Amos Vogel)所做的选择不仅是慷慨的举动,而且常常是英勇的举动。丹·塔尔伯特(Dan Talbot)是一名参展商和程序员,他创办了《纽约客电影》(New Yorker Films),以发行他所钟爱的电影贝托鲁奇(Bertolucci)的电影《大革命前》(Before The Revolution),这并不是一个安全的选择。由于这些以及其他发行商,策展人和参展商的不懈努力,来到这些海岸的图片。从戏剧经验的重要性到对电影可能性的共同兴奋,那一刻的情况永远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回到那些年代。我很年轻很年轻,还活着,并且对一切都敞开心feel。电影一直以来都远远超过内容,而且现在将永远如此。这些电影从世界各地发行,彼此交谈并每周重新定义艺术形式的年代就是证明。
本质上,这些艺术家一直在努力解决“什么是电影?”这一问题。然后将其扔回去,以便下一部电影回答。没有人在真空中操作,每个人似乎都在回应并以其他人为生。 Godard和Bertolucci,Antononini和Bergman和Imamura,Ray和Cassavetes以及Kubrick和Varda和Warhol都在通过每次新的摄影机动作和新的剪辑来重塑电影院,而诸如Welles和Bresson,Huston和Visconti之类的知名电影制片人则为电影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他们周围的创造力。
在这一切的中心,有一位所有人都知道的导演,一位艺术家的名字是电影的代名词以及它的作用。这个名字立刻引起了人们对世界的某种风格和态度。实际上,它成为一个形容词。假设您想在晚宴,婚礼,葬礼或政治大会上描述超现实的气氛,或者就此而言,整个星球的疯狂-您要做的就是说“ Felliniesque ”,人们完全知道您的意思。
在60年代,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不仅仅是电影制片人。像卓别林,毕加索和甲壳虫一样,他比自己的艺术还要大。在某种程度上,这不再是关于这部电影或那部电影的问题,而是所有电影的结合都是在银河系上书写的宏伟姿态。去看费里尼的电影就像去听卡拉丝唱歌,奥利维尔表演或努雷耶夫跳舞一样。他的电影甚至开始使用他的名字-Fellini的Casanova Fellini Satyricon。电影中唯一可比的例子是希区柯克(Hitchcock),但这是另一回事:品牌,本身的流派。费里尼(Fellini)是电影院的专家。
到现在,他已经走了近三十年了。他的影响力似乎渗透到整个文化中的那一刻已经很久了。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受欢迎的Criterion盒子套装Essential Fellini于去年发布,以纪念他的诞辰一百周年。
费里尼的绝对视觉掌控力始于1963年的8½,其中照相机在内部和外部现实之间盘旋,漂浮和so翔,以适应由马塞洛·马斯特罗亚尼(Marcello Mastroianni)扮演的费里尼的另一自我圭多的转变心情和秘密思想。我看到那张照片中的段落,我回想起不计其数的次数,但仍然发现自己在想:他是怎么做到的?每个动作,手势和一阵阵风似乎如何完美地融入到位?就像在梦中一样,这一切感觉如何变得不可思议和不可避免?每一刻如何充满无法解释的渴望?
声音在这种情绪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费里尼(Fellini)在声音方面和在图像方面一样富有创造力。意大利电影院有着悠久的不同步声音传统,始于墨索里尼(Mussolini),他命令所有从其他国家进口的电影都必须配音。在许多意大利图片中,即使是一些很棒的图片,外在声音的感觉也会令人迷惑。费里尼(Fellini)知道如何使用这种迷惑作为表达工具。他的图片中的声音和图像不断播放并相互增强,从而使整个电影体验像音乐一样移动,或者像巨大的滚动卷轴一样移动。如今,人们对最新的技术工具及其能做什么感到眼花azz乱。但是,更轻巧的数码相机和后期制作技术(例如数字缝合和变形)并不能为您制作电影:这取决于您在创建整个图片时所做出的选择。对于像Fellini这样的最伟大的艺术家来说,没有什么东西太小-一切都很重要。我敢肯定,他会为轻巧的数码相机而激动,但是他们不会改变他美学选择的严格性和精确性。
重要的是要记住,费里尼是从新现实主义开始的,这很有趣,因为他从许多方面来代表了它的对立面。他实际上是与导师罗伯托·罗塞利尼(Roberto Rossellini)合作发明新现实主义的人之一。那一刻仍然令我惊讶。它是电影中如此之多的灵感,我怀疑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所有创造力和探索是否会在没有新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发生。这并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一群电影艺术家对他们国家生活中一个难以想象的时刻做出了回应。经过二十多年的法西斯主义,经过如此残酷,恐怖和破坏之后,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国家,人们是如何进行下去的?罗塞利尼(Desica)和德西卡(De Sica)和维斯康蒂(Visconti)和扎瓦蒂尼(Zavattini)和费里尼(Fellini)等电影,美学,道德和灵性紧密缠绕在一起,以至于无法分离,在意大利的救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
Warning: Can only detect less than 5000 characters
我觉得我从自己的生活中了解这些家伙,我自己的邻居。我甚至认识到一些相同的肢体语言,同样的幽默感。事实上,在我生命中的某一点,我是这些家伙之一。我明白了Moraldo正在经历的事情,他绝望地走出来。 Fellini捕获了这一切,如此不成熟,虚荣,无聊,悲伤,寻求下一个分心,令人震惊的下一个兴奋。他赐给了我们温暖和戏剧和笑话和悲伤,也是内心的绝望。我vitelloni是一个痛苦的抒情和苦味般的薄膜,这是平均街道的关键灵感。这是一个关于家乡的一部很棒的电影。任何人的家乡。
至于8½:我每个人都在那些试图制作电影的那些日子里,一个人的转折点,一个个人的印石石。我的是,仍然是8½。
在你拍了像La Dolce Vita以风暴带来世界的照片之后,你做了什么?每个人都挂在你的每一个词上,等着看看你接下来要做什么。这就是在金发女郎金发女郎的中期六十年代中发生的迪伦发生了什么。对于Fellini和迪伦来说,情况是一样的:他们触动了一群人,每个人都觉得他们知道他们,就像他们理解他们,而且,通常,他们就像他们拥有它们一样。所以,压力。来自公众的压力来自粉丝,来自批评者和敌人(以及粉丝和敌人经常觉得他们是一个人)。产生更多的压力。压力进一步。来自自己的压力,你自己。
对于迪伦和家庭式,答案是向内冒险。迪伦以托马斯·默顿的精神意义寻求简单,他在伍德斯托克摩托车事故发生后发现了它,在那里他录制了地下室胶带,为约翰·韦斯利的歌曲写了歌曲。
BERENI在六十年代初开始与他自己的情况,并制作了一部关于他艺术故障的电影。在这样做时,他对未知领土进行了风险探险:他的室内世界。他的改变自我是Guido,是一名着名董事,遭受了作家块的电影等同物,他正在寻求避难,以获得和平和指导,作为艺术家和人类。他在一个豪华的水疗中心寻找“治愈”,他的女主人,他的妻子,他的焦虑制作人,他的潜在演员,他的船员以及球迷和衣架的杂散游行,以及同胞们和同胞们迅速下降 - 其中是一名评论家,宣布他的新剧本“缺乏中央冲突或哲学前提”,金额为“一系列无偿剧集”。压力加剧,他的童年记忆和渴望和幻想意外地通过他的日子和他的夜晚来了,他等待他的缪斯 - 谁来,稍曾经是克劳迪娅Cardinale的形式 - “创建命令”。
8½是由Fellini的梦想编织的挂毯。与在梦中一样,一切似乎良好,在一方面镶有漂浮,另一方面漂浮和短暂的;音调保持转移,有时会猛烈地。他实际上创造了一种可视的意识流,使观众保持在惊喜和警觉状态,以及一种不断重新定义自己的形式。你基本上看着Fellini在你眼前制作电影,因为创造性的过程是结构。许多电影制作人试图沿着这些线路做某事,但我不认为别人曾经已经实现过Fellini在这里做了什么。他有宣誓和与每种创意工具一起玩的信心,将图像的塑料质量延伸到某个点似乎存在于某些潜意识水平上。即使是最看似的中立框架,当你真正仔细看看时,在照明中有一些元素,或者将你抛出的组合物,这是某种方式融入了Guido的意识。过了一会儿,你停止试图弄清楚你是哪里,无论你是在梦想还是闪回或只是简单的现实。你想迷路,并徘徊在Fellini,向他的风格投降。
图片在一个场景中到达了一个山顶,其中Guido遇到了浴室的红衣主教,这是一个到黑社会的旅程,寻找甲骨文,并返回到我们所有源自的粘土。在整个图片中,相机处于运动焦躁不安,催眠,漂浮,始终朝着不可避免的东西,一些引人入胜的东西。正如Guido让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