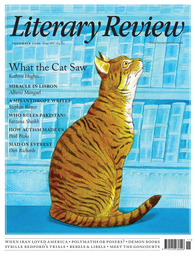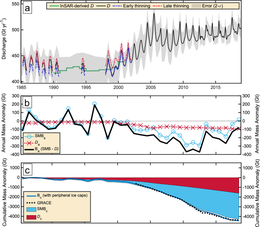大气变化:气象和卡姆斯
我住的城市仍然有时被称为没有幻想的城市。除了和狗一起散步,我几周没有离开房子。在水牛的时间迟缓,但是水仙花芽已经开始肥胖,由过去的日子推动。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检疫春天的开始,每周都会堆积。我正在截止日期,完成我的Albert Camus的瘟疫翻译,这是一个在大流行前委托的项目。 4月将Life和Fictime带入LockStep-in Upstate纽约,以及在我的桌子上的瘟疫小说中,春天只是故事的开始,崛起一定的恐慌。
“肥胖的云从一个地平线跑到另一个地平线上,”卡姆斯写道,“覆盖着与寒冷的寒冷,金色的灯光的阴影的房子覆盖着房屋。”在瘟疫中,天空是一个主角,墙壁和人们在他们之间拔下一场战争,一个难以无穷无尽和障碍的难题。正如Tarrou所说的那样,他们被困在“天空和他们城墙之间”。走在自己的街道上,我注意到人们的情绪是根据天气的第一次改变,邻居站在街角,仰望云。昨天,我越过街道避开阴影方。然后我注意到几乎所有其他行人都采取了相同的行人,向上移动了六英尺,在同一个城市的天空泡沫下。
因为公园挤满了,我去公墓,我知道的几个人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偶尔将在坟墓的过道中努力进入一个朋友,好像这是一个正常的地方,就像超市或繁忙的街道一样。在大流行中,死亡的路径已经重新推出到城市的其他绿地。这是水牛的一个地方,没有警报器,每个人都脱离了危险。墓地里有盛开的树木,鹿与遗传突变变成毛皮。但我只是为了观看运动的戏剧 - 在闪闪发光的领域滑动的云阴影。
这些是巨大的扫描,温暖的前线覆盖数百英里,但它们也是可预测的,雷达屏幕上的亮绿像素的甲骨文。我一直喜欢在不确定性的时刻检查天气。随着孤立通行证的几周,我发现我的猜测味道消失了。未来几个月的未知已经磨损了。我想记住草刀片,慢泉阳光,鹿蹄的两个杏仁,压在泥的泥里。我很遗憾;我不想失去悲伤有时借给世界的原始清晰度。站在树中,用他们的霓虹灯群新生儿花粉,我担心如果我不选择这次怎么记得,那么这种流行病将成为潜潜的东西,压制进入我的肌肉,像习惯一样编码进入我的身体。
但我们真的可以选择我们记得的东西 - 或者只写下我们写下的东西?在瘟疫中,叙述者Rieux包括几乎所有纪事的天气的描述。他标志着天空,就像某种水手一样,在一刻钟的帆船上航行,在云时钟中的缺口时间,其手是风和太阳。并且在一个意义上,他是追随传统。许多早期的瘟疫慢朗乐队还注意到了天气,因为被认为风和蒸气被认为是疾病的载体。奥兰的毁灭性的记录1849霍乱疫情也不例外。 “气氛繁琐地徘徊,”在他的账户中开始了奥兰大教堂的大主教,“lecholéra,”
厚厚的雾,几乎不断地传递,使温度更加努力,尽管赛季的迟到了,但他们仍然坚持;空气用湿度浸透,真正的热量热量是吸引能量,软化勇气,刺激性的思维,推动每个人都陷入困境,使令人难以置信的祸害。 1 1. Mathieu Chanoine,“Lecholéra,”La Vierge de L'Oranie AuxixSiècle(Oran:Imprimerie D. Heintz,1900)。由BibliothèqueTationeedefance重新发布。我的翻译。
这种“不健康的湿度”使得城镇的医生从流行病中送出。正如阿克斯特的纪事表演,瘟疫叙事中的气象都不只是描述 - 这也是悬念的源泉,因为天空的呼吸被认为影响疾病的进步。在十九世纪的医学来源中,卡姆斯咨询了他的小说,湿度被引用作为传播瘟疫芽孢杆菌的一个因素,就像“Miasma”或“糟糕的空气”一样。我们现在知道气候和瘟疫传播之间的关系复杂,有时是矛盾的,但在19世纪,流行的观点遵循了一个可怕的简单轨迹:胶质,疾病,死亡。
Warning: Can only detect less than 5000 characters
Sedgwick的辉煌段落揭示了非自愿记忆的运作与人类晴雨表的想法之间的联系。普鲁斯特和他父亲的人物,每天的天气可能是一个不自主记忆的触发,今天的春天自我和前一个春天失去自我之间的比较。天气是每天提醒过去季节的类似时刻,这是酷前的“地调脉动”,我们现在的经历障碍我们过去的回忆。我们在Covid中有多少人体验我们自己的这些时刻,即使是渴望,不和谐的形式?我们中有多少人觉得春天下午的柔软性,不得不强迫我们的身体想到大流行,保持警惕?
2020年4月,我与一群在纽约市的35名医疗专业人士谈到,作为医院填充Covid患者的困扰。对他们来说,很明显,Rieux博士的性格表达了一个以个人的观点而言 - 当他选择写下他的编年史时,一位医生说,他成为集体创伤的声音。在他在阿尔及尔地球物研究所的几年里,卡姆斯本人已成为人类晴雨表的东西。谁更好地在他的虚构中携带那种知识,而不是Rieux博士,敏感的天气和疾病的Chronicler?通过将他的叙述者提供集体声音,卡姆斯将自己与普鲁斯特的奢华个人主义相结合。但卡姆斯也留下了一个问题 - 如何表达情绪,哀悼,绝望和保持集体?他的一个答案是转向瘟疫的天气作为一种集体经验,因为城市的每个人都被困在同一个天空下。在这本书中最令人痛苦的时刻,当Rieux正在努力与他周围的人死亡时,他允许他的内部感受与天气合并,埋葬在城市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自然现象中的个人经验。这些时刻就像微小的纪念碑,卡姆斯锚定天空的运动中的人类悲伤。
礼宾发生后的一天,大云充满了天空。简短的雨雨殴打这个城市;暴风雨的热量跟随这些粗鲁的淋浴。即使海洋也失去了深蓝色,在朦胧的天空下,它采用银色或铁的色调,痛苦地看到。
目前,“瘟疫”一词首先说,卡姆斯与4月的天空直接对比:
医生还在望着窗外。在窗格的一侧,新鲜的春天的天空,另一方面,在房间里仍然被谐振的词:瘟疫。
一个孩子去世后,疲惫的rieux抬头看了,看到了一个床的修复:
热量慢慢地通过榕的树枝逐渐下降。白炽枕套在早晨的蓝天上滑落,使空气更加令人窒息。
在他的妻子死后,Rieux的母亲等待他的反应,但他正忙着学习天空:
她看着他,但他顽固地盯着窗户,因为一个宏伟的早晨在港口上升。
这些时刻代表了极端的感觉,但他们也通过克制来实现他们的情感拉动。当书的镜头扩大到天空中时,它包含了一个悲伤的悲伤,翻译了一个悲伤,这对于一个城市的组织网格和礼貌的普通语言来说太疯狂了。当天气时,表达损失是一种方法,可以将每个人都能看到它 - 某个未完成的,未解决的,未达到。在Rieux的最佳朋友在流行病的第十一小时死后,他得知政府将一座纪念碑献给瘟疫的受害者。但是,管理的公民愈合不是里贾克斯想找到他的悲伤。相反,他爬到俯瞰城市和大海的露台,到他最靠近他的朋友的地方。虽然他站在那里,但他让天气让他想起他与tarrou谈话的夜晚:
寒冷的天空闪耀在房屋上,靠近山丘,星星像燧石一样坚硬。当他和Tarrou已经来到这个露台忘记瘟疫时,这个夜晚没有那么不同。虚张道脚下的大海比已经胜过了一点。空气仍然和光线,放松了带来秋天的温暖风的肮脏阵风。
关于成为历史记录的事情是你总是跨越了过去的写作与未来所需的界限。但是,没有保证未来的读者将有经验,要求思考你所写的内容。走在我的城市周围,从瘟疫的线条留下出现,就像胖子的鲜花,寒冷,金色的灯,温暖的风。我们不能忘记Camus声称在这个编年史中为我们提供了什么 - “他对瘟疫的了解和他的记忆,他的友谊知识和他的记忆,知道温柔和有一天,要记住它。 “这种因悲伤的这种存在是卡姆斯称之为“没有幻想的生活”。我们会在云盖几天后遇到未来的四月并想到我们的检疫步行吗?我们不断将世界翻译成记忆,但我似乎已经校准了我的内部晴雨表以匹配瘟疫的情绪天气。
在最后的寒冷的一天中,随着北风从加拿大吹嘘,顽固地顽固地抵抗太阳的延长弧,我们的朋友和邻居决定通过写下天空在路面上写下天空的描述来对抗他们的机舱发烧。这是一个简短的窗口进入别人如何回忆这些奇怪的日子。我的丈夫写道,白内障天空不能摇晃。我站在那里抬头看,想象一个在天空是白色天鹅绒的春天时,我可能会感到一定的沉重,这是这种大流行的方式统称我们的生活。在一个悲伤的国家经常被谴责,我希望今年不会丢失时间,我们不会回到这些地面街道上的幻想。也许天气会让我们失明。
图像学分:J. M. W. Turner,“海上黄昏的暴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