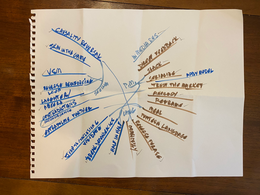绘制孤独的土地
两名男子在一个小帐篷蹲在南极高原,饥肠辘辘地看他们的primus炉炉。没有希望救援,他们试图在他们饿死之前通过两百多百英里的奸诈地形到大型营地。
南极洲南极探险队的成员,他们将在1911年12月左右离开霍巴特,塔斯马尼亚州,于1911年12月,极性勘探的英勇阶段。人群欢呼,彩旗,政治家发表演讲。他们向一个勉强映射的大陆航行,常规计划学习和探索。
1912年11月,经过几个月的具有挑战性的条件,道格拉斯Mawson和Xavier Mertz将探险队的基地留在丹尼森·丹尼森,并在雪橇任务上进行了第三次探险家。他们的目标是在该地区展示一个不受欢迎的南极海岸,被称为乔治·V土地。随着他们的旅程装载在两个守护者上,他们在冰川和风雕刻的冰上取得了良好的进步,在一个月内在一毫秒以上旅行超过三百英里。
Mertz在滑雪板上侦察了滑雪板,第二个诽谤较小的第二个雪橇,听到他身后的一只狗的呜咽。他瞥了一眼。那里什么都没有。他们的伴侣,他的雪橇和他的狗完全消失了。一个巨大的裂缝在似乎,一会儿就像坚实的冰一样。
与他们的朋友失去的雪橇带着主帐篷,铲子,几乎所有的食物。营养不良和憔悴,Mawson和Mertz现在正在沸腾他们最后一条雪橇狗的头骨早餐。
这是我们的船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码头拉开时,这是暮色。我在岸边的灯光和dwindle上看着紫色泡沫的树木,皮革商店的紫色泡沫,梧桐店,带有供应商的山脉拿着“Tomate Lo-Co”的鸽子,鸽子和佛罗里达州的花朵摊位在梅奥广场的流浪狗。
返回Buenos Aires的变暗街道,超越Gran Chaco和Altiplano,超越南美洲,超过五千英里之外,我的丈夫和我们的丈夫失败的婚姻。现在,三个星期,我也会留下这一点。
每一个冬天,我的母亲和继父在南海的探险巡航船上工作,驾驶船和岸之间的黄道带拉船。今年,在最后一分钟,房间为我和我十岁的女儿Jemma打开了,加入了他们在Minerva上的一个巡航。我跳了起来有机会去,而不是远离我的丈夫,而是到这个星球上最寒冷,最遥远的地方。
我们沿着RíodaLata沿着RíodeLaplata的东南部蒸汽,前往南极洲。我以前去过大陆。多年前,我在俄罗斯船上担任南极季节探险领导者的助手。那时我约会了Jemma的父亲,我很敏锐地想念他。使用便携式录像带播放器,当我回到家时,我记录了企鹅殖民地的声音,而且在晚上,我睡在他的红色法兰绒睡衣上面。现在他和我正处于离婚的边缘。
我们在1997年的阳光明媚的六月日结婚,在我的祖父母在长岛南岸的倾斜草坪上。一位歌手朋友唱大赦玛丽亚,因为我走在白色折叠椅之间的草地过道。我们牵着手,看着对方的眼睛,发誓要拥抱并抱着。
玫瑰花瓣在仪式结束时像五彩纸屑一样下雨,后来的烟花爆炸在树上。在我们的蜜月在苏格兰,我们走过黄色毛茛的田野,困扰着我新的丈夫的黑色皮鞋。当我告诉你我们开始希望和美丽时,相信我。我们要写小说,让孩子们一起变老。我们可互换地在我们之间分享相同的宠物名称。
当他哭泣时,我记得一张早晨,“哦,睡觉,你怎么能让她走?!”
当我的丈夫有第一次崩溃时,我们的孩子是两个和四个。他患有未结诊和未经治疗的焦虑症,症状从我身上藏起来,害怕飞行,次粒细胞,侵扰性的想法 - 因为他们让他羞愧和困惑。然后是受感染的蜘蛛咬伤的抗生素课程将他送到了边缘。我通过一系列恐慌的攻击,他的身体痉挛。 “我害怕自己对自己做的事情,”他告诉我。几周,他被禁止,几乎不能下车。最终,在一份药物未能帮助后,另一个初步工作。通过所有的所有,我害怕让他独自一人。
这是新年的1913年,道格拉斯·马蒙试图拉西尔·默兹,现在他唯一的伴侣,从令人眼花缭乱的惯性。陷入困境的天气和默兹·鸡蛋莫尔特的承诺,他们可以在他们回到大地营地的承诺时陷入他们的临时帐篷。无私,他喂ercz是他们狗肉供应的最温柔的碎片。三天后,他们设法包装齿轮并继续穿过危险的冰。他们只让它只有四英里。然后默兹只是停止,无法继续。 Mawson,他自己用饥饿疲惫和削弱,将默兹拖到雪橇上,盖住了他的驯鹿皮睡袋。然后,害怕在锯齿状的风雕刻的冰上失去脚,他跪在他的手上,并在四肢上拉扯雪橇。
那天晚上Mertz呕吐狗肉炖,第二天他自己屎。 “你觉得我没有勇气!”他狂欢。 Mawson手表,令人惊讶的是,默兹将一个冻伤的小指粘在嘴里,咬住咬合咬伤。他吐了泛黄的手指到雪地上。
通过这种自残的行为,默兹安静下来。 Mawson说服他喝了一些珍贵的可可。后来他更猛烈地肆虐,这次打破了一个帐篷杆。马森必须坐在他的胸前来抑制他。他遇到了腹泻的另一个袭击,Mawson再次清理。然后默兹在他的德语鬼尖叫着他的耳朵和坍塌。
在Minerva的酒吧,调酒师将我的女儿混在一起称为椰子吻的小船。很高兴,她在喝一片菠萝和一只小蓝色的伞上喝饮料时旋转在她的酒吧。我的母亲和继父的笑话和故事与他们旅行的朋友一起互化,我试着倾听,但失败,令人失望,令我迫切的离婚如何影响杰马和她的小弟弟。
当我们回到我们的小屋时,房间管家在幻想游行中安排了Jemma的毛绒动物。我们的枕头已经饱满了,我们的白色被藏人拒绝了。 MINERVA刚刚乘坐200岁时,超过150名官员,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他们对我们的每一切需要。我不必为足球夹板做饭或洗衣服或商店,或者让任何人带到牙医。我在时间的海洋中遇到了我的想法。
早上,Jemma用母亲矗立在栏杆上,拍摄了普及的Pintado Petrels和徘徊的信天翁在我们醒来下滑动。无云的天空是蓝色的,阳光照在滚动的灰色肿胀上。无法坐下,我走在上层甲板周围。我的心痛是文字,我的胸部疼痛我每天早上醒来,每天都会携带。我无法想象它越来越好了。这就像我在这一刻困住了我的余生。
我们海上日子的讲座时间表提供了一个受欢迎的分心。我坐在礼堂中,听取船的地质学家解释说,数百万年前,南极洲与南美洲和非洲联系在贡湾的所有部分。然后景观是茂盛和热带的。隐藏在极地冰川下面,整个石化森林,开花植物的化石,猴子拼图树,灭绝的泥浆和鳄鱼样的两栖动物。
没有遗骸。现在它是地球上最寒冷的地方,一个冰盖的冰帽,厚度三英里。而不是树木,有地衣斑块。整个大陆上最大的陆地动物是没有翅膀的飞行。
我们幸福地结婚,据我所知,我丈夫从商务旅行中回家的近12年来令人振奋而遥远。我的第一次思考是他的焦虑药物已经停止了工作。抱着他,当他哭泣时,我试图向他保证。他勉强承认了我。 “发生了什么?”我一直在问。他抱怨,躲避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更多的乐趣。 “你有暧昧吗?”我终于要求了。他冒犯了这一建议。
他花了一个月,让他承认他欺骗了我。
在这忏悔之前,当我知道只是错误的错误时,我曾经等到他睡着了,所以我可以以前的方式把我的手臂放在他身边。在他告诉我之后,他声称他很抱歉。他说,他爱我。他想拯救我们的婚姻。离婚父母的孩子,我决心饶恕特别破裂的孩子。我告诉自己必须有一种回馈我们以前的爱和亲密的方式。我紧紧抓住我们可以再达到它的希望。我们去了夫妻治疗,并阅读了我们的治疗师推荐的自助书。
但是我们的婚姻感觉像一个充斥的镜子,它的每一个熟悉的方面现在都扭曲和怪诞。我不认识我在这种寒冷的偏远陌生人结婚的男人。随着恐惧和羞耻瘫痪,他似乎无法回答我的任何问题。他想要什么?为什么他没有告诉我他不开心?所有他抱怨的只是我在车里唱歌。当他谈话时,它是为了坚持他是“一个好人”。当我谈话时,他记了笔记。一天晚上在一家餐馆,在治疗师推荐的“日期”,我开始哭了。他没有伸出援手,或者说什么来安慰我。在他面前的纸上我看着他写下了泪水。
在他手上跪在雪地上拉扯雪橇后的时间,Mawson在黑暗中醒来,发现默兹在他旁边的睡袋里死了。他的身体已经冷了。 Mawson位于他朋友的尸体旁边的帐篷里几个小时。 “他的凡人框架,”他写道,“在他的睡袋里切换,仍然提供了一些友谊感。”
在南极之夜迷失了,Mawson走过这一刻的一切。他知道他在荒凉的广阔时尚的生存机会是多么苗条。 “我似乎独自站在世界的宽阔的海岸上......似乎很少希望......睡在包里很容易睡觉,外面的天气很残酷。”
但他讨厌浪费的所有努力的想法。最终,他迫使自己爬出睡袋,并在雪的街区下埋葬默兹。他refashions更容易举起。他尽可能地修复受损的帐篷原则。
然后是大风命名。三天他打架只是让帐篷吹走。他的冰霜手指变黑和裂缝。当他将裤子降低到排便时,皮肤落在雪中。 “我的整个身体正在腐烂,”他写道。
当大风在最后一个消退时,Mawson继续穿过雪地和冰朝着极光峰值。他不希望生存,他只是希望有一天待找到的遗体,以及图表和调查他和默兹所做的和他写作的杂志。
当他在他的脚上感到鲜味的疼痛时,Mawson令人震惊的冰山上。坐在雪橇上,他去除他的靴子。他的脚底就离开了。惊呆了,他把它们抱在手里。他实际上崩溃了。
他能做什么?他将脚的鞋底带回原料组织的绷带,拉在他离开的每一副袜子上,并保持走路。
有时候我觉得像一个人类的蜡烛,愤怒像威克一样燃烧我。其他时候,从蓝色中,一波温柔会击中我。一天早上,我注意到我丈夫的胸部上的灰色毛,想到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有多年轻,我们都在一起。他从未经治疗的疾病中遭受了如此之多。我告诉自己,我必须找到一种原谅他的方法。我读了我们的旧情书,研究了我们在镜头上微笑的照片,彼此搂着。
然后另一个谎言会表面。他欺骗了大而小的事情:例如,他的手机计划,例如,他和他一直在欺骗我的女人。关于他的信用卡一系列神秘收费。有一天,他告诉我他想感受到我的痛苦。这是假装和陈词滥调的。我说,“敲开自己。”我的愤怒感觉像酸的酸,尖塔;我永远不能把它放下。我不得不以最大的照顾携带它,因为如果我洒了它,我们整个房子都会溶解。一旦我抓住了他的肩膀并摇晃着他,说:“我想要比你更好的人。”
我们的婚姻需要八个月才能完全分解。它发生了艰苦的。没有什么清洁或清晰的。我们从美丽开始,但结束是凌乱和痛苦的,充满羞辱和失败。
一天晚上,在Minerva上,我梦想着我拿着一个牛排的大型玻璃碗。碎片飞到我的怀里。我一个人,没有人帮助我;我知道我必须自己拉碎片。但是在我看,我的皮肤开始接近锯齿状的碎片,在肉体中嵌入肉体中。
我们的情侣治疗师认为,婚姻自然地发展朝着情绪僵局。焦虑,脆弱性,需要面对自己最糟糕的品质:这些是婚姻景观的正常特征。通过他们的工作是我们如何单独和一起成长。 “婚姻是一个坩埚,”她坚持。
安东·契诃夫乐观较少。 “如果你害怕寂寞,”他建议,“不要结婚。”
想要从自助中休息,我拿起来自船库的南极探险史的书籍。作为逃避,极地冒险的故事造成严峻的票价。我被每次远征开始的热情,如何充满高尚的承诺,那么其中有多少失败。注定的探险家的日志在结束时看得很多。在1880年代,北极的一名成员在二十五名男子死亡中观看了十九岁。 “天哪!这一生是可怕的,“他写道。 “这种持续的痛苦和死亡会不会改变吗?”后来,在5月底的大暴风雪期间:“在我生命中的所有日子里,... [没有]与我在过去几个小时里承担的折磨相比。”
在不同的北极航行中,乔治·德龙和他的船员在被困在冰上后抛弃了他们的船。他们希望通过白斑地区到达北极。相反,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偏远海岸上洗了。 “晚餐在5点晚餐 - 半磅狗和茶,”他写道。 “我们不能对抗风,并留在这里意味着饥饿。”
从亚太郡凯瑞 - 戈尔德旅行的亚洲山区的南极洲之旅,南极洲冬天的皇帝企鹅蛋鸡蛋中:“这种痛苦的痛苦就无法衡量。”他和他的两位同伴失去了暴雪中的帐篷,在冻结的睡袋里蜷缩在冰箱睡袋里,无法吃或喝酒,唱着偶尔的歌来保持他们的烈酒。他们每隔几个小时互相戳戳,以确保他们还活着。
罗伯特·猎鹰斯科特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找到南极之后,在找到Amundsen的挪威国旗已经种植的南极之后:“遗憾地说,从不好变得更糟......我们无法互相帮助,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要做的要做他自己。“然后,“看起来非常黑的东西确实。”
男人的痛苦延伸在景观,景观,难以想象,无目的。首先,他们被迫吃狗,然后是他们的驯鹿皮靴。他们看着他们的同伴死了,然后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缩小了他们自己。所有这些名气和科学进步的愿景,船舶和设备,图表和计划最终降低了。
在Grytviken在南佐治亚州的南部南极岛上,我们停在捕鲸船的墓地,以向其中一个南极伟大,Explerer Ernest Shackleton。当船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Shackleton对南极洲的探险失败之前,我们站在他的坟墓里,他在达到土地之前,他的船耐力被海冰击碎。为了拯救他的男人,Shackleton在一艘小船中穿过暴风雨的德雷克段落,然后越过了南乔治亚未开发的山脉,以便到达东方的捕鲸站。征集捕鲸船队的帮助,他回到了大象岛,挽救了他的船员的每个成员。
这个顽固的拒绝扔进毛巾,我抬起朗姆酒冲头的塑料翻倍。 jemma抬起她的苹果汁。 “到老板,”历史学家说,我们重复,“老板”。
由岸边,年轻的大象密封队在浅滩上争吵,将他们的闪闪发光的尸体互相击球,然后滚动眼睛,因为撞击撞击。 Jemma拍摄了蜕皮王企鹅的挤。她在她生命中有时间,并在她长大时决定成为一个鸟类学家。
当我们离开佐治亚州时,我们通过了开普敦令人失望的人,厨师队伍意识到他刚被发现的土地群众不是一个大陆,但事情令人印象深刻。其他地方名称也唤起了早期探险者的沮丧:欺骗岛,难以接近的极点,荒凉的岛屿。
那天晚上,我的衣柜在我的旁边,我想起了像一个群岛一样的婚姻,我愤怒地映射:更大的焦虑和较小的焦虑,重复性,超越他们的斗篷通奸,在痛苦的半岛上。装入愤怒和痛苦,都是活跃的火山,以及双冰川,诚信和温柔。然后是谎言的岛屿链条,包括大谎言和众多小谎言。在伤害的海洋中,过去的虚假希望,躺在外部限制,然后离婚。
“我们无法互相帮助,”Robert Falcon Scott写道。我想到了我的丈夫和我现在来自玫瑰花瓣和毛茛属植物。令人羞耻和自怜唤醒,他无法帮助我。无论我曾经尝试过多么努力,我都无法帮助他。
在你的婚礼上,你朝着一个你试图设想但从未见过的地方的双人远征。后来,你可以在外星人天空下独自醒来,在你身边的一个冰箱尸体。环顾四周,你想知道你是如何在这里来到这里的。你认为,就像斯科特在杆子上,他努力达到和死于“伟大的上帝,这是一个可怕的地方。”
在MINERVA上抄写并宠坏了,我们远离早期探险者的剥夺。只有景观类似于他们的描述。在每个方向延伸了企鹅岛,冰山和冰窒息的海洋。没有房子,不是一辆车,不是一棵树,不是码头,甚至不是另一艘船。 AdéliePenguins从水的光泽表面迸发出来,朝向岸边的流行。这是人类时间和人类关注领域之外的一个地方:一个单独的,独立的世界,闪闪发光。
我们降落在岩石的海滩上,jemma掀起朝向火山煤渣的厚厚的雪。她一直想爬火山,她告诉我。事实上,当她长大时,她想成为一名普凡士。在我们之前,一个使用拐杖的人在他的脚印旁边留下了一系列漏洞。每个穿刺都用蓝色光芒从下面照亮。这既比俄罗斯船上的时间比我记得更美丽又更孤独。我的一部分想要留在这种冷漠中,永远不会结束。
Mawson,由冰上的眩光半蒙蔽,在冰川上的冰川上,与不祥的裂缝和繁荣呼应。他意识到这艘船很快就会为澳大利亚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