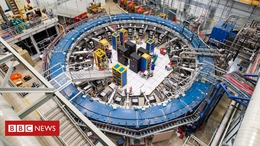听觉的力量:声音定位的军事科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听证会被重新定义为一种战术活动——一种可以决定人类甚至国家生存的活动。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助理战争部长委托撰写的一份高耸报告的前言“战争的结束:图形记录”,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以一声巨响结束,而是如著名诗句中的呜咽声.这张照片在幻灯片上显示了六条水平线,描绘了 1918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11:00 停战前一分钟和后一分钟,摩泽尔河附近美国前线的炮兵活动。左侧描绘停战前一分钟的炮兵活动并显示出一连串锯齿状的线条(“全枪射击”)。在右侧,描绘了停战后一分钟的炮兵活动,只有流畅的线条(“所有枪声”)。 11:01:01 左右两次小幅下跌归因于一个面团男孩为庆祝停火开了两次手枪。除了这些枪声之外,炮兵的活动似乎完全停止了,战场上的枪声顿时变得空荡荡的。 “战争结束”的标题说,这是美国前线炮兵活动的最后记录,图像是从美国测距仪发出的。 “测距,”它写道,“是定位敌方火炮位置和口径的重要手段。”当该图像在《电力杂志》(Journal of Electricity) 上被转载时,有关它的声明甚至更为宏大:“真正的历史在这里是用电写成的!” “战争的终结”是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的众多声学防御方法之一制作的。在战争开始时,声学防御的概念几乎无人知晓。没有一支主要军队拥有通过跟踪敌人发出的声音来跟踪敌人位置的可靠手段。然而,到战争结束时,每个人都开发了新的技术和声音定位技术,通常是为了应对新技术的进攻,并且每个人都在无数场合使用过这些方法——从而产生了新的“声学防御”模式。然而,一种新的进攻武器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新的防御方法就容易获得。据皇家海军志愿预备役中校阿尔弗雷德·罗林森 (Alfred Rawlinson) 称,敌人很容易躲在云层后面。防御的枪应该如何击中他们看不到的物体?他说,答案“非常简单——即,虽然我们看不到它,但我们可以听到它。因此,我们不能用眼睛瞄准,如果我们要射击,就不得不用耳朵瞄准。”尽管如此,他写道,“理论无论多么正确,要转化为实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直到 20 世纪早期,空间听觉几乎都是从声音物理学或听觉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在战争期间,它被重新塑造为一种从战略角度理解的战术活动——可以决定人类甚至国家的生存。听觉空间感知曾经被认为是视觉空间感知的附属,现在被新理解为一项至关重要的技能,“听觉”突然映射到民族国家的权力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第一个声音定位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看到”声音的想法。有些是基于视觉技术,并将源自光学科学的原理转移到声学领域。 1916 年,一位法国陆军中尉设计了一种 viseur acoustique(“声学面罩”),这是一种由镜子和指南针组成的手持设备。一名士兵使用该仪器将他的脸在镜子中的反射居中,这样他就可以同样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耳朵。罗盘然后大概会给出声音的方向。在英格兰进行了使用试听盘的实验,该技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即当隔音盘面向声源时,声像将在圆盘中心与隔音盘相对的一侧形成。声音。这个想法被提出作为光学中阿拉戈光斑的声学模拟,由于光的波动性,一个亮点出现在圆形物体的阴影中心。虽然诸如声学遮阳板和听音盘之类的技术既不是特别有效也不实用,但作为战争中出现的最持久的声学防御技术之一,Baillaud 抛物面也是基于视觉技术的。尽管历史上有声学反射器的例子,但第一个专门为军事用途设计的抛物面声学反射器是由 René Baillaud 在 1915 年发明的,并具有盘子或碗的形式。 Baillaud 是图卢兹天文台的一位天文学家,他在牛顿望远镜上模拟了他的设备。他的设计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抛物面镜无论是反射光还是反射声音,都必须具有相同的反射特性。在贝约的回忆录中,一系列照片展示了声学抛物面经过大约一年的密集实验的发展。我们发现了越来越大的乐器,直径从 60 厘米到 3 米不等;形状各异,使盘子看起来不像凹盘,而更像深碗;和不同的配置,其中包括四个抛物面堆叠成两排。在最大焦点上使用类似听诊器的设备收听的单个审计员变成了两个审计员,他们串联收听,而每个人都坐在设备的两端,使用手轮旋转盘子。我们还发现引入了自动航向绘图仪,这是一种跟踪审计员运动的成像技术,从而产生飞机轨迹的视觉记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用飞机产生了几种声音:螺旋桨的节拍声、发动机声音以及空气与运动飞机机身之间的摩擦引起的振动。然而,最响亮且最容易识别的声音是所谓的“排气音”。各种飞机的排气音在 80 赫兹到 130 赫兹之间,虽然这个音调在飞机运动时有所不同,但始终是低频声音。为了反射飞机的低频声音,各主力军都研制了喇叭声定位器(也称为喇叭声定位器),用可以反射低频声音的大锥形喇叭代替了火炮测距装置的小喇叭。据剑桥大学生理学教授、20世纪初英国防空实验组主任AV希尔介绍,英国陆军研制的第一种小号声音定位器只有一对大号角,其口部直径约 40 英寸。该设备于 1917 年首次用作伦敦防空系统的一部分,只能确定敌机的水平方位。几乎立即开发的第二种型号有两对号角,有时被称为“四小号”或“四号角”声音定位器。一对喇叭用于确定飞机的仰角(高度),而另一对用于确定其水平方位(方位角)。喇叭的“alt-azimuth”安装需要两名审计员,他们从事可能被认为是“双双耳”聆听模式的工作。每个审计员都通过一个类似听诊器的双耳听筒听,该听筒只连接到一组喇叭。一名审计员只听了飞机的高度,而另一名则听了它的水平方位。因此,使用审计员的综合听觉印象来跟踪飞机,这是通过平衡两个耳朵的声级来确定的,这个过程被称为“包围声音”。
四喇叭声音定位器是重型、劳动密集型的设备,需要相当大的努力来运输和使用。此外,通过喇叭声音定位器收听几乎总是在任何实验室都无法复制的不利条件下进行。军事审计员几乎总是在黑暗中运作,这已经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们经常在恶劣的天气和混乱可怕的战斗条件下倾听。众所周知,士兵在战斗中会瞬间耳聋;士兵们回忆说“看到枪手的耳朵在流血”。通过声音定位器收听时,听力受损和听者疲劳是司空见惯的。听众不仅要在陌生和不可预测的环境中从事一项艰巨而繁重的活动,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他有死亡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倾听”是一个极端的命题。鉴于在这种极端条件下聆听的不稳定性质,军事审计员接受了广泛的培训,以培养他们的定向聆听技能。关于声学测角仪(一种法国设备)的军事手册包含有关“声音观察者的培训”和“听众的耳朵培训”的段落。这些段落详细描述了军事审计员必须进行的各种耳朵训练练习才能获得操作声学测角仪的资格- 喇叭声音定位器。声学测角仪听力练习分五个阶段进行。在第一阶段,审计员聆听大约 100 米外的固定声源。助手通过数数、拍手或吹喇叭来提供声音。助理然后侧身移动到另一个点,而审计员则将仪器重新对准他。第一个练习用于消除不可靠的听众。如果审核员的“声学目标”偏离太多,审核员将不被允许进入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助手模仿移动的声源,在以大约每秒一米的速度连续行走时产生连续的声音,距离审计员大约 150 到 200 米。审计员试图通过不断地将测角仪重新对准助手来跟踪声音。一位站在旁听者和助教之间的教官随意吹口哨。在这些点上,助手停止移动,审核员的声学瞄准得到验证。在第三和第四阶段,审核员跟踪实际飞机的声音,首先跟踪其水平方位,然后跟踪其高度。在第五阶段也是最后阶段,两名审计员同时跟踪一架飞机,一名审计员监听飞机的水平方位,另一名监听飞机的仰角。决定审计员“应该每天系统地接受培训”,每天的听力练习“绝对不可或缺”。如果审计师不每天练习,人们认为他“很快就会失去所获得的效率”。战争中机械上最复杂的声音定位器之一是佩兰远距望远镜 (télésitemètre Perrin),它以法国物理学家让·巴蒂斯特·佩兰 (Jean Baptiste Perrin) 的名字命名。其前提是锥形喇叭所能达到的声音放大量必然受到喇叭尺寸和长度的限制。为了增加声音定位器的放大功率而不是其尺寸,Perrin 设计了一个接收器,该接收器将数十个基本喇叭聚集在六角形蜂窝状巢穴中。这些“主号角”通过一套管子连接到中央号角,两名审计员分别通过额外长度的管子进行双耳收听。这个想法是,被称为“myriaphones”的多细胞喇叭组合将使设备能够收集大量声能,而仪器本身可以保持相对较小,因此在运动战的背景下是可行的。
根据 AV Hill 的说法,许多人认为 Perrin 遥测仪比小号声音定位器提供了“更确定的中心位置”,并且使用遥测仪,声音在两只耳朵之间传递的感觉似乎“更加明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一支军事审计专家级,他们感知声音位置和方向的能力成为军事行动中的一项关键资产。在法国,军事审计员每天都接受培训,定向聆听被理解为可以通过听力训练来培养的技能。在声学防御的背景下,“好的倾听者”不一定是听得好的人。相反,一个好的倾听者是能够使用他们的空间听觉来定位和追踪声音来源的人。在战争过程中,声学防御技术变得更加复杂,不仅在其日益复杂的设计方面,而且在它们所需的聆听类型方面。出现了合作和协作的聆听模式,其中涉及几个审计员 - 以及其他团队 - 他们协同工作以感知和解释声学活动。尤其是在战争后期,在声学防御环境中进行聆听显然是一种集体努力。几乎每一种防御性倾听行为都涉及一系列复杂的程序,需要专业知识、多位审计员和其他观察员之间的合作以及人员团队之间的沟通。通过这种方式,聆听变成了一个分散的过程,由许多人分配,每个人都被分配到“聆听行为”的不同部分。同时,倾听行为本身也从个人在日常环境中进行的单一、连续、连贯的行为重新配置为一组由审计人员在极端战争条件下进行的系统化、离散的行为。由于军事审计员的作用是倾听并不断报告他的发现,因此进一步将倾听重新配置为数据收集行为。军事审计员通常不会像声学传感器那样解释声音的含义,而他的角色基本上是观察和报告物理声学数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军事聆听本质上是一项机械任务,预示着当代形式的机器聆听。人类审计师通过制定功能性和高度合理化的聆听模式来执行机器今天执行的功能:声音研究学者乔纳森·斯特恩称之为“听觉技术”的军事化形式。通过声学防御,听力同样被重新配置为感知、观察或视觉绘制声能,而不是仅仅“听到”声音。在一些声学防御方法中,声音的视觉表示以及与声学活动相关的计算——例如确定风和温度等大气条件对特定日期声音传播的影响——取代了听觉。换句话说,在声学防御中,声音“听起来”的方式并不总是很重要。相反,在许多情况下,声音的物理行为才是听力方程式中最重要的部分。如果声音不是被理解为可以听到的东西,而是可以被感知的东西——或者实际上是被观察到的——那么它的定义也必须改变。在战争开始时,声音通常被理解为“某些振动运动对听觉神经产生的影响”,希尔引用了这一定义作为标准。然而,这个定义并不总是适用于声学防御的背景,因为有时需要考虑声音,正如一位军事领导人所写的那样,“不考虑通过耳朵的最终检测。”因此,希尔建议对声音更合适的定义是“听觉器官对其作出反应的那种物质的振动运动”。虽然这当然符合关于声音的成熟想法,但声学防御技术使以有形的方式体验声音作为“物质的振动运动”成为可能。
声学防御同样使“声音传播”的想法具体化。成千上万的人——包括军事审计员,以及许多生活在空中轰炸威胁下的平民——不是面向可见的声音来源,而是面向声音的路径。声学防御使声音移动的想法变得合理,并且通过将自己定位于它的移动,人们可以重新定位历史本身。 Gascia Ouzounian 是牛津大学音乐系副教授,着有《立体声:科学、技术和艺术中的声音与空间》一书,本文改编自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