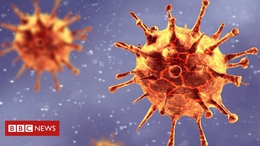辉瑞 Moderna 疫苗研究因安慰剂接受者接受免疫而受到伤害
数以万计自愿参与辉瑞-BioNTech 和 Moderna COVID-19 疫苗研究的人仍在参与后续研究。但一些关键问题不会轻易回答,因为许多曾在安慰剂组中的人现在选择接种疫苗。即便如此,在计划的两年后续研究中仍有有价值的信息。这激励了 56 岁的工作顾问凯伦·莫特 (Karen Mott),他坚持继续学习。 “过去 25 年我一直在服用处方药,”她说,指的是她服用的抗癫痫药。为了证明这些药物有效,以前人们在实验阶段就自愿服用它们,“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回馈的方式。”住在堪萨斯州奥弗兰帕克的莫特对第二针反应强烈,所以她正确地推测她接种的是 Moderna 疫苗,而不是安慰剂。她伤心地读到,安慰剂组志愿者的人做COVID-19的模具。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是幸运者之一?”她说。 “而且我认为这让我觉得,我需要继续提供我们需要的信息。”因此,当诊所在一月份打电话给她并提出透露她的实际疫苗状态时,这对她来说很容易。她同意继续参与为期两年的随访研究。参与者定期提供鼻拭子和唾液样本,以查看他们是否已被感染。他们还提供血液,以便科学家可以更好地了解疫苗如何提供保护。
Mott 是在堪萨斯州莱内萨市一家名为 Johnson County Clinical Trials 的公司接受试验性 Moderna 疫苗的约 650 名志愿者之一。在那里负责这项研究的 Carlos Fierro 博士说,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授权后,每位参与者都被召回疫苗。 “在那次访问期间,我们讨论了各种选择,包括在不接种疫苗的情况下继续研究,”他说,“令人惊讶的是,有人——有几个人——选择了那个。”他怀疑这些人被有关疫苗的谣言吓坏了。但是其他接种安慰剂的人都继续前进并接种了实际的疫苗。因此,现在 Fierro 基本上没有可用于正在进行的研究的对照组。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损失,但鉴于这种情况,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他说。报名参加这些研究的人并没有得到特殊待遇的承诺,但是一旦 FDA 批准了疫苗,他们的开发人员就决定提供疫苗。斯坦福大学临床试验专家史蒂文古德曼博士说,失去这些对照组会使回答有关 COVID-19 疫苗的一些重要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我们不知道保护能持续多久,”他说。 “我们不知道对变异的疗效——为此我们肯定需要一个好的控制臂——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参数是否因年龄、种族或虚弱而有任何差异。”
科学家可能能够推断出其中的一些情况,例如,如果接种疫苗的人在接触病毒变体后通常会生病的情况变得明显。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 FDA 也正在根据数百万人的经验收集更多的安全信息。但是,包括安慰剂组在内的临床试验是收集疫苗有效性信息的最可靠和最确定的方法。 “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得到这些数据,”Fierro 说,即使没有安慰剂组。科学家们已经从疫苗研究中收集了数据,这些数据可以帮助他们确定个人的免疫系统对疫苗接种的反应。这最终可以让他们识别免疫系统特征,称为保护相关性,可以强烈表明疫苗的有效性。但是因为最好的证据来自一项对照研究,古德曼正在考虑如何在道德上进行这些,现在有有效的疫苗可用。一种选择是确定目前没有资格接种疫苗的人群,就像现在的儿童一样。另一种选择是在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研究,那里根本没有疫苗。但这也引发了伦理问题:为什么不向这些国家提供疫苗,而不是招募他们进行研究? “但事实是我们确实有一个不公平的世界,全球健康和融资方面存在不平等,”古德曼说。因此,为人们提供参与研究的机会可能是合乎道德的。 “这些国家本身可能会要求这样做,”他说,因为他们正在努力了解病毒变种对其人口构成的风险。另一种选择是开展一项研究,让所有参与者都接种疫苗,但不是立即接种。例如,两个月后,人们会得到第二次治疗——如果他们最初得到安慰剂,那就是真正的疫苗,反之亦然。古德曼说,这里的一个关键是,没有人应该知道哪个是哪个。这样人们就不会改变他们的行为,这本身就会影响试验的结果,因为知道自己接种了疫苗的人可能会冒更大的风险。
古德曼说,病毒变种的出现“可能真的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因为可能存在某些变种,所有疫苗的功效可能都很低,以至于我们基本上回到了零”。 “我们可能不得不回到安慰剂对照试验。这很难知道。”这是最坏的情况。目前在美国使用的疫苗似乎对在英国首次发现的变种效果很好,并且似乎对在南非首次发现的变种提供至少部分保护,但在几个月内可能会出现更隐蔽的新变种未来几年。 Fierro 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也许在一两年内,现有的疫苗将被证明非常有效,以至于 COVID-19 只不过是一种滋扰。在这种情况下,参加一项有安慰剂选项的研究的风险将低到可以接受,例如,对于尚未接种疫苗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