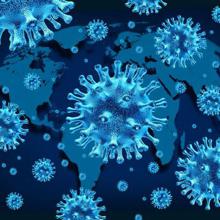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好应对冠状病毒的准备?™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好应对冠状病毒的准备?
在2006年,一种未知的病毒可能从一些野生动物蔓延到人类,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并导致全球大流行的想法,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一个遥远的前景。作为一部引人入胜的科幻惊悚片,它的排名低于“异形:复活”。但国家人畜共患病、病媒传播和肠道疾病中心的阿里·S·S·可汗(Ali S.Khan)的任务是在白天梦到那个噩梦。
(根据可汗的说法,发音为“N.C.Zved”)是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一部分,住在亚特兰大市中心东北6英里处克利夫顿路(Clifton Road)疾控中心大院里一座不起眼的灰色砖房里,后面是锁着的门和锁着的门。在那一年为期两天的访问期间,我沿着走廊一路走访,采访了对埃博拉病毒(是的,不止一种)和他们致命的表亲马尔堡了如指掌的科学家;关于布朗克斯的西尼罗河病毒和亚利桑那州的辛诺布雷病毒;关于巴厘岛的猿猴泡沫病毒(由爬过游客的寺庙猴子携带),以及通过作为宠物出售的冈比亚巨鼠传播到伊利诺伊州的猴痘;关于阿根廷的朱宁病毒和机器。所有这些病毒都是人畜共患病的,这意味着它们可以从动物传染给人。它们中的大多数,一旦进入人体,就会造成破坏。其中一些病毒也在人与人之间很好地传播,爆发了可能导致数百人死亡的局部疫情。它们对科学和人类免疫系统都是新的;它们的出现是不可预测的,很难治疗;而且它们可能特别危险,正如研究它们的分支-特殊病原体-的名字所反映的那样。出于这些原因,一些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包括阿里·汗,发现这些病毒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挑战。“这是因为他们让你保持警惕,”他告诉我。在我访问的第二天,在有趣而可怕的简报中,可汗带我出去吃寿司。
可汗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医生,职业上是一名流行病学家,而且是一个坦率、不敬的诙谐之人。他穿着一件有肩章的制服毛衣;当时,他也是美国公共卫生服务(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Service)的一名军官,该服务是按等级组织的,就像美国海军一样。他说:“你已经听到了我们人民的所有言论。”“这些疾病中你最喜欢哪种?”
“啊,”可汗不屑一顾地说。“我和其他人一样喜欢埃博拉病毒。”在1995年基克维特(Kikwit)爆发埃博拉疫情期间,他做了关键的流行病学工作,组织控制措施,调查传播,将疫情追溯到零号患者,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结束了一场痛苦和死亡的庞然大物。他接着说,“但是,在我看来,这就是我要找的人。”
?我只知道它是一种严重的病毒性疾病,2003年,它来自中国南方,导致多伦多、新加坡和其他几个城市的人死亡。这个首字母缩写代表“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这是一种丑陋的疾病,可能会导致致命的肺炎。8000多人受到感染,其中约10%死亡,然后疫情结束。“为什么?”我问过了。
“因为它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和致命性,”他说。“我们非常幸运地阻止了它。”是从人类耳边呼啸而过的子弹。这是在我们午休的时候,我已经不做笔记了,那是14年前的事了,所以我不能发誓可汗提到了另一件最相关的事情:它是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
阿里·汗现在是奥马哈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奥马汉:他在布鲁克林出生和长大,父母是巴基斯坦移民,他上了布鲁克林学院,然后是纽约州(布鲁克林)的医学院。“然后我做了一件疯狂的事,离开布鲁克林”-疯狂地对待他的家人,“因为我的叔叔阿姨们还没有离开布鲁克林去过这座城市。”他的父亲古拉布·迪恩·汗(Gulab Deen Khan)是一位白手起家的史诗般的人:作为一名十几岁的农民,他从克什米尔长途跋涉到孟买,谎报年龄,在船上找到了一份工作,给发动机加油。他的朋友称他为小个子迪尼,因为他个子很小。搬到美国后,迪尼·汗(Dini Khan)在锅炉里燃煤,为布鲁克林的公寓楼供暖,直到他攒够钱自己买了一栋公寓楼。他赚了钱--看起来是一大笔钱。在失去它之前,在另一种猜测中,迪尼汗决定他年幼的儿子阿里应该学习他家的文化、宗教和语言。他把阿里送回巴基斯坦上初中和高中。由于父母的误判,他选择了拉合尔的一所经典的英国寄宿学校,那里比乌尔都语或伊斯兰教更适合学习板球。当我最近通过Skype联系到阿里·汗时,现年56岁的阿里·汗告诉了我这个故事,不时地夹杂着笑声。他深色的头发
但是,他在疾控中心的任期接近尾声时,作为一名高级官僚,他负责策划,而不是调查;科学只占这项工作的一小部分。“现在几乎都是科学了,”他说。病毒学、流行病学、生态学和疾病科学的其他方面提供了他的使命的实质,“教育下一代公共卫生从业者”。
他目前办公室的装修兼收并蓄,包括各种病原体的电子显微照片,像画像一样挂在流氓画廊里,两个像乌鸦一样大的蚊子雕塑,一个“星球大战”钟,一个“超能英雄6”玩具机器人,世界各地的孩子们寄来的卡片,他旅行时的纪念品和礼物--一个刚果香炉,一把沙特斩首剑--还有一块白板,上面写着他所谓的“我的指标”。他的宝贵指标:衡量他的学校朝着学术目标的进步,科学目标,支持工作的慈善目标。“我是以证据为基础,以证据为导向的,”他说。
我问可汗关于-19的事。到底是什么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呢?他在疾控中心监督的公共卫生准备工作在哪里?为什么大多数国家--尤其是美国--如此未做好准备?是因为缺乏科学信息,还是因为缺乏资金?
有警告。其中一种是可汗最喜欢的疾病。2002年末,一种原因不明的“非典型肺炎”开始在中国南方的广州市及其附近蔓延,广州市是地球上最大的城市群之一。2003年1月,在一名身患呼吸危象的胖乎乎的海鲜商人体内,病毒传到了广州一家医院。在那家医院,然后在他被转移到的一家呼吸机构,这名男子在插管期间咳嗽、喘息、吐痰和吐痰,感染了数十名医护人员。他在广州医务人员中被称为毒药王。现在回想起来,疾病科学家给他贴上了不同的标签,称他为超级传播者。
一名被感染的内科医生是医院的肾科医生,他出现了流感样症状,但后来感觉好多了,于是坐了三个小时的巴士去香港参加他侄子的婚礼。住在大都会酒店的911房间,医生又生病了,沿着九楼的走廊传播疾病。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九楼的其他客人带着疾病飞回了新加坡和多伦多的家。几周后,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宣布了这一决定。(大都会变得臭名昭著,后来被重新命名。)。截至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全球150例新病例。
两个谜团隐约可见,一个是紧急的,另一个是挥之不去的:病因是什么-一种新的病毒,如果是的话,是哪种病毒?它来自哪种动物?第一个谜团很快就被马利克·佩里斯(Malik Peiris)领导的一个团队解开了。佩里斯是一名斯里兰卡医生,在进入香港大学之前在牛津大学获得了微生物学学位。佩里斯专门研究流感,他怀疑H5N1流感病毒可能已经进化成一种可以在人类之间传播的形式。H5N1是一种流感病毒,在禽类中很麻烦,在人中往往是致命的,但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他的团队设法从两名患者身上分离出一种新病毒。这是一种冠状病毒,而不是流感病毒-也就是说,它来自不同的病毒家族,具有不同的家族特征。但是,仅仅在两名患者身上出现这种新病毒并不意味着它就是这种疾病的原因。然后,佩里斯的团队通过抗体测试表明,这可能确实是病原体,进一步的工作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尽管早期的传统倾向于根据地理联系来命名新病毒-埃博拉是一条河,德国的马尔堡是一座城市,尼帕是马来西亚的村庄,亨德拉是澳大利亚的郊区-但人们对污名更敏感。这种病原体后来被称为冠状病毒。最近更名为-CoV-1,这样就可以称-19的毒剂不是武汉病毒而是-CoV-2。
2003年2月23日抵达多伦多,由一名78岁的妇女抬着,她和丈夫在大都会酒店九楼度过了为期两周的香港之旅中的几个晚上。这名妇女患病,然后于3月5日在家中去世,家人照看她,其中包括她的一个儿子,他自己很快就出现了症状。在经历了一周的呼吸困难后,他去了急诊室,在那里,没有隔离的情况下,通过雾化器给他用药,雾化器把液体变成雾,把它塞进病人的喉咙里。“它有助于打开你的气道,”可汗告诉我--这是一种预防哮喘发作的有用而安全的工具。但是,对于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病毒来说,这是不明智的。“当你呼气时,实质上就是把肺部的所有病毒带回空气中--在你正在接受治疗的急诊室里。”急诊室的另外两名患者被感染,其中一人很快因心脏病发作被送往冠状动脉护理病房。在那里他最终感染了
大约在那个时候,阿里·汗(Ali Khan)抵达新加坡,担任世卫组织顾问(从CDC借调)。帮助组织调查和回应。他每天都与卫生部的首席流行病学家周苏凯会面,他们和其他人一起制定战略和战术,通过一个特别工作组获得政府的合作。公共卫生战略是隔离和隔离。“在这次疫情爆发之前,检疫和隔离并不经常引起传染病的爆发,”可汗告诉我-至少在最近没有。在欧洲中世纪的瘟疫期间,被感染的不幸的人有时会被送到城墙外,等待死亡或康复;地中海港口拉古萨(现在的杜布罗夫尼克)建立了特伦蒂诺(Trentino),对来自瘟疫地区的游客进行30天的隔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在天花爆发期间,表现出天花的受害者(特别是如果他们是穷人或有色人种)可能会被关在隔离营里,周围是高高的带刺铁丝网围栏,或者是噩梦般的“收容所”--与其说是要治疗,不如说是为了普通民众的安全。“这是一个有点过时的概念,”可汗冷淡地告诉我。他和Chew以及他们的同事用一个更人性化的版本复兴了它。
陈德胜开始只治疗病人,其他病人被分流到新加坡综合医院。在T.T.S.,每一个疑似或可能的病例都被隔离,“疑似或可能”的定义超出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方针,包括任何有发烧或呼吸问题的人。所有医护人员都穿上了个人防护装备,包括N95口罩,他们被要求每天检查自己是否发烧或其他症状三次。医务人员也被限制在一家机构,因此他们不能在医院之间携带病毒。在危险的过程中,比如给病人插管,他们戴着呼吸头盔,吸入净化的空气。
还采取了坚定的措施来限制疾病在社区中的传播。截至3月27日,学校停课,死亡者的身体在24小时内火化。调查人员追踪到每个新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也是在24小时内,这些接触者被强制自我隔离。“好吧,你就呆在家里吧。我们会在你的房子里安装一个摄像头,还有一部电话,“Khan说,并详细说明了这些说明。“我们会随机给你打电话,希望你打开摄像机到场。”已经有800多人被隔离。藐视家庭检疫,你就会被贴上电子追踪器的标签,比如脚踝手镯。强制隔离带来了后勤挑战,可汗告诉我:“‘一旦你持有它们,你就拥有它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你必须给这些人提供食物,照顾他们的医疗保健,确保他们有住房和衣物。“谁来照顾他们?谁来付钱呢?“。如果你是执行自我隔离的政府部门,你就应该这么做。
到4月24日,已有22人死亡,在这一点上,对违反检疫者的处罚更加严厉:更高的罚款,可能会坐牢。出租车司机每天都要检查体温。离开和到达樟宜机场的乘客以及乘坐公交车和私家车旅行的人也接受了筛查。5月20日,11人因随地吐痰被罚款300美元。这些措施奏效了。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三日,最后一名病人走出陈德胜,一切都结束了。有些人松散地说这是“烧毁”,全世界只死了774人。它没有烧毁。就像阿里·汗告诉我的那样,它被阻止了。
“你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六年后,我问陈德胜的布伦达·昂(Brenda Ang)。
她沮丧地笑了。“自满,”她说。“和冷漠。”平凡但关键的感染控制措施-勤奋的洗手和用酒精擦拭门把手-在危机之后可能会失效。“人们会变得自满。他们认为周围没有新的虫子。“。除了疫情爆发地点之外,新加坡以外还有更大的教训吗?“仅仅保护自己的地盘是没有意义的,”她说。“传染病是如此全球化。”
阿里·汗后来对我说了同样的话:“哪里的病就是哪里的病。”
2015年,另一种冠状病毒抵达韩国,在一名68岁的阿拉伯半岛出差归来的男子身上。三年前,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被认为是一种疾病,绰号骆驼流感,因为单峰骆驼似乎携带病毒并将其传播给人。这种病毒可能最初来自蝙蝠-也许是埃及墓蝠-但可能已经在骆驼身上传播了至少30年。它可能早在2012年就已经蔓延到人类身上,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感染就没有了
超级传播者事件也推动了这次疫情的爆发,但韩国医疗保健系统的一些方面加剧了疫情。由于公民通过国家保险计划获得廉价的医疗服务,对他们去哪家医院几乎没有限制,人们经常购买治疗。这位商人在感觉不适后去了三家不同的医院,最终住进了首尔的第四家医院,在那里他被诊断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到那时,他已经感染了29人,其中两人自己成为超级传播者,多了97例。有时病房里有四张或更多的床位,病人被允许接待访客,这导致了传播,通风不佳,感染控制不力,隔离标准狭窄,以至于通过偶然接触感染的人被错过了。“在这一点上,他们认识到了冠状病毒会发生什么,这种病毒会导致你的社区和医院的医疗保健获得性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