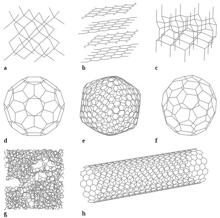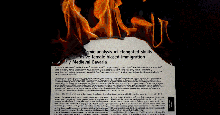专访8年前预测流感大流行的科学作家
2012年,作家大卫·夸曼(David Quammen)写了一本书,名为“溢出:动物感染和下一次人类大流行”(Spiloverage:Animal Inftions and the Next Human Epidance),这本书是科学家们对另一种埃博拉类型疾病出现的可能性进行了五年研究的结果。共识是:确实会有一种新的疾病,很可能来自冠状病毒家族,从蝙蝠中出来,它很可能会出现在中国的一个菜市场或附近。
但无法预料的是,我们会有多么毫无准备。在这次采访中,“快报”的小丹·德罗莱特采访了住在蒙大拿州博兹曼的作者,他谈到了是什么吸引了他选择这个话题,新病毒的性质,为什么预计会出现更多病毒,以及是什么使一些病毒比其他病毒更有可能感染人类。夸曼还谈到了他的下一本书(仍未命名,但关于冠状病毒)。他告诫说,不要对疫苗的开发过于乐观,他说,导致新冠肺炎的冠状病毒可能会以某种形式世代存在:“这种病毒永远不会消失。”
(编者按:为了篇幅和清晰度,本采访经过浓缩和编辑。)。
管家:是的。虽然我最近像很多人一样呆在家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为出版商研究一本关于冠状病毒的新书。但是他们一让我进来,我就会在中国武汉挨家挨户地敲门。
夸曼:不完全是。我尊重这种病毒的风险。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研究溢出效应时,我爬进了中国南方的蝙蝠洞。
我已经关注了危险的新兴病毒足够长的时间,虽然我意识到了危险,但我知道这只是一个计算风险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情绪化的话题。
在我看来,我已经在博兹曼的家了,已经两个月没有离开过房子了。因此,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有幸将风险降低到0.0。很快我就会开始做高风险的事情。
德罗莱特:关于病毒似乎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警觉和偏执。为什么会这样呢?
奎曼:病毒对人来说很可怕。与细菌不同的是,即使用[标准]显微镜也看不见它们。我们甚至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知道病毒的实际存在,尽管这个词已经广为流传。整个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都是由一种病毒引起的-一种没有人能看到、分离或识别的假想病原体。那有多恐怖啊?因为有很多细菌引起的继发性感染,而那时我们还没有抗生素。
因此,1918年一定是一件奇特而可怕的事情:这个看不见的东西来到镇上,杀死了你的家人,然后离开了。就像“出埃及记”里的死亡天使。
德罗莱特:所以你认为很多恐惧是因为它是看不见的,神秘的…。
管家:是的。还有关于病毒是否活着的争论--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
巧合的是,我现在正在阅读这个角度,为“国家地理”的一篇关于病毒进化史的文章做准备。
也许所有这些古怪的东西加在一起,会让人们特别害怕。另外,近几十年来,在我看来,有一些非常危言耸听的治疗新兴病毒的方法,比如热区。尤其是埃博拉病毒-这本书涉及的病毒-已经被赋予了全面的、大吉诺尔式的戏剧性耸人听闻的感觉。
埃博拉病毒是一组非常危险的密切相关病毒之一;我认为现在有5种病毒被归类为埃博拉病毒属。人们听说,“这种病毒会导致身体融化并流血而出。”然后有几个病例进入了美国,人们都吓坏了。
德罗莱特:我想回到一个问题上来:你说有一种理论认为病毒甚至可能不存在?
夸曼:我们的想法是,病毒只是包装在蛋白质胶囊中的一大块遗传密码-本质上只是一个蓝图,它接管了你的细胞,重新编程让它们自我复制,然后繁殖并传播到你的其他细胞,然后可能从你传播到其他人。
这个概念的一个有趣的转折是“病毒细胞”,这是由一个叫Jean-Michel Claverie的家伙和另一个叫Patrick Forterre的科学家提出的。他们说:“不要把这些病毒颗粒看作是病毒。把它们想象成配子而已。“。换句话说,病毒颗粒不过是人类精子的等价物--它不是全能的人类。当病毒在你的一个细胞中,并成功地劫持细胞进行自我复制时,真正的病毒生命身份就出现了-那就是活病毒,或称病毒细胞。
这一过程的产物是这些携带有感染性基因组到其他细胞的颗粒。把这些想象成配子。然后当它们进入另一个细胞时,你就有了一种受精卵细胞-生物学家称之为受精卵。
夸曼:我做了大约35年的科学作家,这是一种在职培训。
但实际上,我最初是一名小说家,为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做研究生工作,后来逐渐成为一名对科学感兴趣的非虚构类作家。
夸曼:当我在73年搬到蒙大拿州时,我想,“我受够了常春藤覆盖的大学”,想以作家为生。我对自然界很感兴趣,开始在蒙大拿大学修一些动物学的非学位课程。但那是动物学。
1982年,我的第一任妻子开始在亚利桑那大学攻读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硕士学位。所以我和她一起去了图森。她下课回到家,开始谈论这个叫罗伯特·麦克阿瑟的家伙,他就像理论生态学的詹姆斯·迪恩--非凡的青春希望,以及过早的死亡。
这让我很感兴趣。然后,巧合的是,我发现他和E.O.威尔逊写了一本名为“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的书。
当时我是“外在杂志”的专栏作家,在研究有关它的专栏时,我想:“我想知道有没有人为流行杂志写过关于岛屿进化和灭绝的文章?”
感觉就像是发现了猛犸象洞穴。我从这个小洞进去,然后走出这个宏伟的大房间,墙上挂着这些令人惊叹的画作。这就是我与岛屿生物地理学的邂逅。这就是我花了八年时间写的“渡渡鸟之歌”这本书。
德罗莱特:说到进化,我的理解是,绝大多数病毒永远不会从一个宿主物种跳到另一个宿主物种。那么,有些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夸曼:有些病毒恰好是所谓的“预适应”,可以实现从动物到人类的飞跃。
在冠状病毒的情况下,你有一种自然产生的蝙蝠病毒,它的外部恰好有这些被称为钉状蛋白的旋钮。每个尖刺的作用就像一个抓钩,让它抓住一个目标细胞,并可能进入。
事实证明,这种尖峰蛋白最擅长抓住的细胞是一种叫做马蹄蝙蝠的物种。这些特殊的蝙蝠在其细胞外部有一种被称为ACE-2受体的东西。因为这些特殊的受体,它们很容易受到这些特殊病毒的攻击。
碰巧的是,我们人类在我们自己的细胞里,在我们的呼吸道里都有这些ACE-2受体。因此,巧合的是,这种自然产生的蝙蝠病毒从一开始就相当有资格攻击人类细胞。
这就是病毒能够传播到人类的原因。显然,它在击中第一个人之前就有这种能力。因此,这种病毒被预先改编成一种人类病毒--很可能是这样。
德罗莱特:对于这种病毒来说,跨越物种-人畜共患病-一定就像哥伦布发现美洲一样:突然之间,一个全新的世界向我们敞开了大门。
夸曼:是的,虽然我更愿意把它比作第一批从南美大陆吹到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十几只雀类。这一小群雀类被一场风暴吹向西,将它们带到了500英里外的大海,它们降落在这些没有任何捕食者或任何竞争对手的火山岛上。所以他们拥有一切。它们可以在那里繁衍生息,也许还能分化成许多不同种类的雀类。这是生态殖民,然后是进化适应。这就是病毒会发生的情况。
管家:是的。15年来,科学家们一直说:“当心冠状病毒,它们可能非常危险。”五年来,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中国科学家施正力一直警告我们要警惕在中国蝙蝠身上发现的冠状病毒;SARS是一种冠状病毒,它是在2003年从中国蝙蝠身上发现的。那对人类是非常危险的,但它不像这只那样容易传播。但史和她的团队在云南省一个洞穴的蝙蝠身上发现了一种与之非常相似的病毒,并在2017年发表了一篇论文,称“要警惕这些马蹄蝙蝠身上的这些特殊的冠状病毒。它们需要最高的准备。“。那是三年前的事了。
德罗莱特:病毒是不是直接从蝙蝠传染给人类的?或者从蝙蝠到穿山甲或者从果子狸到人类?
泉门:它可能感染了一个或多个中间物种。有一些重要的新工作来自一组中国和西方的科学家,他们注意到这种疾病与一些穿山甲冠状病毒有多么接近。它还与其他一些蝙蝠冠状病毒很接近,不仅是石正丽发现的,而且是新的。这是一种病毒的拼图游戏。
德罗莱特:这就引出了我的下一个问题:很多责任都归咎于中国的菜市场。究竟什么是菜市场?
泉门:几天前,一位中国朋友说:“你们所谓的菜市场,就是我父亲过去带我去买新鲜蔬菜的地方。”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但像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这样的湿货市场,与这一切的开始有关,是你买新鲜蔬菜的地方。你可以在那里买到海鲜--活的和死的--还有鸡、鸭和青蛙。
这些野生动物有两个可能的来源。一种是在有控制的卫生条件下圈养繁殖野生物种,另一种是从野外捕获动物,把它们关在笼子里。
夸曼:是的,虽然“丛林肉”这个词有一定的污名。一般来说,当非洲人做这件事时,我们称之为丛林肉;当中国人做这件事时,我们称之为菜市场。当我们在蒙大拿州做这件事时,我们只是把它叫做游戏--没有任何耻辱。
德罗莱特:中国的菜市场和郊区的农贸市场没有区别吗?
夸曼: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想想纽约州北部的一个不错的农贸市场,那里有奶酪、蜡烛、新鲜蔬菜、有机鸡肉、火鸡等等。
也许放臭鼬的笼子是堆放在有机鸡的笼子上的,这样臭鼬的尿液就会像雨点一样落在鸡身上。现在,你想买那些鸡吗?
宽门:在某种程度上,是的。但捕获野生动物并将它们活生生地带到出售所有其他形式食品的市场是极其危险的。所以世界说:“看,中国,你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不会在文化上污蔑你,这是正确的。但看在上帝的份上,还是控制一下这种交易吧,因为它很危险。“。
德罗莱特:有些人声称在这样的市场买卖野生动物是中国古老的传统。
泉门:我的一位中国朋友于武飞(音译)为“纽约时报”写了一篇专栏文章“穿山甲的复仇”,说这不是神圣的传统。事实上,他发现中国古代文献上说:“不要吃穿山甲,你会生病的。穿山甲不是食物,不要吃。“
因此,吃穿山甲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古老传统。这更多的是一种新的中产阶级炫耀性消费时尚的一部分。比如“我有一个商务晚宴,所以我要带我的客户去一家餐厅,在那里我会用猴脑或穿山甲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德罗莱特:这与你自己的时报专栏有关:“我们入侵热带雨林和其他野生景观,那里栖息着如此多种类的动植物。在这些生物体内,有如此之多的病毒。我们砍树,杀动物,或者把它们关进笼子送到市场。我们破坏生态系统,使病毒脱离它们的自然宿主。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他们需要一个新的东道主。通常情况下,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夸曼:这就是总结。有更多的人畜共患病,因为我们正在破坏环境。
但重要的是要承认,在过去的20万年里,我们人类一直在捕杀和食用野生动物。因此,我们大概总是接触到野生动物携带的许多病毒。所以这是一件古老的事情。
最新的是,这个星球上有78亿人,是1918年流感时人口数量的四倍。我们绕地球旅行的速度翻了两番,一些城市的面积翻了两番。所以我们有更多的大型脊椎动物,生活在密集的群体中,从一个地方流畅地移动到另一个地方。
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病毒目标--一个让它们殖民的巨大生态系统。因此,当一种病毒确实进入人类并发现它可以复制并传播给下一个人类时,这种病毒就打开了巨大机会的大门。最新的是规模。
因此,在过去的60年里,出现了所谓的溢出效应,即新病毒进入人类并造成麻烦:1959年,马丘波,或玻利维亚出血热。马尔堡,1967年,来自被送往德国马尔堡用于研究目的的猴子。埃博拉病毒于1976年首次出现,MERS于2012年出现,寨卡病毒于2015年出现,还有这个。因此,它正在更多地发生,产生更大的后果,并有更大的潜力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德罗莱特:气候变化有影响吗?我们是否看到温暖天气的疾病现在出现在以前的温带地区?
宽门:在某种程度上。登革热、黄热病和疟疾正在向北移动,因为携带它们的蚊子正在向北移动。这是气候变化最明显的影响。
而森林碎片化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我们现在新英格兰有了更多的莱姆病,因为它不再是完全被落叶森林覆盖的地区,而是被分割成树篱、草坪和小片森林,携带着大量的白脚老鼠-这些老鼠携带着导致莱姆病的蜱虫。因为猫头鹰、鹰、狐狸或黄鼠狼等捕食者的数量不像猫头鹰或黄鼠狼那么多,所以这种老鼠出没的数量要多得多。所以老鼠的数量增加了,当你的孩子外出到院子里玩耍时,他更有可能感染莱姆病。
管家:是的。而且每一次溢出都有更大的机会变成一场疫情,每一次疫情都会变成一场流行病,每一次流行病都会变成一场大流行。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来阻止这种情况。
夸曼:对我和我10年前听过的科学家来说,关于这次疫情的一切都是可以预测的。
一种病毒开始进入人体并从一个机场传播到另一个机场--但是我们没有可以工作的诊断试剂盒。我们没有可以修改成这种冠状病毒疫苗的平台疫苗。我们没有公共卫生应急能力。在这个国家,我们没有综合的国家计划。除了每天站在那里担心自己的民调数字的撒谎的总统之外,我们一无所有,而一个名叫托尼·福奇(Tony Fuci)的高尚男子被迫站在他旁边。他做了30年的这份工作,他是自瓦伦达以来最伟大的走钢丝的人。
所有这一切都让我非常惊讶,我们完全没有准备好。特朗普说,“嗯,我们将对飞入的中国人关闭边境。再也不会有中国人能飞进来了。“。太棒了。太棒了。这将会解决这个问题。不。
然后他就什么都不做了。我不想把这件事纯粹政治化,特朗普只是一种症状。但由于种种原因,美国一直措手不及。
夸曼:今天早上在NPR上,有人不经意地说,“也许六个月或一年后,这种病毒就会消失。”
这个病毒不会消失的。这个病毒永远不会消失。
我们有孩子和孙子的朋友,他们的曾孙将接种这种病毒的疫苗。
夸曼:医生保罗·奥菲特对速溶疫苗持怀疑态度。他一直在告诉每个人放慢对疫苗的期望,停止庆祝莫德纳或吉利德或任何获得原型疫苗的人。他说,在非常初步的阶段,对于很小的样本量,有太多的喧嚣。疫苗的研发需要很长时间,而且需要很多运气。然后疫苗的规模化生产需要另一卡车的时间…。
重要的是要记住,这是每个人的责任;这不仅仅是一些吃穿山甲或蝙蝠的中国人的错。这也不是非洲人吃丛林肉(有时包括灵长类动物)的过错。这是我们78亿人的责任,因为我们都是食物、资源和能源的消费者。我们关于吃什么、穿什么或买什么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借鉴了这些野生生态系统。
如果我们选择生孩子,那么我们选择旅行的次数和我们有多少孩子也是如此。所有这些决定都不同程度地给自然界带来压力,并导致病毒与人类接触。即使使用手机也会带来环境成本;我们正在消耗让这些东西内部的电容器工作的矿物,比如钽铁矿石。
世界上只有几个地方开采钽铁矿石,比如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距离他们最大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不远。我们消费者要求矿工去那里为我们拿到钽铁矿石;他们除了丛林肉还能吃什么呢?
因此,拥有一部手机,你就是在要求矿工去开采钽铁矿石的地方,很有可能其中一个地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为你开采钽铁矿石的人很可能是在吃蝙蝠、猴子、大象或低地大猩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