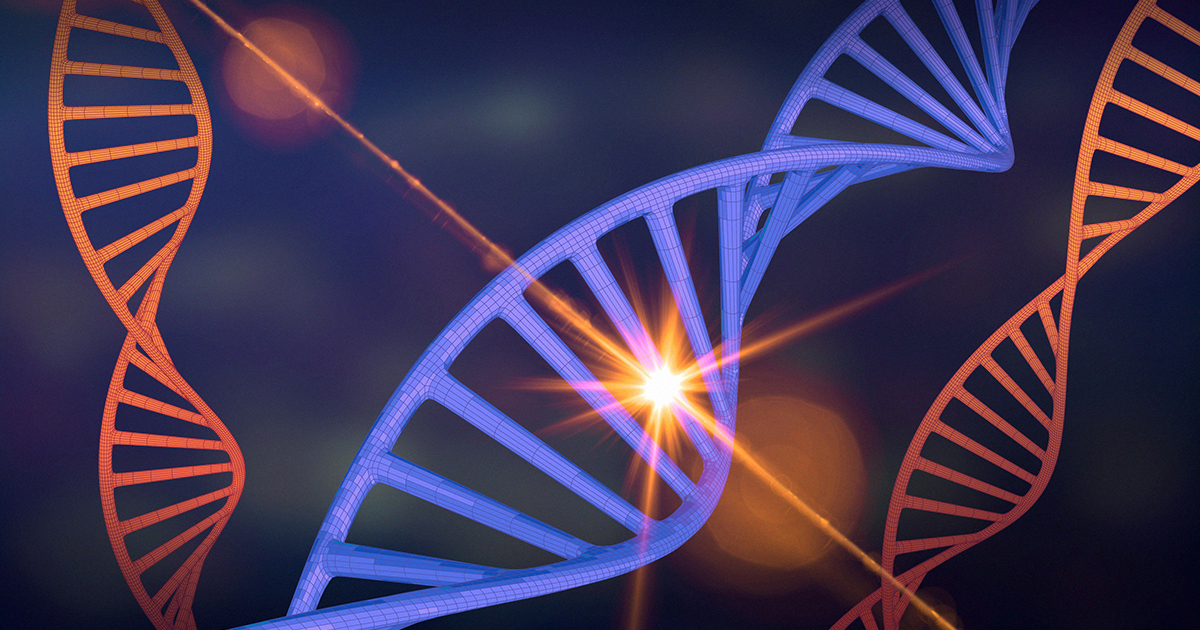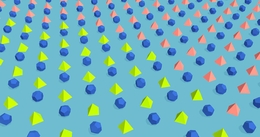宇宙射线可能解释生命对右手DNA的偏爱
如果你能缩小到足够小,可以像螺旋楼梯一样沿着地球上任何动物、植物、真菌、细菌或病毒的基因螺旋下降,你就会发现自己总是向右转--而不是向左转。这是一个普遍的特点,需要一个解释。
化学家和生物学家认为没有明显的理由说明为什么所有已知的生命都喜欢这种结构。“手性”分子以成对的形式存在,就像右手手套和左手手套相匹配一样。基本上,所有已知的化学反应甚至都会产生两者的混合物。原则上,由左撇子核苷酸砖制成的DNA或RNA链应该和由右撇子砖制成的一样好(尽管结合左右亚基的嵌合体可能不会那么好)。
然而,今天的生活只使用了化学公司提供的两套乐高积木中的一套。许多研究人员认为选择是随机的:那些右撇子遗传链只是碰巧最先出现,或者数量稍多。但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些人一直在思考生物学与生俱来的利手性是否有更深层次的根源。
“这是地球上的生命和宇宙之间的联系之一,”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在1860年写道,他是最早认识到生命分子中不对称的科学家之一。
现在,两位物理学家可能已经通过将自然DNA的一成不变的扭曲与基本粒子的行为联系起来,验证了巴斯德的本能。这一理论发表在5月份的“天体物理杂志快报”上,并没有解释生命如何获得现在的惯用手的每一步,但它确实断言,陆地DNA和RNA的形状并不是偶然的。我们的螺旋线可能都可以追溯到宇宙射线意想不到的影响。
哈佛大学天文学家、该校生命起源倡议主任迪米塔尔·萨塞洛夫(Dimitar Sasselov)说,这项工作“指出了一种我们没有考虑过的新的手性试剂”,他没有参与这项研究。“看起来非常不错.”
宇宙射线是来自深空的子弹,原子弹片不断地落在我们的头上。这些猛烈的天体是纽约大学高能天体物理学家诺埃米·格洛布斯(Noémie Globus)和熨斗研究所(Flatiron Institute)计算天体物理中心的长期猎物。(“广达杂志”是一份编辑独立的出版物,由西蒙斯基金会(Simons Foundation)赞助,该基金会也为熨斗研究所(Flatiron Institute)提供资金。)。但格洛布斯直到2018年才过多地考虑宇宙射线可能会如何影响生命,当时她是卡夫利粒子天体物理和宇宙学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在那里她遇到了同为天体物理学家的斯坦福大学研究所前所长罗杰·布兰德福(Roger Blandford)。
他们开始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宇宙射线阵雨,就像DNA链一样,都有惯用手。物理事件通常向右打破的频率与它们向左打破的频率一样高,但被称为介子的宇宙射线粒子利用了自然界罕见的例外之一。当介子衰变时,这个过程受弱力的支配,弱力是已知镜像不对称的唯一基本力。撞向大气层的介子会产生粒子阵雨,其中包括电子及其较重的兄弟姐妹µ子,所有这些粒子都配备了相对于其路径具有相同手性磁取向的弱力。Globus说,这些粒子在穿过大气层时会反弹,但总的来说,当它们撞击地面时,它们往往会保持自己喜欢的手性。
研究人员推测,地球上最早的有机体可能只有两个品种,它们可能只是一根赤裸的遗传物质理发杆。一些人的DNA或RNA链像我们的一样卷曲,她和布兰德福德将其称为“活的”分子(手性命名惯例因场而异),而另一些人的DNA或RNA链与我们的相反,即“邪恶”的生命。通过一系列玩具模型,研究人员计算出,偏向的宇宙射线粒子比起理论上会导致突变的“邪恶”螺旋,更有可能将电子从“活的”螺旋中击散。
其影响将是微小的:根据事件的能量,可能需要数百万次(如果不是数十亿次)宇宙射线撞击,才能在一条“活的”链中额外产生一个自由电子。但是,如果这些电子改变了有机体遗传密码中的字母,那么这些微调可能会加起来。格洛布斯认为,在大约一百万年的时间里,宇宙射线可能加速了我们最早的祖先的进化,让他们在竞争中击败了他们的“邪恶”对手。“如果你没有突变,你就不会进化,”她说。
研究人员的下一项任务是看看真实粒子的左旋手是否真的能导致他们模型中看到的快速突变。在他们发表了他们的研究之后,Globus向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生物学家和工程师David Deamer寻求帮助。她的想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提出了他能想到的最简单的生物测试:一种被称为Ames测试的现成测试,将细菌菌落暴露在一种化学物质中,以找出这种物质是否会导致突变。但研究人员计划用手性电子束或µ子束来烘烤微生物,而不是评估一种化学物质。
粒子的左旋性真的可以使微生物变异的证据将强化他们的观点,即宇宙射线将我们的祖先推下了进化的起点,但这仍然不能完全解释地球上生命的均匀手性。例如,该理论没有解决“活的”有机体和“邪恶的”有机体是如何从包含右手和左手积木的原始奶昔中实现的。
“这是非常困难的一步,”NASA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NASA 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资深天体生物学家、西蒙斯生命起源合作项目(Simons Collaboration On The Origins Of Life)的研究员杰森·德沃金(Jason Dworkin)说,“但如果这个[理论]能提供一种不同的机制,另一种达尔文式的压力,那就很有趣了。”
甚至在基因进化进入画面之前,另一个未知的过程似乎就阻碍了“邪恶”的生命。形成蛋白质的简单氨基酸分子也存在于生命喜欢的“活”构型和不喜欢的“邪恶”构型中(尽管“活”氨基酸的首选手性几乎完全是左撇子)。德沃金和其他人对陨石的仔细分析发现,某些“活的”氨基酸比“邪恶的”氨基酸多出20%或更多,这一过剩可能是他们传递给地球的。多余的分子可能是数十亿年来暴露在圆偏振光下的幸运幸存者,圆偏振光是一组沿着同一方向螺旋运动的光束,实验表明,这种光束可以比另一种稍微彻底地破坏一种氨基酸。
但是,像宇宙射线一样,光束也有边际效应。需要无数的互动才能留下明显的不平衡,所以其他一些力量可能也在起作用。德沃金说,光必须粉碎难以承受的大量分子,才能解释这种过度行为。
萨塞洛夫鼓励Globus和Blandford考虑宇宙射线是否可能与偏振光联合起来塑造小行星上的氨基酸。他推测,在地球上,产生明显手性差异所需的宇宙射线剂量-他将其比作超音速子弹-可能被证明过于致命。“你破坏了太多的东西,”他说。“你可能用的是[正确的]左撇子,但从本质上说,你是在自食其果。”
归根结底,研究人员努力寻找一种理论来平衡手性的增加和生物材料的破坏,这一事实表明,我们的祖先可能很幸运地找到了这条微妙的界限。
萨塞洛夫说:“像地球这样的行星有一些特殊之处,可以保护这种化学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