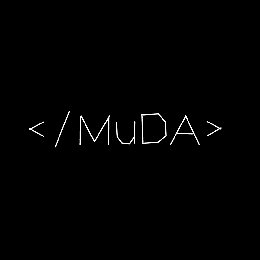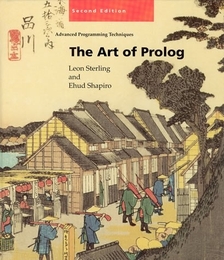相框应该被认定为一种艺术形式吗?
美国早期现代主义者约翰·马林最令人难忘的是他对新墨西哥州陶斯峡谷的动感沙漠和布鲁克林大桥红日的锐利维度的绘画。但对史密森美国艺术博物馆(Smithsonian American Art Museum,SAAM)的相框保护员马丁·科特勒(Martin Kotler)来说,包裹马林作品的相框和里面的画布一样重要。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马林在每一幅画和它的框架之间寻求一种“幸福的平衡”。他与纽约市相框制造商乔治·奥夫(George Of)合作创造了定制的坐骑,他在坐骑上涂上水彩,以增强里面绘画的调色板。在他职业生涯的后期,马林手工制作了他的镜框,并稳步地将他的艺术推到了边缘:纽约天际线布鲁克林大桥帆船的黑色边框上有银色条纹,就像交通繁忙的道路上的线条。
但过去的私人买家和博物馆管理员很少像科特勒那样珍视相框。一些帧被编目并存储,一些帧被遗忘和重新发现,而另一些帧则被彻底丢弃。直到最近,大多数人-包括专家-认为相框是可互换和可消耗性的,如果他们曾经想到过的话。
科特勒在谈到镜框时说:“当你在学校的时候,它从来不会被讨论。”许多框架制造商的名字丢失或被遗忘。在测试幻灯片和教科书上,艺术作品几乎都是不加边框的。学术上的盲点被传递给了参观者。科特勒说:“当人们走进博物馆时,有太多的事情要讨论。”在构图、色彩和艺术家传记之后,几乎没有时间讨论造型。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设计:框架基本上是功利性的物品。它们的存在是为了保护艺术品免受粗暴的搬运、人的接近以及灰尘和光线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他们还为观众走神的眼睛提供了护栏。“是母亲抱着自己的孩子,”科特勒说。但许多相框本身就是艺术品,理应被视为艺术品。
有些物品,比如马林或当代艺术家马修·巴尼(Matthew Barney)的那些物品,是“艺术家镜框”--由艺术家制作,因此与艺术品密不可分。马林或当代艺术家马修·巴尼(Matthew Barney)是塑料行业的先驱。其他的则是由框架大师完成的委托,比如大胆的布奥艺术建筑师斯坦福·怀特(Stanford White)(他把自己的奇幻设计交给工匠们制作),波士顿奢侈品商店Carrig-Rohane(科特勒称其为“框架中的劳斯莱斯”),或者雕刻大师格雷戈里·基什内尔(Gregory Kirchner)(他只制作了12个已知的框架)。还有一些是由像科特勒这样的保护者制作的,他为SAAM的珍宝制作了微妙、安全和历史上准确的箱子。
“相框遭受了流放和破坏,”林恩·罗伯茨(Lynn Roberts)说,他是一位自由职业的艺术历史学家,也是相框博客的创始人。但我们可以重新学会看东西。罗伯茨说,当人们“意识到那里有另一段历史时,他们开始问越来越多的问题。”“他们被镜框是如何制作的,做了什么,以及它们纯粹的多样性和美感迷住了。”
框架一直是一种保护形式。但罗伯茨说,这种狭隘的观点“很快就被意识到在这幅画和墙壁之间有了另一块空地,这块空地本身可以用来装饰”。虽然四块木头足以保证安全,但框架制造商喜欢巴洛克框架的镀金和多色曲线,不对称的洛可可峰和装饰艺术外壳的阶梯形几何形状。
科特勒说,当欧洲商店在重复他们的设计时,大多数美国人对大规模生产的“便利框架”感到满意。在1860年之前,他们进口这些华丽的石板,然后把它们贴在全国各地的绘画上。它看起来好不好看并不重要,只要合身就行了。虽然国内商店最终出现在波士顿、费城和纽约,但他们的作品并不一定是原创的。制造商往往是多产的小偷。如果像怀特这样的人展示了一个革命性的新镜框,全国各地的商店很快就会开发出仿制品-这是一个完全合法的主张,即使在今天,也很少有专利保护镜框和镜框。
但随着20世纪的临近,镀金时代的艺术家们开始对整个过程进行更批判性的思考。例如,阿什坎学校的成员想要反映他们作品的原始、冷漠精神的框架,而不是旧世界大教堂的框架。到了20世纪40年代抽象表现主义的出现,许多艺术家决定他们根本不想要镜框。
圣达菲乔治亚基夫博物馆的保护负责人戴尔·克朗赖特(Dale Kronkright)说:“现代画家认为,如果你戴上历史框架风格,就会失去这幅画的美感。”O‘Keeffe和她的同龄人希望观众在没有分心的情况下考虑形状、颜色、线条和构图的工作方式。为了确保她的愿景得以实现,O‘Keeffe与纽约市镜框制造商Of合作,开发了八个截然不同的镜框,恰好适合她的画作。
虽然O‘Keeffe作品的管理人员仔细保存了她的画框,但其他艺术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好品味”--至少它是在当下构思的--常常凌驾于历史真相之上。史蒂夫·威尔科克斯(Steve Wilcox)是美国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rt)的前相框保护员,他说,博物馆过去会移除原始相框,转而采用一种房屋风格。“没有人把它当做一个道德过程来认真对待,”威尔科克斯说,他在整个学区被称为“框架中的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 Of Frame)。
私人收藏家往往更加恶劣。罗伯茨回忆说,一幅德加画作最近出现在艺术品市场上,原始画框完好无损,但拍卖行用镀金木质画框取代了它。罗伯茨说:“它看起来华而不实,像巧克力盒,德加肯定会被吓坏的。”但“对于商业世界来说,一个镀金雕花框架会让一些东西显得更重要,价值一百万美元。”
今天,大多数博物馆都在寻求以真实的框架展示他们的藏品,这些框架真实地反映了作品创作的时代和艺术家的愿景。但长达几个世纪的框架贬值可能会使这个卑微的目标成为一项西西弗式的任务。
威尔科克斯说:“你可以通过翻阅卷册来找到那一句话。”
第一个目标是确定现有框架与内部工作的关系。赫什霍恩博物馆和雕塑花园(Hirshhorn Museum And Sculpture Garden)的框架专家贾尼斯·柯林斯(Janice Collins)说,这项工作需要对历史框架风格和材料有广泛而深刻的了解,而且通常还需要拥有该领域专业知识的策展人额外的一双眼睛。策展人想要更新约瑟夫·阿尔伯斯(Josef Albers)的作品的相框。阿尔伯斯是一位现代艺术家,最出名的是他的一系列对广场的敬意。但柯林斯采访了一位阿尔伯斯方面的专家,这位专家解释说,这位艺术家精心挑选了自己的画框。所以原来的固定装置留了下来。
如果这个框架是原创的,许多文物保护人员会试图调查它的起源故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特勒一直利用业余时间追捕一个名叫莫里斯·芬肯(Maurice Fincken)的人,他为约翰·斯隆(John Sloan)的一幅画制作了一个镜框。科特勒说:“背面有一个漂亮的纸质标签,但你去搜索一下,就会发现什么都没有。”“现在我的好奇心高涨了。”随着更多的挖掘,他发现Fincken在费城以外的地方工作,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基本上从记录中消失了。最近,科特勒确认了一名后代,他可能能够解释更多的故事。
一旦确定了它的来源,保护人员就会努力保护这个镜框,它可能已经经历了磨损、撕裂和不太巧妙的修饰。科特勒回忆起他在亚历山大·霍格的“尘埃碗”和艺术家画框上的作品。“一百万年前,博物馆说,‘把那个镜框取下来,设计出另一个更有同情心的镜框,’因为它真的是一个丑陋的镜框,”他说。科特勒按要求做了,但他保留了原来的相框,并“慢慢地,慢慢地清理掉了其他人做的东西”。当德克萨斯州的一家博物馆为霍格的职业生涯做回顾展时,科特勒能够用它的原始画框把它运给他们。这幅画并不漂亮,但对这位艺术家来说是真实的。
如果一件艺术品是在一个不真实的相框里,找到一个合适的、空的替代方案,或者从头开始建造一个,这是相框保管员的工作。例如,在史密斯学院艺术博物馆(Smith College Museum Of Art),阿什坎艺术家乔治·贝洛斯(George Bellows)的画作“宾夕法尼亚发掘”长期以来一直陈列在路易十四风格的镜框里,全部是编织和金色的。但该学院框架保护项目的学生们建造了另一种选择-仍然镀金,但带有微妙的芦苇造型,更适合贝洛斯的作品。
尽管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忽视,但这一框架最终可能会发挥作用。“就艺术史而言,这是一个相当新的领域,但在过去的15年里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威尔科克斯说。
威尔科克斯在20世纪70年代刚开始的时候只记得一本关于装框的书,今天已经有几十本了,像框架博客这样的网站让保护人员的洞察力可以向大众开放。历史悠久的工艺和新技术的结合导致了环境控制框架的发展,这些框架仍然尊重艺术家的意图。一些博物馆,主要在欧洲,已经策划了致力于装框艺术的展览,包括伦敦的国家肖像美术馆和卢浮宫。
虽然他最近退休去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山区,但威尔科克斯说,他希望领导世界各地的相框“极客”们的研讨会,并继续培养我们对相框的新生敬意。但就目前而言,他说,“我只是在享受我的风景。”
窗外的景色?“我没想到会这样,”他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