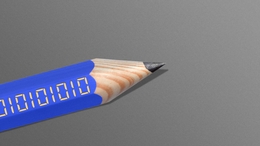繁荣改变了福克兰群岛
在瘟疫肆虐的时候,这是一个可以撤退的地方。城外是绵延数英里的空地,几乎没有道路。除了靠近地面生长的白草、黑色灌木丛和岩石,什么都没有。只有低矮的山,没有树,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从海上吹来的持续不断的风。这里非常安静,至少在风停下来的时候是这样,有些人觉得这种寂静和空虚令人难以忍受。在1982年战争之前,一些较大的农场雇佣了几十个人,那里有居住着四五十人的定居点,但这些人中的大多数现在都走了,要么搬走了,要么移民了。如今,每12平方英里就有一个人。一些老房子空置,被遗弃;另一些则被拖出定居点,留下一条碎石路,因为住在那里的人骑着马。
在东福克兰和西福克兰这两个大岛的边缘,有700多个较小的岛屿,一些是空的,另一些只有一两个家庭居住:几座房子,一些发电机,一条跑道。有水管和互联网。有了足够大的冰柜,你可以在这里呆上几个月。更长的时间,如果你知道这里的人们直到最近才知道如何生活:宰杀自己的羊肉,挤牛奶,收集海鸟蛋和骗取的浆果,挖泥炭作为燃料。在与阿根廷的战争中,当人们逃离小镇,出现在农舍里时,人们并不太担心养活他们,或者是那些躲在鸡舍和剪毛棚里的英国士兵。农民们有菜园,有无数的羊,面粉和糖装在50公斤的袋子里。
150年来,当福克兰群岛还是大英帝国遥远的前哨时,许多人从苏格兰高地赶来当牧羊人,这些岛屿与设得兰群岛或斯凯岛有着奇怪的相似之处-荒凉的岩石景观,狂风暴雨,近海-就像苏格兰的一部分已经分裂进入大西洋,向南漂流了8000英里,经过爱尔兰,然后是葡萄牙,经过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向下越过巴西和乌拉圭的海岸。但在这里,在空气非常清新的日子里,人们知道漂浮的冰山一定很近。这里有水边的企鹅:三英尺长的王企鹅,戴着蛋黄围兜;蹲着的岩石企鹅,头上有尖利的黑色羽毛,像胶状的头发;戴着奇思妙想的帽子的绅士企鹅。三月,当瘟疫肆虐时,企鹅们无所事事。它们正在蜕皮,因此不能游泳或进食。人们说,换羽既累又不舒服。企鹅们站在海浪附近的人群中,背对着风,等待它们的羽毛脱落。
话又说回来,当瘟疫真的来临时,可能就无路可逃了。每周有两个商业航班离开这些岛屿:一个是周六飞往智利南部的蓬塔阿雷纳斯(Punta Arenas),另一个是周三飞往圣保罗。即使在正常情况下,这些航班也经常因为机场的强风而被取消,现在这两个航班都已经停止。有飞往英国的军事航班,但这些航班依赖中途停留来加油,如此多的国家已经关闭了边境,以至于有几个星期根本没有航班,这些岛屿也完全被切断了。曾经有一艘船每月从蒙得维的亚运来一次水果、干货和邮件,在定居点周围巡视,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居住在更偏远农场的人们被警告说,如果他们生病了,就没有人能来接他们,所以那些风险最大的人正在前往唯一的城镇-东福克兰的斯坦利-如果可以的话。
直到最近,福克兰群岛还是一个准封建殖民地,在那里,过去的阿卡迪亚式的不列颠被保存在缩影中-人口1800人,领土略大于牙买加。岛上的居民几乎都声称有英国血统,他们吃英国食物,种植英国花园,花园里挤满了花坛和侏儒。他们把联合航空的千斤顶从他们的汽车和温室里飞了出来。他们展示了母国罕见的爱国主义:他们庆祝女王生日,每周日在大教堂唱国歌。当年长的岛民谈到英国时-即使他们从未去过那里,他们的家人已经在福克兰群岛生活了五代人-他们称它为“家”。
约翰·福勒于1971年乘邮轮抵达。在海上度过了可怕的几天后,他在凌晨四五点钟醒来,发现船是静止的。他穿着睡衣上了甲板,看到它们停泊在斯坦利的码头上,离港口上方陡坡只有几条街的小镇,有彩色屋顶的小白房子,空气中弥漫着泥炭烟的味道,看到了看起来像三曲的东西。
在2013年的全民公投中,除了三名选民外,所有选民都选择保留为自治的英国领土,但福克兰群岛现在不再像以前那样是英国人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已经成为一个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的地方-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暂住的工人,逃离国内政治的人。今年2月,一个小型代表团抵达,代表一群对北京感到紧张的香港华人。几个南非白人出现了;3月初,一名来自开普敦的离异承包商带着一叠名片造访了斯坦利的办公室,他最近刚从科威特的十年监狱中脱颖而出。但阿根廷主权主张的持续压力迫使岛上居民向世界证明,他们不仅仅是一群随意的定居者,除了他们生活的土地什么都没有。
直到三百年前,福克兰群岛一直是无人居住的,除了狼、海豹和岛鸟-企鹅、蝎子、Skuas和黑脸的地面暴君。1690年,英国船长约翰·斯特朗进行了第一次有记录的着陆,但他没有停留很长时间。法国人在17-60年代建立了一个定居点,并很快被移交给西班牙人。在同一时期,英国人在西福克兰附近的桑德斯岛(Saunders Island)维持了几年的前哨,但在与西班牙人发生冲突后,他们认为这不值得,于是回国,留下了一块维护英国主权的铅牌匾。18世纪末,西班牙人在东福克兰驻扎了40年。18世纪20年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许可下,一位来自汉堡的胡格诺牧牛场商人从大陆雇佣了高乔,开始了一项持续了几年的定居点,直到被一艘美国炮艇摧毁。英国人在1833年收回了这些岛屿,但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在斯坦利建立了一个城镇。
在那之后,人们从四面八方乘船而来--来自英格兰的牧羊人,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渔民,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海豹猎人,捕鲸者,海盗。在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斯坦利的港口挤满了在环绕合恩角的可怕旅程中失事的废弃船只-这是前往加州淘金热的欧洲探矿者选择的路线。许多水手被遗弃了-他们与死亡擦肩而过,或者只是因为在从蒙得维的亚出发的崎岖航道上晕船而受到创伤。他们躲在Camp(坎波的英国化,或“乡村”-在福克兰群岛,意思是所有不是城镇的地方),直到他们的船离开。后来,人们乘坐游艇抵达-他们在前往其他地方的途中驶入斯坦利港,并决定定居-一对来自澳大利亚的夫妇,一家来自法国。
一名在外岛生活多年的男子过去常说,福克兰群岛有两种人:坎普的人大多是在清理期间被赶出高地的农民的后裔,他们勤劳诚实;斯坦利的人是因为行为不端而被扔下船的人的后裔,不值得信任。但是夏令营里有各种各样的。20世纪60年代,当莱昂内尔·布莱克(绰号蒂姆)在西福克兰的希尔湾农场担任经理时,那里有一些青少年罪犯在那里工作,其中一人刚刚从博斯塔尔来到福克兰群岛。要让人们搬到八千英里外去做低薪合同工并不容易,所以你不能挑剔。蒂姆在“农民周刊”上登广告招聘牧羊人,招聘了一名钢铁工人、一名园丁和一名电影放映员。
来的人就是这么多:他们回复了一则广告。福克兰群岛不是大多数人想去的地方,甚至不是听说过的地方,所以你必须引起他们的注意。在早期,农场经理会在英国各地的报纸上发布通知。后来,人们会在Catererglobal这样的酒店工作网站上发布简历,或者在谷歌上输入“海外工作”。你没有得到那些留下很多东西的人。就连蒂姆本人也在那里,因为他是第三个儿子,他父亲在萨默塞特的农场没有地方容纳他。
蒂姆是福克兰群岛的贵族:他的祖父罗伯特·布莱克在19世纪70年代在希尔科夫买了一半的股份;他在农场生活了20年,有8个孩子。在世纪之交前不久,他的身体因关节炎和骑马事故而受损,他回到了英国,但他在希尔湾的那部分土地留在了家里。这是一种常见的模式:早期的所有者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但到了20世纪,大多数农场都由英国的缺席地主拥有,或者由福克兰群岛公司(Falkland Islands Company)-相当于东印度公司的福克兰群岛公司(Falkland)拥有,将贸易和治理结合起来。政府是由不与当地人打成一片的外籍人士管理的:福克兰群岛岛民是殖民地臣民,受到了相应的对待。在一年一度的五月舞会上,人们跳起了华尔兹
当他跟在羊群后面走的时候,他总是看着它们,看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动作:
你还得注意其他的事情。春天,海鸥和土耳其秃鹫袭击羔羊,啄食羔羊的下巴,直到它们啄出它的舌头。你会看到一只母羊的肚子上沾满了鲜血,羊羔曾试图吸吮,但没有舌头可以吸吮。那时候,除了自家羊肉需要的几种动物外,你不屠宰肉,因为岛上没有屠宰场,也没有办法把肉卖到市场上,所以当一只羊太老了,不能产好羊毛时,你就把它杀了,然后把它的身体扔到海滩上。
蒂姆·布莱克(Tim Blake)在希尔湾(Hill Cove)的头20年里,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这个农场和福克兰群岛的其他农场一样,运行着一个在英国逐渐被立法取缔的制度,即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卡车法案(Truck Act)。农场工人很少处理现金:他们拿到的是纸币,而且在和解的农场商店有一个信用账户。到了年底,农场经理会告诉他们减去购买量后还有多少钱,他会为他们交税,把剩下的钱存入政府的储蓄账户,或者帮助他们投资。这位经理可能是唯一的地方当局-他主持婚礼并分配惩罚;据说就在蒂姆·布莱克来到希尔湾前不久,那里的一名男子因吹口哨而被解雇。因为饮酒可能是个问题,特别是在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的冬天,农场商店对酒类的销售实行配给销售。当一个人到了不能再干农活的年龄时,他不得不退休,这意味着他不得不离开农场的房子搬到斯坦利去。但在斯坦利,退休人员除了去酒吧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可做的,而且他们经常在酒馆过后不久就去世了。
农场经理和他的家人住在“大房子”里,有一个女佣、一个厨师和一个园丁。已婚男子要么住在主居民点的小房子里,要么住在与世隔绝的农场的“外面的房子”里,在那里他们可以照看附近的羊群。作为合同的一部分,这些家庭得到了住房,并给了羊肉吃,给牛喝牛奶。为了多样化,他们吃企鹅蛋,企鹅蛋又圆又大,像网球一样大;他们尝到了海藻的味道,蛋黄是红色的。这些岛屿上的教育参差不齐。一些较大的定居点,有十到十五个孩子,有一所校舍,但许多孩子有一位巡回教师,他可能每两三个月就和他们住两周。在老一辈农场管理者中,一些人认为把农场孩子教育得太好是不谨慎的。
单身农场工人和一名厨师住在棚屋里。除了大房子里的女佣,附近可能没有单身女性:1973年人口普查时,整个西福克兰有一个未婚女性和51个未婚男性。许多女性嫁给了英国士兵-东福克兰有一小部分皇家海军陆战队驻军-然后离开了岛屿;即使男性找到了结婚的人,离婚率也非常高。所以,如果一个男人受伤了,照顾他的很可能是经理的妻子。当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在斯蒂芬斯港(Port Stephens)的一台发电机的传动带下将手压碎,血液从他的指尖喷出时,是农场经理的妻子在蜡烛火焰上加热了一根针,并将其穿过他的每一个指甲,以释放压力。
如果没有足够的已婚男子住在外面的房子里,有时会有一个单身男子独自住在那里,一次几个星期见不到任何人。20世纪50年代左右,在西福克兰的一个农场里,有一个独自生活的牧羊人,他病得很重,以为自己快死了,所以他把狗放出来,喂鸡,躺在床上,双臂交叉在胸前,等待死亡,想着迟早会有人找到他。过了一会儿,他感觉好些了,又起来了,几十年后这个故事还在讲。每个人都认为这很好笑。
在定居点里有一种压缩的亲密关系,既令人窒息又令人窒息:在这么小的地方几乎没有什么秘密,一家人相互依赖帮助。如果有人生病了,医生可能需要几天时间才能找到他;分娩很少,所以人们不得不借钱。每年剪毛结束后,每个主岛上的一个定居点都会举办体育周,农民的家人会聚在一起庆祝。白天,有赛马、剪毛比赛和牧羊犬选拔赛,有时早餐喝杜松子酒和补品,晚上喝酒跳舞,一直跳到凌晨四五点。除了房子没有别的地方可住,所以可能有20个人睡在两三个房间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几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来,因为营地里没有电话,邮件每个月都会来一次。当邮轮为其中一个外岛带来信件时,大陆上的人会生火让人们知道信件来自哪里:一封是给当地的,两封是给英国的。后来,当寄往外岛的邮件到达斯坦利时,它们被分拣成麻袋,然后从飞机的舱门扔到岛上。1950年,政府建立了一项连接40个农场的无线电话服务;这个系统的缺点和魅力在于人们可以听到彼此的电话。每天上午十点,斯坦利的一位医生会通过无线电话进行会诊,每个人都会停下手中的工作,围坐在收音机旁,端着一杯茶,听岛上的居民描述他们的咳嗽、疼痛、妇科问题和肠易激的情况。
推动福克兰群岛在20年内走过两个世纪历史的巨大变化实际上始于战争前不久,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大约在托尼·希斯曼(Tony Heathman)学会剪羊毛的时候。托尼在这些岛屿上的根可以追溯到蒂姆·布莱克(Tim Blake)的根,但他来自农场工人,而不是绅士:他主要在东福克兰的海豚角长大;他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