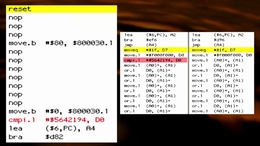“街头霸王2”不仅仅是一款游戏,它还是一个门户。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动乱期间在北爱尔兰长大,我发现了一个门户网站,它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彩色照耀着这个世界-由于贫困、冲突和分裂-这个世界经常是单色的。很容易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浪漫化和翻新为霓虹灯和合成器的时代,而忽略了前互联网时代的简朴,在这个时代,在首都以外接触文化的机会往往如此有限,以至于它呈现出神话般的比例,需要挖箱子和寻找磁带,并被嫉妒地囤积起来。一个例外是游乐场的交通空间,那里有嘈杂的声音和灯光。我和我的朋友们很快就被禁止进入我们当地的游乐场-部分原因是轻微的犯罪行为,但主要是因为在一个以利润为动力的地方被剥皮了。幸运的是,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避难所:在我家乡德里的一个工人阶级聚居区,我家街道上一家录像带租赁店的后面,有一款街机游戏。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一切。
“街头霸王2”(1991)只是一款游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设计初衷是和其他任何一款游戏一样能吃掉同样多的硬币,但它要多得多。它构成了一个激烈竞争的竞技场,附近的年轻人和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人都可以在其中考验自己的技能和主张自己。它还提供了一个避难所,当你走进房间,发现只要你能负担得起玩游戏的费用,你就可以独自玩这个游戏。游戏是与世界接触的一种形式,是找到你在其中的位置的一种方式,是建立社区的一种手段,也是一种主权;它为你提供了逃离、孤独和享受社区的能力。通过“街头霸王2”,你发现了你和其他人开始和结束的分界线,注意到那些玩得精神错乱的人,以及游戏是如何演变成现实生活中的对抗的。渐渐地,你开始意识到自己记忆秘密动作和制定策略的能力。你通过测试自己发现了自己是谁。
“街头霸王2”也是通向其他世界的一扇窗户。这款游戏对不同角色和全球背景的刻画陈词滥调到了可笑的程度,这并不重要。(例如,俄罗斯摔跤运动员赞吉夫(Zangef)最初打算叫伏特加·戈巴尔斯基(Vodka Gobalsky)。)。我们太年轻了,除了它所激发的无限的好奇感之外,我们什么都注意不到,特别是当我们开始意识到场景是基于真实的地方时,尤其是当我们开始意识到场景是以真实的地方为基础的时候。正是因为我们的无知和纯真,在达西姆寺庙的背景下,或者在赞吉夫工厂地板上的锤子和镰刀的背景下(在苏联解体的时候),或者在E.Honda的浴室里迷人的浮世绘风格的瓷砖的背景下,看到象头神甘尼萨,感觉令人陶醉。令我惊讶的是,柳氏舞台上的月光城堡是根据日本松江堡的真实城堡建造的,而且在泰国的大城府可以找到萨加特级别的巨型卧佛。春礼的香港的街道和市场似乎在召唤我们去探索。街头霸王2可能只是一款游戏,但它给了我们一种诱人的感觉,当我们长大并离开家时,真实的生活,以及它所有的希望,就在那里等着我们。
在我扮演街头霸王II的20年里,互联网、移动技术和全球化彻底改变了世界。我成长的这个国家被和平进程改变了,不管这个进程有多有缺陷。然而,随着当前新冠肺炎危机的国际封锁,偶尔会有一种感觉,我们回到了那个似乎永远不会结束的黑白时代;寻找门户不仅是为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或激励我们,还希望它们能以某种方式引领我们走向未来。世界仍然在那里,我们将回到什么将取决于我们如何共同行动。这不再只是一场游戏了;也许它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