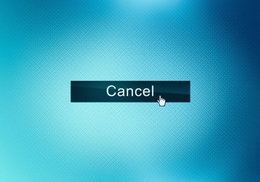数字化的文化战争
他说:“我相信理想的未来,有赖於我们刻意选择行动的生活,而不是消费的生活,有赖于我们创造一种生活方式,使我们能够自发、独立而又互相联系,而不是维持一种只容许制造和取消制造、生产和消费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只是通往环境枯竭和污染之路上的一个中转站。”未来更多地取决于我们对支持行动生活的机构的选择,而不是我们不断发展的新意识形态和技术。“-伊万·伊利奇(Ivan Illich),美国非学校社会(1971)。
编程说明:很高兴你们中的这么多人发现音频版本很有用。你现在可以在iTunes、Spotify和Stitcher上以播客的形式关注时事通讯,如果通过“播客”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我在以一种不那么生动的方式阅读主要文章。只需点击上面的“在播客应用中收听”即可。希望这涵盖了你们中发现该功能有用的大多数人。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留下评级或评论。
社会学家詹姆斯·亨特(James Hunter)发表“文化战争:为定义美国而奋斗”一书已经过去了大约30年。自那以后,这个有名无实的短语已经成为公众谈论自己的主要内容,尽管就像所有这样的短语往往做的那样,在亨特关于美国公共生活中当时新颖的裂痕的争论中,它已经脱离了本土语境。
最近,我发现自己比往常更多地求助于这个短语。我通常会回避它,因为这个短语本身似乎鼓励了它试图描述的东西。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分析框架,这个短语使我们有条件将文化动力视为战争,从而将我们锁定在这样一个观点所带来的功能障碍中。“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等等。然而,尽管我心存疑虑,但对于公共领域发生的许多事情,这句话无疑是一个有用的速记。因此,举个例子,当有人问起美国的口罩惨败时,我只是简单地说,面罩很遗憾地被卷入了文化战争,这可能太过花言巧语了。但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需要考虑。正因为它是如此有用的速记,它可能会阻碍我们更仔细、更深入地思考我们的情况。毕竟,概念既可以澄清,也可以模糊。
但我也一直在思考“文化战争”的框架,因为无论我们对这种冲突说什么,在亨特写书后的近30年里,它们都不是静止的。当然,一个关键的发展是,这三十年几乎与数字公共领域的出现完全重叠。事实上,几周前,我想到了一个似乎很有用的类比:数字媒体的出现对于文化战争来说,就像工业化武器的出现对于常规战一样。
考虑到这一论点,我认为重新审视亨特的作品可能会有所帮助,看看它是否仍能为我们的现状提供一些启示,特别是探索数字媒体对“文化战争”的进行产生了什么影响。为简明扼要起见,虽然我不确定我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成功,但我选择列出几个要点供我们考虑。所以我们开始吧。
这一点似乎显而易见,但一开始就值得强调。我们沉浸在数字媒体流中的一个后果往往是对现实主义的高度体验,这既包括缩短我们的时间视野,也包括假设我们正在体验的东西一定是新颖的或史无前例的。这种情况的危险在于,我们将文化战争误认为是社交媒体的影响,而不是将其理解为美国公共生活的一个长期特征,与社交媒体有着复杂的、多方面的关系。
1991年,亨特考察了人们熟悉的领域--例如:家庭、言论自由、艺术、教育、最高法院和选举政治--充分记录了我们倾向于哀叹当今公共话语状况的大多数特征(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两极分化、辩论的棘手和痛苦的性质、潜在的敌意、缺乏文明、将意识形态对手描述为需要铲除的敌人,特别是在目前的辩论中,亨特所说的“不容忍的幽灵”和所谓的“极权主义的‘威胁’”被亨特称为“不容忍的幽灵”和所谓的“极权主义的‘威胁’”,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的辩论中,亨特称这些特征为“不容忍的幽灵”和所谓的“极权主义的‘威胁’”。
在描述他所谓的“中庸之食”时,他还指出,需要“激动人心”意味着“比起有条不紊、深思熟虑的辩论,耸人听闻的公开辩论更有可能引起普通人的注意”。“响亮的、耸人听闻的喧嚣的净效果,”他补充道,“就是让更安静、更温和的声音变得无声。”
亨特还评论了公共话语中高度的怀疑:“在当今充满担忧和不信任的氛围中,”他写道,“试图与众不同和改善的观点往往会被归类为所有其他不肯定忠于自己事业的观点。”亨特还对媒体技术在创造这些条件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但我们将在下面的另一点上谈到这一点。
最后,虽然亨特的作品普及了“文化战争”的讨论,但他并没有创造出这个短语,正如他所说,这个短语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文化战争的概念起源于德语单词kulturkampf,即“文化斗争”,它专门指定了新教和天主教派别之间为控制新统一的德国国家的文化和教育机构而进行的斗争。
正如亨特继续展示的那样,美国文化战争的起源也植根于19世纪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以及后来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的类似斗争。当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些主要是在一个更大的、明确的西方宗教参照系内的内部争吵。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亨特意识到贯穿美国社会和政治的这些冲突的性质发生了重大转变。文化战争是亨特为更好地理解这些发展并绘制其后果所做的努力。
重要的是要提醒自己,文化战争的势头先于社交媒体的出现,因为我们不应该自欺欺人地认为,只要我们设法控制社交媒体,一个温和和文明的公共领域就会出现。不过,正如我将在下面讨论的那样,社交媒体显然对事情没有帮助。
回想一下,正如亨特坚持的那样,文化战争包含了关于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美的深刻而真实的分歧,这是很有用的。可以说,在以一系列来自前线的报道开始后,亨特邀请我们考虑以下问题:“如果这些事件不仅仅是政治疯狂的闪光灯,而是揭示了参与根深蒂固的文化冲突的不同社区的诚实关切,会怎么样?”
亨特认为事实的确如此。“美国,”他声称,“正处于一场文化战争之中,这场战争已经并将继续在公共政策和各地普通美国人的生活中产生反响。”尽管文化战争的性质再次发生了变化,但事实无疑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现在我们在谈论“文化战争”时,往往带有更多贬义或轻蔑的意味,而且带着不少恼怒。我理解这样做的诱惑力。事实上,我最近不止一次这样用过这个词。事实上,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文化战争的当代表现往往以看似微不足道的不满为特征,例如,关于什么构成适当的圣诞节/节日问候。但是,即使在他们的举止表现上,他们仍然背叛了一些潜在的道德关切。情况也是如此-我认为这是更相关的考虑-文化战争现在往往是由我们可能认为是雇佣兵的骗子推动的,他们煽动和利用任何真诚持有的道德原则,最初激起了普通公民的担忧。
因此,虽然文化战争数字化的一个后果是普遍的不信任假设,但我们应该记住,文化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植根于根植于根植于相互竞争和不可调和的道德权威来源的根深蒂固的道德信仰。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参与者和立场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显然不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在任何特定的文化战争小规模冲突中,我们看不到所有的小题大做是为了什么,那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种不同的道德秩序中,而不是那些我们认为自己的观点如此令人困惑或反感的人。
这里的关键很简单:如果我们把文化战争问题,特别是那些我们不关心的问题,简化为仅仅是摆姿态、不诚信的政治化,或者是真诚的乡下人被虚无主义的操作者欺骗的情况,我们就会误解我们的文化状况。
那么,如果我们不能将文化战争归咎于数字媒体,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正如我上面所建议的,我认为把这种关系类比为工业化战争带来的战争变革是有用的。
我首先要指出的是,媒体技术在亨特的分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亨特指出:“使公共演讲成为可能的媒体技术,赋予了公共话语以其自身的生命力和逻辑性。”以下是他如何将此事放在一份冗长的声明中,为了在正文中强调,这份声明用斜体表示:
当代公众讨论的两极分化实际上被进行这种讨论的媒体所强化和制度化。正是通过这些媒体,公共话语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公共修辞的类别不仅脱离了演讲者的意图,而且还压倒了绝大多数将自己定位于这些辩论“中间”的公民的观点和观点的微妙之处。
现在,令人惊讶的部分来了。在题为技术与公共话语的一章中,亨特将他的大部分讨论都花在了…上。直邮,你知道,在选举期间到达你邮箱的无数明信片和传单。亨特还谈到了电视和广播,但他认为直邮是真正引发文化战争的相对新颖的媒体技术。我不是有意贬低他的讨论,远非如此。了解旧媒体在新媒体出现时的影响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更重要的是,选择直接邮件与数字化文化战争的条件进行了引人注目的比较,在数字化文化战争中,直接邮件在有针对性的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广告中找到了最相似的东西。后者的相对复杂、个性化、频率和规模很好地说明了数字化对文化战争的影响。
那么,让我们回到我对工业化战争的类比。虽然历史学家倾向于将工业化战争的起源定位于美国南北战争的后期,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才看到工业技术对战争行为的全面影响。工业化应用于战争的显著特征包括武器装备(机枪、远程火炮、爆炸炮弹等)的重大进步,蒸汽动力铁甲舰艇的发展,铁路部署军队,电报即时通信,以及后来坦克、飞机和毒气的出现。
简而言之,战争的工业化通过提高现代军队的速度、规模和力量,极大地增强了现代军队的破坏力。此外,工业化战争变成了全面战争,涵盖了整个社会,模糊了平民和战斗人员之间的界限。最后,正如所有形式的机械化所趋向的那样,它使远距离有效杀戮成为可能,从而使战斗体验进一步去人格化。作为这些发展的结果,现代战争的准则、战术、战略、心理和后果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当然,这个类比的逻辑是直截了当的。数字媒体极大地提高了发动文化战争的工具的速度、规模和力量,从而改变了它们的规范、战术、战略、心理和后果。
文化战争的小规模冲突现在一下子就展开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战线很快就形成了。数万名参与者(并不是所有人)被动员并部署到前线。他们进行大规模的工作,通常是针对某些个人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主要是败坏名誉和使人不快,但也会迷惑、煽动、耗尽和打击士气。旧的、也许总是理想主义的劝说和驳斥目标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此外,成为激战的小规模冲突无限期地蔓延,成为人们关注的黑洞,成为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消耗。
沿着这些思路,我们可以看到,数字媒体的力量在于它们的直接性和规模,但也在于它们扩大战争的能力。直邮可能是针对你的,但社交媒体让你直接参与到行动中来。带上你们的迷因,同志们。我们不再仅仅是政治和知识阶层的精英战士为我们的忠诚而进行的战斗的旁观者。在数字化前线,我们都全副武装,并敦促我们加入这场战斗。精英们自己很快就成了他们曾经煽动的对自己有利的文化战争的受害者。
数字化也会引发全面的文化战争。我们体验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这既是文化战争武器广泛分布的结果,也是这些同样的工具如何侵蚀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古老的、始终脆弱的鸿沟的结果。现在,文化战争是全面的,因为它们是包罗万象的,毫不留情的。与其说我们总是在前线,不如说是前线一直在我们身边。虽然文化战争确实总是涉及对私人事务的公开辩论,但数字化的文化战争吞噬了私人生活的更多方面。
思考这一问题的一种方式是沿着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对前台社交生活和后台私人生活的古老戏剧性区分。在文化战争的背景下,我们可能会将这种区别框定为前线的社会生活和相对安全的后方展开的私人生活。数字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前台和后台的界限,让我们参与到永久印象管理的工作中,同样,数字媒体也模糊了文化战争中前线和后方的区别,使我们体验的方方面面都成为潜在的素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一些文化战争的小规模冲突是轻率的。数字工具催生的升级逻辑要求越来越多的平民生活被卷入这场斗争,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
这也是框定所谓“取消文化”辩论的有用方式。这场辩论正是由文化战争的数字化引发的,这使得有必要就应该如何进行战争谈判达成新的理解。谁是合法的目标?什么是相称的反应?什么行动和意见应该被合法地吸引去战斗?旧的类比规则已经行不通了,我们也没有达成新的共识。
因此,虽然认为数字媒体引发了文化战争是错误的,但如果认为我们现在只是在经历同样的旧文化战争,那也同样是错误的。显然,新的数字战场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冲突的性质。
同样应该清楚的是,数字化的文化战争给出了一切迹象,表明从本质上和设计上来说,这场战争是没完没了的。鉴于文化战争植根于长期存在的道德和意识形态冲突,这些冲突源于从根本上不可调和的道德权威来源,它们不会简单地逐渐消失。降级的诱因很少(除了纯粹的疲惫),很难想象休战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更不用说真正的和平或和解了。鉴于支撑数字化文化战争的平台将从其扩散中获利,文化战争源于并回答了人类采取有意义和道德影响的行动的基本需求,特别是在一个否则会让我们在道德上被麻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媒体政治政权中,那么在同样的程度上,它们将倾向于有增无减。
虽然了解数字媒体如何改变了文化战争的进行方式是很重要的,但我倾向于发现最有趣和最重要的是文化战争的界限是如何被重新划定的,联盟是如何重新配置的。同样,亨特30年前的工作在解释文化战争是如何重新划定文化冲突的界线时特别有用。我们需要类似的努力来理解为什么我们的旧类别不再作为当前社会政治领域的指南。但是,虽然我认为这是更有趣和更重要的领域,但我担心我要提供的肯定让人感觉更具试探性和投机性。也就是说,这里有几件事需要考虑。
首先,作为背景,亨特认识到20世纪末日益激烈的文化战争与以前的情况不同,因为美国社会见证了道德权威来源的激增,并因此将传统行为者重新调整为新的结构。他认识到,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以及各种新教教派彼此分开的旧界线不再牢固。道德权威的新分配跨越了旧的制度界限。亨特确定了两个关键群体,他称之为小o正统派和小p进步派。他们的主要特征是,他们是否像正统那样把道德权威放在外部和传统的来源上,或者像进步者那样把道德权威放在自我的决定或科学理性主义的交付上。(需要注意的是,亨特使用“正统”和“进步”这两个词的方式很特殊,与当时或现在的用法重叠,但并不等同。)。例如,在亨特绘制的当时新兴的文化战争中,东正教天主教徒更有可能与东正教浸礼会教徒和东正教犹太人找到共同事业,而不是与他们表面上的共同宗教者-进步天主教徒-找到共同事业。令人震惊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位著名的天主教道德哲学家写了一本名为“全基督教圣战”的书,敦促那些猎人呼吁东正教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在文化战争前线联合起来。很难想象有比亨特分析的那种调整更好的例子了。
其次,虽然亨特专注于媒体技术的部署方式,以推动新的文化战争联盟的现有原因,但我认为重要的是要了解文化战争的数字化本身是如何产生新的配置的。例如,直接邮寄者针对的是现有的邮件列表。在某种意义上,直接电子邮件的工作方式是相同的,即使它具有增强的功能。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