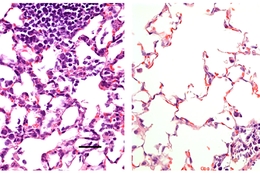为疫苗结果做准备
所以让我们花几分钟时间来思考一下当疫苗试验开始读出时会发生什么。我假设数据会及时免费获得(这意味着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因为替代方案并不是真正好的选择。另一个不太好的选择是宣布第一个宣读即时获胜者,因为(正如安东尼·福奇所指出的)这肯定会搞砸其他人的审判。但是,如果我们避免这些错误(没有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还有一些相当可能的事情,我认为一般公众还没有做好准备。
其中之一是:如果第一批疫苗的结果不是很令人印象深刻怎么办?这是有可能发生的。我真的希望不会,但业内任何人都会告诉你,在你进行疗效试验之前,你不知道真正的疗效会是什么样子,这对疫苗和其他任何东西都是一样的。我会说,可用的生物标记物(抗体和T细胞)在疫苗工作中比在许多其他领域要强得多,但另一方面,它是免疫学。充满了有趣和有趣的惊喜。因此,如果第一次真正给出可靠疗效读数的试验结果比我们所有人都希望看到的要低/弱,我猜媒体和公众不会接受得太好。我认为,人们会争先恐后地拍摄“天哪,我们不能给科罗娜制造疫苗”,这会播下一些绝望和恐慌的种子。我预计股市也不会很好地接受这一消息。
但是,即使第一个结果不是很好,也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被灌输了。拥有几种不同的疫苗,使用不同的平台技术,这是一件好事。我们真的要拭目以待,看看各种方法会产生什么,尽管“等待和观望”并不是现在的时代精神。我们有不同的腺病毒(和其他载体,稍后会出现),灭活病毒疫苗,候选mRNA,重组蛋白-没有理由认为这些都会出现相同的结果,这一点很重要,要记住。
在这一点上,还有另一种很有可能的可能性:功效拼凑的被子。如果我们得到的结果是混合的,疫苗A相当好,但在老年患者中并非如此,而疫苗B在该队列中似乎更好,但更难推出分发,而疫苗C在不同的患者队列中显示出更均匀的结果,但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候选疫苗中都被其他候选疫苗击败,而疫苗D很强,但肯定有更多的不良事件。。.你明白我的意思了。我可以很容易地想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问题是,它不会一下子就掉下来。我们将一个接一个地获得这些不同的结果,并将它们放入不可避免的混乱图景中,随着更多的数据点可用来调整我们的计划。总体而言,我认为过早宣布一种获胜的疫苗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除非有什么东西出现,只是在整个领域踢了一脚冠状病毒屁股,坦率地说,这是可以接受的),但告诉每个人等待,看看下一种疫苗会带来什么,可能不会得到很好的接受。开始给人们服用任何看起来合理的东西都会有巨大的压力,你不能为此责怪任何人。
关于这些不良事件,我不是免疫学家,但我最担心的可能是格林-巴利综合征。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我把它读成类似gee-yah bur-ray的发音,但我在野外听过很多其他更英国化的发音。无论你怎么说,GBS都是一种自身免疫反应,导致神经系统的髓鞘受到攻击-显然是坏消息,但好的部分是大多数病例都能解决。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这样的,即使是许多解决的问题也涉及到在医院度过一段时间,病情相当严重。GBS在一些呼吸道感染后自发发生,原因是免疫学原因仍在研究中,并且最常见于年轻女性。它可以在接种疫苗后出现,就像它在感染后出现的方式一样,它被广泛认为是1976年猪流感疫苗推出的大问题之一,而且肯定是疫苗开发人员一般都在密切关注的事情。我们不想纠结于这个问题,但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事件,只有大型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试验才有机会让我们了解这个问题。作为背景,1976年的疫苗被认为导致每10万接种疫苗的人中就有一例额外的GBS病例-在你走进更广泛的人群之前,你很可能根本不会感染这种疾病。“青少年在冠状病毒注射后被送往医院”不是一个对任何人都有好处的标题。
更广泛的人口总是令人担忧的问题,
我希望这不是一个科学上不识字的问题。从理论上讲,疫苗不是“一刀切”的想法可能是一件好事;如果几种疫苗通过了测试,每种疫苗都可以针对特定的人群,那么每种疫苗的生产量就可以减少。然而,这引发了一个问题:暂且不谈在美国这样一个相对特权的国家,一个相对特权的个人拥有这样做的资源和机会的伦理影响,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接种疫苗,然后后来发现另一种疫苗对他或她的个人情况更有效,然后“切换”到那种疫苗,这是可行的吗?或者混合疫苗等同于混合药物?我们是不是永远被我们选择的第一个词“卡住”了(请原谅双关语)?
话虽如此,我非常担心断章取义的惊吓标题的影响,比如这里假设的那些(更不用说社交媒体的“病毒式”影响了)。据草率报道,为数不多的几个异常值可能会扼杀足够多的人信任疫苗以确保其在增强免疫力方面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在某些方面,我想我们在报道香港“再感染”事件时,可能已看到这一点。)。
我还担心“让每个人都通过两针免疫课程的后勤保障”--恐怕“非同小可”不足以形容这一点。这将意味着将可获得的疫苗数量翻一番(仅在美国就从约3.2亿增加到约6.4亿),并将涉及的成本翻一番。也许更重要的是,这将对疗效造成重大障碍-我们需要记住,能够提前一个月为这样的事情做计划是世界上许多人-穷人、无家可归者、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和/或混乱的人物生活-不享有的特权。那些每周一周、每天一天、甚至一小时一小时生存的人不太可能遵守他们的预约。这将不是一个向前推进的微不足道的问题。
我的年龄还不足以亲眼见证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推出,但我的理解是,相当多的人最终在某种程度上同时接种了两种版本的疫苗。但你会想要单独测试它们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仅仅因为它们单独是安全的就认为它们在一起是安全的是不明智的,而且取决于方法(特别是像腺病毒载体疫苗这样的东西,在我的门外汉的理解中-德里克的帖子已经大大改进了这一点),第一针可能会干扰第二针,使其效果低于其他方法。
我对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推出记忆犹新。我既接受了Salk疫苗(一种注射),也接受了萨宾口服系列(SOS)。许多畏首畏尾的人对索尔克疫苗望而却步;是SOS给美国的脊髓灰质炎带来了致命的打击。SOS需要两个(或更多?)。几周内的剂量。我记得安瓶放在我们冰箱的架子上。
索尔克疫苗于1955年推出。我8岁的时候,我记得我站在学校门前排队等待接种疫苗。我们都接种了疫苗。没有真正的选择。沙宾疫苗于1961年推出。我当时14岁。我也接种了疫苗。
我们很高兴接种了这两种疫苗中的任何一种。小儿麻痹症很可怕。我认为比贪婪可怕得多,因为小儿麻痹症针对的是儿童和年轻人。
今年早些时候,公共广播公司(PBS)有一个关于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精彩专题。我强烈推荐它:
就像上面的保罗·W和沃尔特·索布查克一样,我小时候既接种了索尔克脊髓灰质炎疫苗,也接种了萨宾脊髓灰质炎疫苗。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也接种过目前的肺炎疫苗(我知道这些疫苗针对的是略有不同的菌株,尽管我相信有重叠),也接种过带状疱疹疫苗Zostavax和Shingrix(尽管Zostavax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在美国不再是常规疫苗)。通常情况下,接受针对同一疾病的两种不同疫苗是不成问题的。但显然,基于腺病毒的疫苗(mRNA疫苗)有一个考虑因素,即人们可能对腺病毒有抗体,因此疫苗不能提供对新抗原的免疫力-这一点以前在本博客和其他地方已经讨论过了。因此,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不能只轮流服用每一种目前最受欢迎的疫苗(即使假设有售)。
顺便说一句,我同时接种了Salk和Sabin疫苗,但它们相隔一年多。从我当时收集的情况来看,沙宾疫苗对那些以前接种过索尔克疫苗的人效果更好。副作用较少。等。
不过,您不能真的对此一概而论。有些病毒在接种多种疫苗后可能会变得更糟。(登革热是我在这里唯一真正确定的疾病,但它是存在的证据。)。
另外,顺便说一句,我两个都吃过了。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接种过口服活疫苗-我非常耐心地忍受着一抱针孔,然后最后一个他们干脆作为滴管喂给我,里面装满了葡萄味道的东西。我被激怒了。你的意思是我可以把它们都吃光?!我的父母试图向我解释小儿麻痹症是特殊的,但我没有。那些懒惰的、憎恨儿童的医生需要采取行动,将所有疫苗都制成可食用的形式。
大约25年后,我在一家病毒学实验室工作,有人想在普通设备上研究脊髓灰质炎,所以我买了助推器-灭活的东西。唯一的副作用是,当我一个月后献血时,筛查献血者的人加倍服用了。
“…。仅仅因为他们单独在一起是安全的,就认为他们在一起就会安全,这是不明智的。“。
我们独立测试药物的安全性,然后每天不假思索地狼吞虎咽地吃下2-5种(或更多)组合。
疫苗组合的安全性将通过上市后监测进行评估,就像评估DUG组合一样。
我不相信我们在这种监视上做得如此出色,但无论如何,这是理论上的。
德里克提到的没有“一刀切”疫苗的情况并不新鲜。目前的疫苗在效力和人口统计学上一直存在差异。Zostavax和Shingrix之间、注射版本和鼻腔喷雾(FluMist)版本的流感疫苗之间存在差异(儿童和老年人群之间的有效性/无效性)。因此,如果不同口味的新冠肺炎疫苗针对不同人群,这不会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护理人员会根据标签标准进行选择。
参与管理脊髓灰质炎系列…的“护理者”相对较少,如果你的意思是指与接受者有1对1关系的私人医生。要么是Salk版本,要么是Sabin版本。他们都在学校接受管理,整个班级都在公共区域集合,一次走到一张椅子或桌子前,在那里注射或注射安瓶。
目前的疫苗接种是在医生/护士/药剂师的环境下进行的,因此我使用了通用术语“护理员”。如果它是在工业(大规模疫苗接种)规模上推出的,其他人(护理人员等)也会参与进来。但接种疫苗的选择将基于预先确定的指南,即标签。我自己注射过疫苗,产品的选择是根据病人的需要量身定做的。所有这些解决方案都已经到位。
人们已经接种了两种版本的带状疱疹疫苗。来自疾控中心(一个你可以信任的消息来源):“你可能已经接种了一种不同的带状疱疹疫苗,名为Zostavax。如果你这样做了,你仍然需要2剂Shingrix。“。
是的,我妻子和我都买了。Shingrix有非常好的佐剂和高水平的抗原。第一次拍摄对我来说还不错。第二个带来了产品标签上的所有副作用,正如它所指出的,第二天所有的副作用都消失了。我们的大多数朋友对第二针也有反应。总比得带状疱疹强。
少数候选疫苗确实使用“载体”(通常是腺病毒)病毒携带Covid抗原密码。使用这些疫苗,您将同时对Covid抗原(可能是Spike或Spike的RBD)和病毒载体产生免疫反应。使用相同病毒载体的第二次接种可能会被你的宿主对媒介的免疫力击败。
我认为,任何COVID疫苗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护最脆弱的人,死亡统计数据将老年人和有某些潜在医疗条件的人确定为主要的高危群体。在流感疫苗的基础上,目前的做法是为每个人接种疫苗,以保护弱势群体。然而,对于儿科疫苗,我们只针对婴儿和幼儿,因为大多数成年人可以对溺爱不成熟免疫系统的传染病不屑一顾。此外,在流感的情况下,链球菌的继发感染构成了最大的死亡风险,我们现在有一种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抗链球菌疫苗。带状疱疹疫苗的开发也是为了照顾老年人。在回答最初的海报时,有很好的证据表明,一个人可以有效地在两种带状疱疹疫苗之间切换。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主张一个更微妙的流感疫苗计划,而不是普遍接种疫苗,因为全民疫苗的使用率令人震惊。无论如何,我认为在COVID的任何3期试验中纳入足够数量的“高危”个体是很重要的,因为我相信我们应该期待这些群体比整体人群更好的遵从性。此外,这是最有可能显示疗效的地方,希望这将鼓励LES autre,因为疫苗变得更容易获得。如果没有强制性的疫苗接种,我无法想象会有太多普通民众撸起袖子想要接种疫苗,即使有效,对接受者的影响也不大。
第一针不太可能不提供至少一些保护。特别是AZ疫苗在第二针后抗体滴度仅增加4倍。
既然我们无畏的领导人提议在选举前(和第三阶段结束)发布AZ的疫苗,我想知道AZ是否会同意。他们会拿自己的声誉冒险吗?他真的能强迫他们在没有他们合作的情况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制作出它(国防生产法案)并分发吗?
今天我们了解到,事实上,中国从7月份开始在临床试验之外一直在接种国药疫苗。
这是他们几个星期来在军队里用的吗?
阿斯利康是在英国注册成立的,因此最终不在特朗普的管辖范围内。也就是说,由于他们在美国卖得很多,如果他们不遵守他的路线,他很可能会让他们感到不愉快。
为什么这位激进的左翼暴徒、投掷炸弹的马克思主义者德里克·罗(Derek Rowe)就康复血浆的批准对我们尊敬的特朗普总统进行了抨击?这位以自我为中心的伪科学专家德里克·罗曾经上过哪所医学院,有什么临床经验,接受过什么医学培训或教育?零!
也许德里克·罗(Derek Rowe)在街上与他深爱的激进自由民主党暴徒一起进行一些骚乱、抢劫和焚烧会更好。罗不应该被信任,因为他显然是一个共产主义煽动者。他甚至扼杀了言论自由,并为自己对特朗普总统的可耻诽谤感到愤怒。罗喜欢辱骂我们伟大的总统,然后他关闭评论,这样就没有人可以因为他扭曲的政治声明而指责他。
罗应该把他愚蠢的政治和医学观点留在他那垃圾科学的布尔什维克头脑里。
如果罗继续散布政治谎言和社会主义宣传,他非法提供医疗建议的行为将不得不受到调查。
也许罗就是那么坏,不过我还是喜欢德里克·洛的博客…的博文内容丰富。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一些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的帖子,但要有更多的押韵。
德里克唯一的专长就是坐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