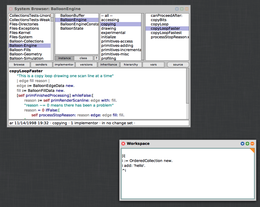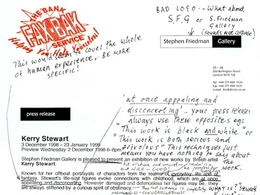T·S·艾略特,“诗歌的艺术”第一卷
采访是在纽约的路易斯·亨利·科恩夫人的公寓里进行的,她是图书公司的路易斯·亨利·科恩夫人,他是艾略特夫妇的朋友。漂亮起居室的书柜里收藏了大量现代作家的作品。靠近入口处的墙上挂着一幅艾略特先生的画像,是他的嫂子亨利·威尔·艾略特夫人画的。一张刻有艾略特夫妇结婚照的银框放在桌子上。科恩夫人和艾略特夫人坐在房间一端的沙发上,艾略特先生和采访者在中间面对面。录音机的麦克风放在他们之间的地板上。
艾略特先生看起来特别好。他在拿骚度假返回伦敦的途中短暂访问了美国。他晒得黝黑,自从面试官见到他后的三年里,他似乎发胖了。总而言之,他看起来更年轻,看起来更快乐了。在采访中,他经常瞥艾略特太太一眼,好像他在和她分享一个他没有回答的问题。
采访者之前曾在伦敦与艾略特先生交谈过。罗素广场(Russell Square)上方几层楼的Faber and Faber的小办公室在墙上陈列着一系列照片:这里有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大照片,还有皮乌斯十二世(Pius XII)的插画;这里有I.A.理查兹(I.A.Richards)、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W·B·叶芝(W.B.Yeats)、歌德(Goethe)、玛丽安·摩尔(Marianne Moore)、查尔斯·惠布利(Charles Whibley。在与艾略特先生的一次谈话中,许多年轻诗人都凝视着那里的面孔。其中一人讲了一个故事,说明了艾略特先生谈话中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经过一个小时严肃的文学讨论后,艾略特先生停下来思考他是否有最后一句忠告:这位年轻的美国诗人即将像艾略特先生40年前那样去牛津大学。然后,艾略特先生严肃地建议购买长羊毛内衣,因为牛津的石头很潮湿,就好像他在建议拯救一样。艾略特先生很清楚风度和信息之间的滑稽不相称,但他却能表现得很慈祥。
类似的组合修改了这里报道的许多评论,手势的讽刺之处在页面上是看不见的。实际上,采访有时会从讽刺的、略带滑稽的转向滑稽的。这盘磁带不时被艾略特的笑声打断,特别是在提到他早年贬低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时候,以及关于他哈佛时代未出版的、收集不当的博洛国王(King Bolo)诗歌的问题时,尤其是在回应他早年对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贬损时。
也许我可以从头说起。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在圣路易斯开始写诗的情况吗?
在菲茨杰拉德的奥马尔·凯亚姆(Omar Khayyam)的启发下,我在14岁的时候开始思考,用同样的风格写了一些非常悲观、无神论和绝望的四行诗,幸运的是,我完全压制了这些诗-如此彻底,以至于它们根本不存在。我从没给任何人看过。第一首诗首先出现在史密斯学院的唱片中,后来出现在“哈佛倡导者”中,这首诗是为我的英语老师写的练习,是对本·琼森的模仿。他认为这对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很有好处。然后我在哈佛写了几篇文章,刚好有资格当选“哈佛倡导者”的编辑,这让我很享受。然后我在大三和大四的时候爆发了。在波德莱尔和朱尔斯·拉福格(Jules Laforgue)的影响下,我变得更加多产,我想我是在哈佛大学大三的时候发现他的。
有没有人特别把你介绍给法国诗人?我想应该不是欧文·巴比特吧。
不,巴比特会是最后一个人!巴比特一直称赞的一首诗是格雷的挽歌。这是一首很好的诗,但我认为这显示了巴比特的某些局限,上帝保佑他。我想我已经为我的消息来源做了广告,这是亚瑟·西蒙斯关于法国诗歌的书*,我是在哈佛联盟中偶然发现的。在那些日子里,哈佛大学联盟是任何选择加入它的本科生的聚会场所。他们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图书馆,就像现在许多哈佛大学的图书馆一样。我喜欢他的语录,我去了波士顿某处的一家外国书店(我忘了名字,不知道它是否还存在),那家书店专门卖法语、德语和其他外国书籍,找到了拉福格和其他诗人。我不能想象为什么那家书店会有像拉福格这样的几位诗人的存货。天晓得他们有多久了,或者有没有其他的需求。
当你还是一名本科生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有哪位年长的诗人占据主导地位?今天,这位年轻的诗人正在艾略特、庞德和史蒂文斯的时代写作。你能记得你自己的文学时代感吗?我想知道你的情况是否有很大的不同。
我认为,在英国或美国没有任何人特别感兴趣的在世诗人,这是一种相当大的优势。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但我认为,如果有这么多你们所说的占主导地位的存在,那将是一种相当麻烦的分心。幸运的是,我们没有被对方打扰。
我略微注意到了罗宾逊,因为我在“大西洋月刊”上读到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其中引用了他的一些诗,这根本不是我喜欢的。在那个时候,哈代几乎不是一个知名的诗人。有人读过他的小说,但他的诗只是真正为后人所熟知。然后是叶芝,但那是早期的叶芝。凯尔特的暮色对我来说太多了。除了死于酗酒或自杀或这样或那样的90年代的人之外,真的什么都没有。
你和康拉德·艾肯在担任“倡导者”主编时,有没有在诗歌方面互相帮助?
我们是朋友,但我认为我们一点也不影响对方。当谈到外国作家时,他对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更感兴趣,而我则完全支持法国作家。
嗯,是的。有一个人是我哥哥的朋友,一个叫托马斯·H·托马斯的人,住在剑桥,他在“哈佛倡导者”上看到了我的一些诗。他给我写了一封非常热情洋溢的信,使我振作起来。我希望我还留着他的信。我非常感谢他给我的鼓励。
我知道是康拉德·艾肯把你和你的工作介绍给庞德的。
是的是这样的。艾肯是个非常慷慨的朋友。有一年夏天,当他和哈罗德·蒙罗(Harold Monro)等人结束工作时,他试图把我的一些诗放在伦敦。没有人会考虑出版它们。他把它们还给我了。然后在1914年,我想,夏天我们都在伦敦。他说,“你去庞德吧。把你的诗给他看。“。他想庞德可能会喜欢它们。艾肯喜欢它们,尽管它们和他的非常不同。
我想我是先去拜访他的。我想我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他肯辛顿的三角形小起居室里。他说,“把你的诗寄给我。”他回复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了。过来聊聊他们吧。“。然后他把他们推到哈丽特·门罗身上,这花了一点时间。
在一篇关于你的辩护律师时代的文章中,为了纪念你的60岁生日,艾肯引用了一封来自英国的早期信件,在信中,你提到庞德的诗句“令人感动地无能”。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改变主意的。
哈!这有点鲁莽,不是吗?庞德的诗句首先是由“哈佛倡导者”的编辑W.G.Tinckom-Fernandez给我看的,他是我和康拉德·艾肯的密友,以及那个时期的其他Signet*诗人。他给我看了埃尔金·马修斯的那些小东西,欢欣鼓舞和个性。*他说,“这是你的拿手好戏,你应该喜欢这个。”嗯,我没有,真的。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相当花哨的、老式的、浪漫的东西,是一种隐蔽和匕首式的东西。我对此印象不是很深。当我去看庞德的时候,我并不是特别欣赏他的作品,虽然我现在认为我当时看到的作品非常有成就,但我确信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会发现伟大的东西。
你在印刷品中提到,庞德把“荒原”从一首大得多的诗剪成了现在的形式。你是否从他对你诗歌的总体批评中受益?他有没有删掉其他的诗?
是。在那个时期,是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批评家,因为他没有试图把你变成他自己的模仿品。他想看看你想做什么。
你有没有帮忙改写过你朋友的诗?比方说埃兹拉·庞德的?
我想不出任何例子。当然,在过去二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对青年诗人的手稿提出了无数的建议。
别问我。这是我不知道的事情之一。这是一个未解之谜。我把它卖给了约翰·奎恩。我还给了他一本未发表的诗集笔记本,因为他在各种事务上对我都很好。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们的消息。然后他死了,他们没有出现在拍卖会上。
庞德从荒原上砍下了什么东西?他是不是整段都剪了?
整个部门,是的。有一段很长的篇幅是关于一次海难的。我不知道这与其他事情有什么关系,但我想,它的灵感相当于“地狱”中的尤利西斯章(Ulysses Canto)。然后还有一个环节,就是仿制的强奸锁。庞德说:“试图去做别人已经做得和能做的一样好的事情是没有用的。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不是的。我认为在更长的版本中,它同样是无结构的,只是在一种更徒劳的方式上。
我有一个关于这首诗的问题,这与它的作文有关。在兰贝斯之后的思考中,你否认了批评家的指控,他们说你在“荒原”中表达了“一代人的幻想破灭”,或者你否认这是你的意图。现在,我相信,F·R·利维斯已经说过,这首诗没有进展;但另一方面,最近的评论家们,在你后来的诗歌之后写作,发现了荒原基督徒。我想知道这是不是你的部分意图。
不,这不是我有意识的意图的一部分。我认为在兰贝斯之后的思考中,我谈论的意图更多的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我说的不是我的意图。我想知道“意图”是什么意思!一个人想把心里话说出来。一个人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直到他发泄出来,他才想说出心里话。但是我不能肯定地把“意图”这个词用在我的任何一首诗上。或者任何一首诗。
我还有一个关于你和庞德以及你们早期职业生涯的问题。我在某处读到过,你和庞德决定在十几岁的时候写四行诗,因为弗尔斯的自由已经走得够远了。
我想这就是庞德说过的话。写绝句诗的建议也是他提出来的。他让我上了Emaux et Camées*。
我想知道你对形式与主题关系的看法。那么,您是否会在完全不知道要在其中写些什么之前就选择了该格式呢?
是的,在某种程度上。一位研究原作。我们研究了戈蒂埃的诗歌,然后我们想,“我有什么要说的吗,这种形式会有什么用处?”我们做了实验。形式推动了内容的发展。
当然,我早期的自由运动是在努力练习与拉福格相同的形式下开始的。这意味着仅仅是长度不规则的押韵行,押韵出现在不规则的地方。它没有那么自由,特别是以斯拉称之为“艾米格主义”的那种。,当然,下一阶段也有更自由的东西,比如“风夜狂想曲”(Rhapsody On A Windy Night)。我不知道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脑海中是否有任何类型的模式或实践。它就是朝那个方向来的。
你有没有可能觉得,你是在写一些东西,而不是任何模型?或许是对桂冠诗人的攻击?
不,不。我不认为一个人总是试图拒绝一些东西,而只是试图找出什么是适合自己的。有一位真正被忽视的桂冠诗人,罗伯特·布里奇斯(Robert Bridges)。我不认为好的诗歌可以在一种推翻现有形式的政治尝试中产生。我想它只是取代了。人们总能找到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不能这样说,我怎么才能找到这样做的办法呢?”没有人真的为现有的模式操心。
我想你是在“普鲁弗洛克”之后、“杰罗尼”之前用法语写诗的,这些诗出现在你的诗集里。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写出来的。从那以后你写过信吗?
不,我永远也不会。那是一件我无法完全解释的非常奇怪的事情。那段时间我以为我已经完全枯竭了。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写任何东西了,非常绝望。我开始用法语写一些东西,在那个时期,我发现我可以。我想是因为当我用法语写诗的时候,我没有那么认真地对待这些诗,也就是,没有认真对待它们,我并不是那么担心不会写诗。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看看我能做些什么。这件事持续了几个月。其中最好的已经印出来了。我必须说,埃兹拉·庞德经历了这些事件,我们在伦敦认识的法国人埃德蒙·杜拉克(Edmond Dulac)帮了他们一些忙。我们漏掉了一些,我想它们完全消失了。然后我突然又开始用英语写作,完全失去了用法语写作的欲望。我想这只是一些帮助我重新开始的东西。
你有没有想过成为一名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就像上个世纪的两位美国人一样?
斯图尔特·梅里尔和维埃莱·格里芬。我只是在哈佛毕业后在巴黎度过的浪漫一年里才这么做的。当时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放弃英语,设法在巴黎安顿下来,勉强度日,然后逐渐写法语。但是,即使我比以前更会说两种语言,这也是一个愚蠢的想法,因为首先,我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成为一名双语诗人。我不知道有哪种情况下一个人用两种语言写出了同样出色的伟大甚至优秀的诗歌。我认为一种语言必须是你用来表达自己的语言,在诗歌中,为了这个目的,你必须放弃另一种语言。我认为英语在某些方面确实比法语有更多的资源。我想,换句话说,即使我的法语和你提到的诗人一样精通,我的英语可能比我在法语方面做得更好。
不,我目前没有任何计划,除了我想我想,在刚刚摆脱了“元老政治家”之后(我只是在离开伦敦前通过了最后的校样),想写一篇批判性的小散文。我从来不会超前一步思考。我是想再演一出戏,还是想写更多的诗?我不知道,直到我发现我想做这件事。
我在那方面没什么,没有。一般来说,对我来说,一件未完成的事情就是一件可以擦掉的事情。如果里面有什么好东西,我可以在别处用到,那就把它留在我的脑海里,而不是放在抽屉里的纸上。如果我把它放在抽屉里,它仍然是一样的东西,但如果它在内存中,它就会变成另一个东西。正如我以前说过的,烧焦的诺顿从大教堂谋杀案中不得不剪掉的碎片开始。我在“大教堂里的谋杀案”中了解到,如果你认为是好诗的优美台词完全没有动作,那就没有用了。那是马丁·布朗派上用场的时候。他会说,“这里有非常漂亮的台词,但它们与舞台上正在上演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
你的一些小诗实际上是从长篇作品中剪下来的吗?有两个听起来像“空心人”
哦,那些是初步草图。那是早些时候的事了。其他的我在期刊上发表,但没有在我的诗集中发表。你不会想在一本书里把同一件事说两次。
你似乎经常把诗分成几段来写。它们是从单独的诗开始的吗?我特别想到了“灰烬星期三”。
是的,就像“空心人”一样,它起源于不同的诗歌。我记得,“灰烬星期三”的一、两个部分的初稿出现在“商业”和其他地方。然后渐渐地我开始把它看作是一个序列。这是我的头脑多年来似乎确实以一种诗意的方式运作的一种方式-分开做事情,然后看到将它们融合在一起,改变它们,并使它们成为一种整体的可能性。
你现在有没有像“老负鼠实用猫书”或“波洛王”那样写东西?
这些东西确实时不时会来!我对这样的诗句做了一些笔记,其中有一两只残缺不全的猫可能永远也写不出来。有一个是关于一只迷人的猫的。结果太悲哀了。这绝对不会行得通的。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为一只出了问题的猫哭泣。她的职业生涯很可疑,做了这只猫。这对我上一卷“猫”的观众来说是行不通的。我从来没摸过狗。当然,总体而言,狗似乎不像猫那样适合写诗。我可能最终会做我的猫的放大版。这比另一卷书更有可能。我确实加了一首诗,这首诗最初是为费伯和费伯做的广告。它似乎相当成功。哦,是的,你知道,在每一种类型的诗中,严肃、轻浮、恰当和不恰当,人们都想保持自己的手。一个人不想失去自己的技能。
现在在写作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兴趣。我想知道你是否可以多谈谈你写诗的实际习惯。我听过你在打字机上作曲。
一部分在打字机上。我的新剧“元老政治家”有很大一部分是粗略地用铅笔和纸写成的。然后,在我妻子开始工作之前,我先自己打了出来。在我自己打字的时候,我会做一些改动,非常可观的改动。但是,无论我是写作还是打字,任何长度的作品,比如一出戏,对我来说都意味着固定的工作时间,比方说十比一。我发现一天三个小时差不多是我能做的实际作曲的全部。我可以晚点再打磨。我有时一开始会发现我想再坚持下去,但第二天当我看着这些东西时,我在三个小时后所做的事情从来都不能令人满意。最好还是停下来想想其他完全不同的事情。
你有没有按计划写过一些平淡无奇的诗?也许是四个四重奏?
只是“偶尔”的诗句。四重奏没有按计划进行。当然,第一本是在35年写的,但是在战争期间写的三本书更是断断续续。在1939年,如果没有战争,我可能会试着写另一个剧本。我认为我没有这个机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在我个人看来,战争所做的一件好事就是阻止我过早地写下另一个剧本。我看到了“家庭团聚”的一些错误之处,但我认为,任何可能的戏剧都被封杀五年左右,才能振作起来,这要好得多。四重奏的形式非常适合我写作的条件,或者说完全可以写作。我可以分段写作,我不必保持完全相同的连续性;当我在做战争工作时,即使有一两天没有写作,就像他们经常做的那样,这都无关紧要。
我们一直在提及你的剧本,却没有提及它们。在“诗歌与戏剧”中,你谈到了你的第一个剧本。我想知道你是否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你对“元老政治家”的意图。
我想,我在诗歌和戏剧中说了一些关于我的理想目标的话,我从来没有指望能完全实现。我真的是从家庭团聚开始的,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