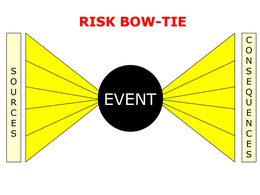风险的三个方面
我从小在太浩湖滑雪比赛长大。我是斯阔谷滑雪队的成员,十多年来,它一直是我生活的中心。在几个月前的一次会议上,有人问我滑雪在投资方面教会了我什么。这是在舞台上,你不能思考你的答案-你必须脱口而出你能想到的任何东西。我不认为滑雪能教会我任何关于投资的知识。但有一件事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好吧,让我把这件事带到一个黑暗而悲惨的地方,”我在给一群500名陌生人讲述一个我近20年来很少谈论的故事之前说。我们十几个人从小一起滑雪长大。大多数人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到了2001年,我们都快十几岁了,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醒着的大部分时间从未远离过对方。我们一周滑雪6天,每年10个月,在山上的冰川上度过夏天。俄勒冈州的胡德和新西兰,那里的季节反映了我们的季节。滑雪是第一位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参加了独立学习项目,这让我们绕过了传统的高中。滑雪了一整天之后,我们在晚上读了几本书,填了几张表,令我们惊讶的是,这让我们拿到了文凭。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使我们的关系更亲近于兄弟姐妹,而不是朋友。滑雪比赛是团队和个人运动的奇怪混合体。你们作为一个团队训练、旅行和吃饭,但这项运动本身是个人的。我们的比赛结果不是相互依赖的;我们每天的理智是相互依赖的。任何十几个青少年组成的团体都会找到一种方法来迎头相撞。我想我们有一半的时间都恨对方。20年后,我们中几乎没有人保持联系。但是,到2001年,在十几个与我共度大半生的青少年中,我们中有四个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这是他们中的两个人--布兰登·艾伦和布莱恩·里士满的故事。当奇妙的事情变成例行公事时,你会认为它们是理所当然的。斯阔谷是北美最大的滑雪场之一,是1960年奥运会的举办地,每年吸引100万游客。它美得令人吃惊。对我们来说,这只是家的延伸。滑雪比赛每天需要四个小时的训练,这对我们来说就像是工作。剩下的时间-每天另外四个小时,一周六天-我们只是四处滑雪,没有条理,玩得很开心。我们称之为“免费滑雪”。其他人都管它叫滑雪。2001年2月15日,我们刚从科罗拉多州的一场比赛回来。我们回家的航班延误了,因为太浩湖被暴风雪袭击了,即使按照它自己的标准也很凶猛。当有一层新的雪地需要坚硬的冰时,你就不能参加比赛或训练。所以现在是免费滑雪一周的时候了。当月早些时候,塔霍收到了几英尺厚的轻盈蓬松的雪,这些雪来自北极的温度。2月中旬袭击的风暴是不同的。天气很暖和-几乎不到冰点-而且威力很大,在它之前到来的轻质粉末上留下了三英尺厚的湿重的积雪。我们当时没有想过这一点--我们在17岁的时候没有想过太多--但是大雪加上蓬松的雪创造了教科书上完美的雪崩条件。想象一下,上面有一层厚厚的沙子,上面有一层厚重的水泥。现在想象一下把这些层放在陡峭的山上。它很易碎,很容易滑下来。这就是2001年2月下旬斯阔谷的情况。滑雪场善于管理这些条件,以确保人们的安全。很少有游客意识到这一点,但如果你在暴风雪过后的清晨参观滑雪胜地,你会听到像炸弹爆炸的声音。这声音没有欺骗性。在迫击炮、手榴弹和从直升机上投下的炸药的组合下,滑雪巡逻队控制着危险球场的爆炸,在度假村空无一人时故意触发雪崩,在客人到达之前先发制人(查看一些视频)。这是一个有效的系统,使主要度假村的雪崩事故变得罕见。但是,如果你在越界滑雪--躲在“请勿穿越绳索”下滑雪,在没有被湾区游客触碰的禁地滑雪--系统就帮不了你了。越界滑雪是非法的,是非法侵入的一种形式。度假村不想让你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太危险了。越界区域没有巡逻,所以如果你受伤了,你要靠自己。它们通常不会通向缆车,所以你必须自己想办法再上去。它们不是为了控制雪崩而轰炸的。因此,滑雪者最有可能在这里--超出界限--发现大自然母亲滑动的愤怒。2001年2月21日上午,布兰登、布莱恩和我像以前一样,在斯阔谷滑雪队更衣室会面。几年后,布莱恩的妈妈告诉我,那天早上他离开家时的最后一句话是,“别担心,妈妈,我不会滑雪越界的。”但是我们一打开滑雪板,我们三个就这么做了。斯阔谷的背面,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