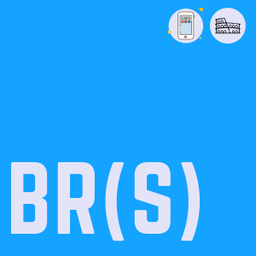语言是提高我们思维质量的技术
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的书“技术寡头”(Technopoly,1992)第一次让我意识到语言是一种组织和交流思想的技术。
马歇尔·麦克卢汉意识到,我们塑造了我们的技术,我们的技术也重塑了我们。也就是说,语言技术不仅帮助我们将思想外化,而且还改变了我们将感知内化的方式。因此,语言的目的不仅仅是信息的交流。它是一种提高我们思维质量的技术。
作为一种技术,语言提供了负担(即,使某些事情变得更容易),并施加了约束(即,使某些事情变得不可能)。
例如,一旦我们习惯了用文字思考,我们就会(下意识地)更容易去思考那些我们有文字的事情,而很难去想我们没有文字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英语不断增加新词--让我们更容易想到“朋友”、“网络星期一”或“众筹”。“。
在宽带互联网接入普及之前,这些话都没有任何意义。每个新词的发明都是为了传达一种体验,这种体验比可以简化为一个单词或短语的体验要复杂得多。但是,一旦这个新词想要代表的体验变得普遍起来,这个词就会成为共享体验的占位符。
有了这个新词会改变我们对体验的理解方式,以及我们对它的看法。
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发明新词来改变我们的语言,但是语言的改变也改变了我们的大脑。我们语言的体系结构是一种强大的方式,既能赋能我们的思想,又能引导我们的思想。同样,铁路技术是加快重型货物运输的有力手段,但只能到达铺设铁轨的目的地。任何语言的局限性都体现在新词的必要性上--即我们思想的新归宿。
语言比词汇更强大。重要的不仅仅是单词和它们所代表的经验,还有语言的结构方式、标点符号、多义性(或非多义性)以及语法和拼写规则。
因为语言是一种提高思维质量的技术,所以语言的结构会影响思维的结构。例如,数学和计算机编程也是“语言”。它们不是口头的,但它们有自己的符号、句法、语法和交际能力。
就像口语一样,数学和计算机编程具有引导思想的能力,不仅是通过符号,而且还通过控制这些符号、命令和运算符如何联系在一起的规则。就像Python是人工智能的语言之一一样,英语也是人类智能的语言之一。
一旦一种语言的规则和规范建立起来,与该语言相一致的文化期望也就建立起来了。例如,在日语和德语中,拼写和发音规则是标准化的,并且可以根据一致的语法进行解读。尽管德国人以创造连续不断的句子(以动词结尾)和长复合词而臭名昭著,但主导解码这些又长又复杂的句子和单词的机制是可靠的和始终如一的。
德国人和日本人造的车比法国人好,这有什么奇怪的吗?在语言复杂但可靠的地方,思维也是如此,制成品也是如此。
在某种程度上,洞穴壁画就像原始的互联网--智人在文明前的“博客”。只不过,我们的远古祖先没有画色情画,而是留下了指导手册,教他们的同龄人如何狩猎。詹姆斯·格莱克(James Gleik)在非洲会说话的鼓中发现了一个非语言技术/语言的最新例子(“信息”,2012年)。关键是“语言”比那些有字母的“语言”要多得多,而且它们都不仅仅是交流知识和信息。
一旦你明白语言会改变你的思维质量,你就理应改进你的语言,这样你就可以提高你的思维。
当父母告诉他们的孩子,“不要忘了你的家庭作业!”孩子听到的是“…”忘了你的作业吧!“。
人类大脑需要额外的认知努力才能识别句子中否定的“not”。大脑甚至需要更多的努力,才能用一些关于他们应该做什么的不言而喻的建议来取代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和一个有这个习惯的女人约会,她过得很糟糕。当她努力定义我们的关系和她在其中的角色时,她经常求助于说她不想说的话。例如,我记得我们在飞机上坐在一起,往返于某个外国城市时的这段对话。
我:“我们降落时你能帮我查一下吗?”她:“我不是你的秘书!”我:“好的,我明白了。下次我要去国际商务旅行,我会请一位秘书而不是你。
问题是,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只知道她不是什么。果不其然,当我有机会去中国领导一个关于可持续发展知识重组的研讨会时,我邀请了另一位女性,她更了解她是谁,以及她为什么会在那里。
当她在研讨会上被问到“你是做什么的?”我的新国际约会对象说,“我和汤姆一起来的。”
她没有用她没有做的事情来掩盖这个问题。她明白自己是什么。
当时间到了,她很高兴去北京的星巴克,把八份不同的咖啡订单都弄对了-尽管她一个字也不会用中文交流。(原来,他们也不懂英语。但不管怎样,整个车间的桌子都拿到了他们想要的咖啡,因为这位新来的女人性格开朗,足智多谋。
我的新旅行对象也不是秘书。不同的是,她愿意接受基于她所做的事情建立更紧密关系的邀请,而不是基于她不做的事情而接受更疏远的关系。
我和“不是”女人的关系,尽管有一些可怕的化学反应,也没能从负面情绪中幸存下来。
许多人会使用像“if”这样的逻辑操作数作为最后通牒,而不是偶然可能性。例如,他们可能会说,“如果你对这件事要表现得很差劲,那么我就拿着球回家!”
这样做的问题是大脑不理解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区别。一旦你说了一句像“…”这样的话。你会是个混蛋,然后我就拿着球回家,“你的大脑已经把”if…“忘得一干二净了。”句子开头的部分。因此,真正应该是关于未来的问题变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第一个是取代“if…”带有“When…”的语句。“就像在说,”当你不高兴的时候,我会带着我的球回家。“。
“何时”更像是承诺,而不是最后通牒。它避免了错误的非此即彼的困境。
“When…”是一种承诺,而“if…”是一种操纵。
也许“When…”吧。对你不会像对我一样管用。无论哪种方式,都有第二种更有效的方法来克服“if…。“扭曲。
在计算机编程中,经典的逻辑偶然性是“if…。然后是…。否则…。.“。Else很关键,因为它告诉计算机在“if…”时要做什么。“条件为假。
在普通的英语会话中,加上“Else”听起来有点别扭,但加上“…”或…“。声明听起来更好,打破了最后通牒变成自我实现预言的陷阱。
例如。更有建设性的是,把IF的最后通牒改写为:“如果你要对这件事表现得很混蛋,那么我就拿着球回家--或者我们都可以按规则玩,一起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看看以“or”后面的短语结尾是一个更积极、更有创意的建议,可能会导致更亲密、更有趣的关系吗?
它经常出现在谈话中。有人会说,“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做这项工作。”
感觉是高兴、疯狂、悲伤和害怕的东西。我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我读了吉姆·麦卡锡(Jim McCarthy)的“面向你的头脑的软件”(2002)。麦卡锡在微软与工程师共事多年,他意识到许多程序员与他们的情绪脱节,以至于他发明了像“高兴、疯狂、悲伤、恐惧”这样的多项选择反应协议,以帮助他们识别和描述自己的情绪状态。
这么多人学会用“感觉”这个词来描述想法的原因是他们想要避免批评。
只有像我这样的混蛋才会跟你的感觉争辩,对吧?我是说,没人能告诉你什么感觉,不是吗?
所以,如果你觉得承包商上周应该修好你的屋顶,…。那么,谁有资格批评你呢?仅仅因为你对屋顶一无所知并不意味着你没有权利表达你的感受,对吗?
当你把一个想法说成是一种感觉时,你是在告诉自己,你的想法不可能是错的,你把自己关在了另一种观点之外。
另一方面,表达真实的感觉(如悲伤或恐惧)会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变得脆弱。我们小时候都有过因为合法的情感表达而受到羞辱的经历,我们明白我们的情感可以被用来操纵或剥削我们。将想法错误地贴上感觉标签的第二个好处是,它帮助我们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它让别人看不到我们的情绪状态,所以我们可以避免羞愧和操纵的风险。
了解思想和感觉的区别,并有勇气正确使用这两个词。
你最后一次遇到一位熟人是什么时候,他以这样的话结束了谈话:“哦,耶!我们真的应该聚在一起喝杯咖啡!“。
注意到上一节的最后一句话了吗?(上面写着:“…。要有勇气正确使用这两个词。“)。
但问题并不在于结束句子的副词。是中间的副词。
今天我和两个朋友有过一次经历,他们试着从公寓的冰浴开车去两英里外的热瑜伽课。我们试图驾驭道路封闭和迂回,这是每年这个时候蜿蜒穿过我的城市的半程马拉松比赛的结果-我们做得很糟糕。
我的一位乘客给瑜伽馆打了电话,问如果我们迟到了,是否还可以参加。她说,“因为我们正好10分钟后就到了!”
副词后面的每一句话都没有可信度,因为当我们相信我们所说的话时,我们不需要副词的虚假虚张声势来加强我们的虚张声势。
当你发现自己在句子中插入副词时,试着改变措辞,去掉副词,看看你是否仍然想说你想说的话。如果你和你想说的话之间没有副词缓冲,你很可能会感到不舒服。
副词是一种表达你希望是真的东西的方式,同时向你的听者发出信号,你们都知道那不是真的。
“很难做出预测,特别是对未来。”--约吉·贝拉(Yogi Berra)。
当我们使用预测的语言时,比如“他不可能去做那件事!”我们不由自主地对结果变得自负起来。做出预测意味着,无论我们所说的是对是错,我们都有情感上的利害关系,如果现实与我们的预测不符,我们的声誉可能会受到损害。
预测需要我们在事实之后对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合理化:1)我们是多么聪明,因为我们是对的(例如,“我早告诉过你了!”),或者2)我们错了并不是我们的错(注意副词)。
用可能性语言重新表述你的预测语言。与其说“…。Will…“。问“如果…。?“。
通过探索“What If…”的可能性。?“。语言,你避免了自我投资陷阱,停留在创造性的解决问题和学习的模式中。额外的好处是,你为成功准备了多条道路,并且可以适应那些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