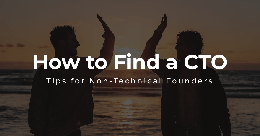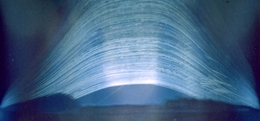说服技术是否应受到限制?
说服力与我们的物种一样古老。民主和市场经济都依赖它。政治家说服公民投票或支持不同的政策立场。企业说服消费者购买他们的产品或服务。我们都说服我们的朋友接受我们对餐厅,电影等的选择。对社会至关重要没有它,我们就无法让一大群人一起工作。但是,就像许多事情一样,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说服的性质。社会需要调整其说服规则或承受后果。
尤其是民主社会,急切需要就说服在他们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技术如何使强大的利益针对目标受众进行坦率的讨论。在公众舆论是统治力量的社会中,总是有动员公众舆论是出于不良目的的风险,例如挑起恐惧以鼓励一个群体讨厌另一个人以赢得职位,或针对个人弱点来推销那些可能不会使消费者受益。
关于说服一直存在规则。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U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执行法律,声称对产品“必须真实,无误导,并在适当情况下以科学证据为后盾”。政治广告商必须在电视广告中标识自己。如果某人滥用职权强迫另一人订立合同,则可以争辩说有不当影响力使该协议无效。然而,说服力比真相,透明度或施加压力要多。
说服还涉及心理学,而且很难进行调节。用心理学说服人们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爱德华·伯奈斯(Edward Bernays)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公共关系先驱和侄子,他进行了吸引自我的营销实践。他的方法是将消费与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联系起来。 Bernays在其1928年的《宣传》一书中倡导了工程活动,以说服目标受众。在一项著名的特技表演中,他雇用妇女在参加1929年纽约市复活节星期日游行时抽烟,在将吸烟与妇女解放联系起来的同时引发了丑闻。烟草业将继续向销售1960年代的卷烟销售生活方式。
长期以来,情感诉求一直是政治运动的一个方面。在186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南方政客和报纸编辑散播着对“黑人共和党”获胜意味着什么的恐惧,描绘了奴隶的解放会对国家造成什么样的可怕后果。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现代共和党人在西班牙语电台的广告和社交媒体上的消息中使用了古巴裔美国人对社会主义的恐惧。由于涉及到的情绪,许多选民相信竞选活动足以使他们影响自己的决定。
互联网使说服的新技术走得更远。那些希望影响他人的人可以收集和使用有关目标受众的数据来创建个性化消息。通过说服技术,追踪技术可以跟踪那些人访问的网站,他们在网络上进行的搜索以及他们与社交媒体互动的内容,从而使那些可以使用此类工具的人们更好地了解受众,并在受众最有可能看到的地方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消息。该信息可以与有关其他活动的数据(例如,离线购物习惯,某人访问的地方以及他们所购买的保险)相结合,以创建有关它们的个人资料,该个人资料可用于开发有说服力的消息传递,从而激发特定的响应。
同时,我们与技术的互动越来越影响我们的自我意识。我们在与亲密者阅读,搜索和交谈的同一个数字环境中,营销人员可以获取这些数据并将其重新提供给我们。如今,Bernays不再需要发掘可能激发您或吸引您的社会原因,您可能已经通过在线行为分享了这一点。
一些营销人员认为,星期一女性的吸引力降低了,尤其是早晨的第一件事-因此,这是向她们做化妆品的最佳时机。 《纽约时报》曾经尝试通过根据文章内容预测读者的情绪来更好地定位广告,从而使营销人员在悲伤或恐惧时能够找到受众。一些音乐流媒体平台鼓励用户公开其当前的情绪,这有助于广告商根据其情绪状态来定位订户。
我们口袋里的电话为营销人员实时提供了我们的位置,从而帮助他们在地理位置上相关的广告,例如向参加政治集会的人进行宣传。这种始终在线的数字体验使营销人员能够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以及何时,何地以及那时我们可能会感觉如何。
所有这些都不旨在成为危言耸听的人。重要的是不要夸大说服技术的有效性。但是,尽管其中许多烟雾比现实更多,但它们可能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善。该技术已经存在,可以帮助预测某些目标受众的情绪,在任何给定时间精确定位他们的位置,并提供相当量身定制的及时消息。该能力需要走多远,才能削弱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决策者的自主权?
目前,在说服方面几乎没有法律或道德上的限制,也没有关于这种技术有效性的答案。在为时已晚之前,世界需要考虑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极限。
例如,人们早就知道人们更喜欢与像他们这样的人一起制作的广告:种族,种族,年龄,性别。长期以来,已经对广告进行了修改,以适应出现的电视节目或杂志的总体受众特征。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远。存在一种技术,可以拍摄您的头像并将其人口统计学上与您相似的脸部进行变形。结果是一张看起来像您的面孔,但是您无法识别。如果那比粗略的人口统计目标更具说服力,那可以吗?
另一个例子:如果广告商制作故意操纵您情绪的广告怎么办,而不仅仅是在发现您脆弱时向您做广告?在某些方面,能够在可能引起某种情感反应的内容旁边放置广告,这已经使广告商能够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区别是媒体宣称它不是在设计内容以故意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可以主动地向目标受众发起宣传,然后传递适合自己心情的有说服力的消息,这是否可以接受?
此外,基于情感的决策并不是应该为重要的公民选择(例如投票)提供信息的缓慢思考的理性类型。实际上,情感思考有可能破坏该系统的正当性,因为选民本质上被激发朝着有权力和金钱的人想要的任何方向前进。考虑到数字技术的普遍性,人们经常对它们做出反应,那么在说服性技术中应该允许多少情感?是否有不应该跨越的线?
最后,对于当今大多数人来说,信息和技术的普及是无处不在的。美国成年人平均每天花费超过11个小时与媒体互动。如此高的参与度会导致生成并汇总有关您的大量个人数据,即您的偏好,兴趣和心态。控制说服技术的人对我们越了解,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感觉如何,何时感觉到我们以及我们在哪里,他们越能定制促使我们采取行动的信息。毫无戒心的目标处于严重不利地位。可以通过相同的服务来调解我们的数字体验并以我们为目标吗?是否有太多针对性的问题?
具有说服力的技术的力量动力正在发生变化。获得说服的工具和技术不是平等主义的。许多人需要大量的个人数据和计算能力,从而将现代的说服力变成军备竞赛,在军备竞赛中,更好的资源将可以更好地影响受众。
同时,普通人对这些说服技术的工作原理知之甚少,因此不太可能理解他们的信念和观点是如何被他们操纵的。更重要的是,没有什么规则可以保护人们免受说服技术的滥用,更不用说清楚是什么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操纵,以至于它能有效地使代理机构脱离目标人群。这会形成一个积极的反馈循环,对社会很危险。
在1970年代,人们普遍对所谓的“潜意识内的信息传递”感到恐惧,这些信息声称性和死亡的图像隐藏在印刷广告的细节中,例如香烟广告中的烟卷和酒类广告中的冰块。这几乎是个骗局,但这并没有阻止联邦贸易委员会和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这是一种非法的说服技术。这就是担心人们在未经其知情和同意的情况下被人为操纵的原因。
现在是时候就限制说服技术进行认真的讨论了。这必须首先阐明允许的内容和不允许的内容。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强大的说服者将变得更加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