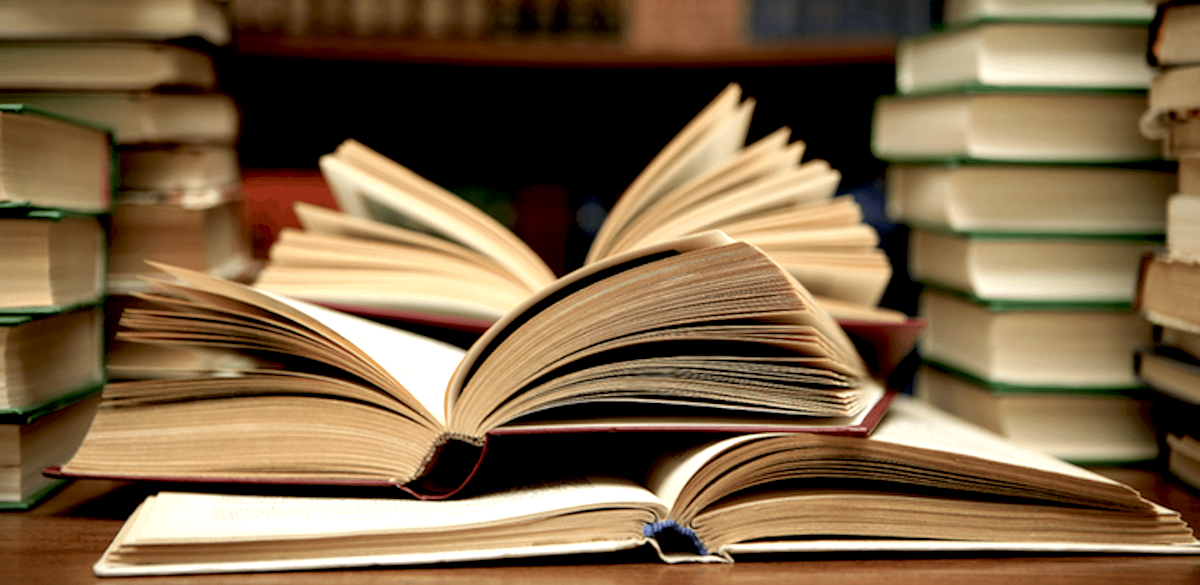我们应该如何阅读?
Warning: Can only detect less than 5000 characters
但是,仅仅能够解密文本并不能真正意义上的全部阅读—除了阅读所谓的“翻页器”之外,它还可以教您如何翻页。的确,从要求不高的作品中吸引您的是一种乐趣,他们沿着他们的路线奔忙,以微不足道的分辨率诱使您继续获得同样的picayune难题。 Bu让我们面对现实:读一本Dan Brown小说是文学,就像演奏Kandy Krush则是先进的战略思维。虽然“乐于读书”可能包含多种文本,但鉴于一个人的身分是另一个人,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作为问题的答案,我们应该怎么读? “享乐”比享乐主义在我们必须称之为现实世界中所需要的享乐要多。
这又使我回到了一个杂乱无章的变化,这种杂乱是出于忠实而不是失职而生的;保真度不是给定的作品或其作者,而是保真度极高的文本,经过精心加工,研究,交织和编织,构成了完整的文学作品。混杂阅读是理解一件作品的爱抚,而在另一本书的怀抱中—混杂的读者则是优秀的教育家。我们应该如何阅读?当美食家吃东西时,我们会读下去,吞噬掉巨大的文字杯。没有人告诉我不要从娃娃谷突然转向卡拉马佐夫兄弟,所以我做到了。不仅如此,他们还警告我不要将范妮·希尔(Fanny Hill)的段落与弗朗兹·范农(Frantz Fanon)所写的段落混在一起-因此,我也这样做了。通过不加选择地阅读,我学会了辨别,也学会了理解:因为只有获取大数据集,我们才能开发出足以解释新材料的模式。
我们应该如何阅读?我们应该读到不要指望理解所有读到的内容:如果遇到不理解的指示符,或者无法明确辨别指示符,则应该继续阅读,并确保上下文可以提供答案,否则作者将在另一个单词中再次使用相同的单词。就个人语素而言,对巨著也是如此:理解,参与和享受都取决于一种能力,不仅可以使人难以置信,而且还可以使人理解,从而使自己成为最甜蜜的奢侈,有疑问的。
数字阅读带来的众多问题之一是其驱动力使所有文本都像在其上显示的屏幕一样透明:手指触摸并出现定义-轻扫一下,然后我们会得到注释,光泽和表现出惊人的丰富性。然而,当我回想起来时,我始终以最消极的能力找到了最深的参与:与抵制字典或百科全书的努力相比,我通过抵制努力学习了更多的东西,因为我继续学习如何做到这一点阅读。
为了重现我能够达到如此文学水平的环境,当代读者将不得不退缩到没有任何互联网连接的目的地,并且必须足够远地复制孩子对世俗问题的遥远见解。然后就是ennui了,我们无聊地提出了发明,除了阅读以外,没有什么比阅读更有创造力了。如果我们的文化因其无情的商品化而无法忍受的一件事,那就是即使是一小部分的乏味也应保持不受干扰或不货币化。
我相信,正是我在父母的书中进行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浏览,使我一上大学就能够吸收教授设定的大部分惩罚性阅读清单,每篇论文通常为十卷或同等水平;而且我们每个学期每周都要读两篇论文。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精英教育:但是,它的精英主义主要在于布罗卡和韦尼克地区三年的锻炼:大脑中最参与文本解密的那些部分。
我把这些抽动和过度活跃的神经元带入了一种懒惰的生活中-我曾经开玩笑说我二十来岁的时间都躺在床上看小说,而且正如弗洛伊德如此出色地观察到的那样,没有笑话之类的东西。我不希望此结论归结为某种针对基于屏幕的阅读的dia病-这样做,似乎有点,嗯,很丰富,因为您,亲爱的读者,很可能现在就这样做。但是我不知道这种状况是否代表一个像MRI机器中的阅读器一样无穷无尽的能力,即关于MRI机器中的阅读器的阅读能力。这就是说,就像数字阅读器的眼睛在屏幕上滑动得太快一样,然后在另一个屏幕上(可能是一个显示图像而不是文字),因此模拟对象的扫视被木板和装订夹住了。
这是与所有滥交行为相对应的纯洁的排斥:保持单一文本的信念,直到最后将其强化,无论朗格或那些紫色的段落,对读者而言,它似乎都是不忠实的。当然,在当今时代或多或少可以立即获得整个世界文学的时代,这种固定性可能很难实现,即使不是不可能。
当我们的文化在1990年代后期达到“高峰纸”的时候,我的床头柜吹嘘着我正在同时阅读的一堆摇摇欲坠的书。二十年来,只有一个电子阅读器,里面可能装载着我同时进行的多达70篇文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仍然有时间(并且拥有狡猾的头脑)秘密进行特别诱人的作品集会。而且我仍然坚决支持这样一种观念,即在文本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之间的摇摆中,我们发现了我们对阅读的真正热爱和参与。
但是新的阅读技术对我们的阅读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我们的阅读方式一样重要。我希望在我的下一篇关于Lit Hub的文章中谈及这个话题,他坚信通过探讨有争议的问题关于规范,我们将对实践有更多的了解。
这是威尔·塞尔弗(Will Self)撰写的有关如何阅读以及为什么阅读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