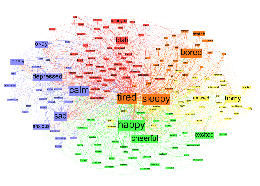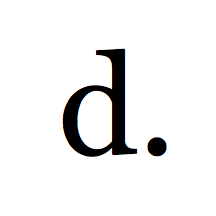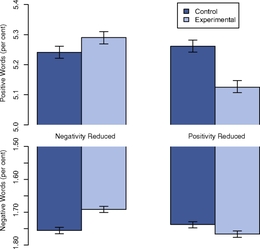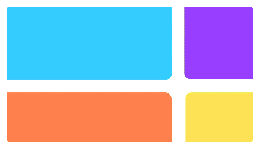情绪管理
这是Agnes Callard撰写的一系列有关公共哲学的专栏文章的一部分;在这里阅读更多
种族主义并不会让我生气。您可能会认为这是因为我不属于边缘化种族,但性别歧视也不会使我生气。尽管事实上他们似乎激怒了我许多人,但我也没有对精英主义或滥用职权感到愤怒。我坚决以大屠杀为中心的童年未能使我对纳粹或反犹太主义者产生敌意情绪。
但是,我不会形容自己拥有和平的气质。我可能会对别人认为琐碎的事情感到生气,并且很容易看到别人深刻理解了背叛,而别人却看到了简单的误解。在公开演讲的语境中,我对修辞胁迫非常敏感,能够尝试使用武力,甚至会遇到好意的一般性建议。
当您的怒气无法与他人的怒气融为一体时(当它拒绝邀请时浮出水面,并且尽管没有公司陪伴也持续存在),您经常会发现自己处于愤怒管理尝试的接受端。有时,可以通过引入新信息或纠正误解来解决这些对话,但是当这些策略失败时,它们通常会演变成纯粹的情感拔河,在其中您会听到自己的愤怒无济于事。现在该继续前进了;最终我们在同一个团队中。或者,也可以说是“愤怒管理”,尽管它通常不被称为“愤怒管理”,但您会听到,如果您不生气,就不会引起注意。除非您与我们在一起,否则您将反对我们。
这些演讲都不会顺利进行-至少我不能接受。
该隐谋杀了他的兄弟后,就亚伯的下落向上帝撒谎-“我不知道。我是我兄弟的监护人吗?” —上帝在该隐爆炸:“你做了什么?听!你弟弟的血从地上向我哭泣。”上帝能听到亚伯的血在哭泣,但该隐却听不到。上帝的愤怒代替了该隐对他兄弟的爱应该成为的空洞:如果该隐无法完全掌握谋杀他兄弟的错误,那么就必须有人。这个故事以惊人的经济性清楚地表明,既有真实的,客观的道德事实,而且甚至对于上帝来说,访问这些事实都是出于愤怒。愤怒是一种道德感。
在人类中,有时只有愤怒的人才能理解某些不公正的程度。因为他们愿意牺牲自己所有的其他关切和利益,以便几乎以神圣的注意力参加道德组织的撕裂。当我真的很生气时,我什至不知道我可以让自己平静下来-心脏的眼睛没有眼皮-提出要求的人向我袭来,以适应苏格拉底的诉求,试图消除我从我的财产,事实。他们称我为“非理性”,但似乎没有看到有生气的理由。
另一方面,也有不这样做的原因。亚里斯多德说,愤怒是报仇的愿望,他是对的,尽管愤怒的人倾向于用别的名字来称呼它。愤怒促使人们对报复行为施加崇高的标签(“正义”,“责任”);在雾中,坏事看起来很好,只是因为别人先做了坏事。例如,考虑一下当认为目标不公正时,那些会以其他方式认为明显嘲笑他人的外表显然不道德的人经常会这样做的人。
愤怒还使人们以一种高尚的眼光看待不公正的受害者,仿佛被冤moral在道德上使一个人得到了改善,而不是通过围绕道德伤害重新组织精神来扭曲他们的心理。甚至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对这种痛苦保持警惕,并抵制了我的家人和老师作为我的犹太遗产所呈现出的反犹太主义的吸引力。大多数本来会是我亲戚的人被纳粹杀害了,所以我很难说这是不合理的,那些幸存者一直说“永远不会忘记”;但是,我拒绝永远记住。
抵制两种形式的愤怒管理的冲动有些令人费解。为什么我听不到镇静剂试图消灭我那痛苦的,报复的雾气;我为什么不将愤怒感引导我的道德观念引向关于不公正的事实呢?生气是否是一种道德洞察力的形式(一种道德观念)还是一种道德观念的破坏(一种复仇的迷雾)如何取决于一个人当前是否在生气?这是愤怒管理的难题。
我认为,解决方案要求我们承认我们对正义作出回应的能力存在分歧:一个人越完美地关注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对一个人准备应对的错误的严重性就越不敏感。愤怒的人的观点与无生气的观点截然不同:每个人只能看到他们所看到的正义方面。当涉及到愤怒以及缺乏愤怒时,我们有理由抵制他人将自己的理由转移给我们的尝试。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尝试转变的尝试可能始于理性的话语,但它们往往演变成欺凌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转变”者被迫假装看到自己看不见的东西,或假装没有听到哭声在他们的耳边。这种愤怒鸿沟是我们政治困境的核心,并在最深层次上构建了我们彼此之间的互动。但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本身很难识别。
为了让人们看到它,我建议我们改变柏拉图的策略。柏拉图认为,如果我们首先看到正义在和谐统一的城市中广为人知,我们就会更好地理解灵魂。我认为,如果我们从研究冲突的灵魂开始,我们会更好地理解城市中的不公正现象-我们彼此之间的冲突。因为有一种人际关系的类比,我们似乎无法彼此进行对话,即我们无法与自己进行对话。有时候,一个灵魂的各个部分会说不同的语言。
几周前,当我回想起他生日那天一无所有时,我给我的朋友寄来了他生日礼物。我感到一阵愤怒,并很想把包裹丢掉而不是邮寄。在这两个选项之间被撕裂不像在菜单上的两个听起来不错的菜单之间被撕裂,还是在海边度假或在山上度假之间被撕裂。在这些情况下,我可以退后一步,调查我的选择,然后得出偏好排序,例如,如果最终无法获得我喜欢的菜式或地区,则可以合理地选择我的第二选择。我的所有部分最终都站在同一侧。生日的困境不是这样的:如果爱情战胜了恶意,但邮局却被关闭了,这并不意味着我回到第二好的选择去寻找附近的地方垃圾桶。
生日选择和其他选择之间的区别是很深的。确实,生日案件的分歧甚至比我们在“悲惨的选择”中所发现的情况还要深,例如苏菲在两个孩子之间的选择。使悲剧性选择悲惨的原因在于,这两个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一个人的一生并不能补偿您因另一个人的死亡而失去的一切。一个人强烈希望同时拥有两者,并被迫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相比之下,在生日的情况下,困难在于一个人不能同时想要两者-至少一次要。从价值上看,使礼物变得毫无用处的观点(所谓的“朋友”实际上是一个不加思索的混蛋,他不值得我当朋友!)就是在邮寄上看起来并不好;同样,当我沉迷于想象他对礼物的享受时,这种思想活动与冲动破坏它的冲动是不相容的。
我可以在这些观点之间摇摆不定,但我不能一次真正地兼顾两者。我不能问“考虑到所有问题,我该怎么办?”无需提出关于正在考虑什么事情的问题:没有“所有”都包括使我的朋友失望的恶意快乐和使他快乐的快乐。这些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它们是不可能的。
现在,通过将这些无用的价值分配给多个人,让我们从灵魂转向城市。考虑一下正义感使她无法放弃愤怒的人与正义感使她无法生气的人之间的冲突。如果我们把每个人都看作是我在生日案中摇摆不定的一种相反的道德观点的典范,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愤怒与无生气之间的相互作用变成了拔河。没有合理的方法来裁定他们的冲突-第三方调解员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他们想和谁在一起的人之间来回切换。
愤怒鸿沟经常被视为政治灾难:我们怎么能希望让每个人都坐在同一页上?为什么人们如此愤怒地改变主意呢?我一直在提出一个答案:人们因为理性和对正义的关心而抵制愤怒管理的强制性策略。那些坚持不懈的人拒绝让别人将他们从自己的财产中驱逐出去,这是事实。
也许正义确实是一种神圣的事物,某种规模的错误只能由一个人的回应来接受。我们应该为人类心理的异质性而感激,而不是为我们无法做出统一的回应而感叹:它使我们能够掩盖彼此的盲点。如果没有一个人在情感上是完整的,那么真正的道德权威就是集体,我们需要-并且需要学会认识到我们的需要-对于那些受白炽灯,无法熄灭的,集中的愤怒所鼓舞的人。他们看到了我们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我们不应反省地迫使他们冷静下来。我们还需要认识到那些天性平和而明智的人在另一端的美德,并停止认为这样的人会因为有些生气而变得更好或人性化。
生日难题的故事是真实的;这是几周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然而,奇怪的是,它也适合我几年前为我的书制作的一个虚假示例的模板,该示例是一个苦涩的妻子,她想丢掉一封信,信中她的丈夫不慎而苛刻地要求她邮寄邮件。
但是生活并没有完全模仿哲学。我的苦妻被任命来裁决她的内心冲突,但是当思想实验对我来说栩栩如生时,我并不孤单。当我前往邮局时,我儿子整个早晨都被困在屋子里,感到无聊,他问他是否可以陪我散步。当我经历愤怒的时刻时,他在我的身边-这与我的朋友没有给我礼物的事实无关,而是他努力地将其解释掉以为自己找借口的事实,以及嵌入其中的更大的行为模式-那是当我的眼睛朝着我知道垃圾桶所在的方向飞快的时候。
这不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报仇毁灭。如果我儿子没去过那儿,我很可能会再做一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该如何解释自己?
“包装里有什么?” 我们走路时儿子问我。 “告诉他我生日快乐,或者,实际上,第二个想法,他可能不那么高兴从一个从未听说过谁的母亲刚刚告诉他的生日的孩子那里得到生日快乐……” 我告诉儿子,我将按照这些条件传达生日愿望,我做到了。 别人的存在可以使我们变得更好,即使他们并没有使我们更像他们,也不改变我们,甚至不了解我们。 有时,其他人通过不感觉自己的感觉,确切地通过坚定地保持自己的身份来帮助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