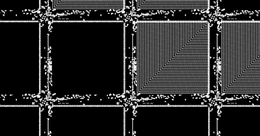无尽的生命(2014)
我的心理健康档案在1969年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生活中呼啸而过。我最近离开了天主教会(Opus Dei),这是我年轻的灵魂所奉献的宗教秩序,随后发生了严重的萧条。下面打印的记录是我许多看护人无法企及的。从那时起至2012年,他们记录了我在波士顿地区各个医疗机构和精神病诊所的治疗情况。
我是怎么经过他们的?两年前,当我陷入抑郁时,一位正在帮助我的朋友认为查看我的记录会很有用,所以我要求他们。为什么现在要发布它们?当然,这不是因为我认为我的治疗记录中的这些摘录显示出任何特殊的文学技巧或表现出异常有趣的心态,也不是因为我打算对我的治疗师,雇主或保险公司进行最小的丑闻调查。所有专有名称均已更改。
我们分散注意力的智力需要尽可能多的谈论抑郁症的方法,仅此而已。另外,鉴于这个特殊恶魔的寿命,试图从大量文字和针对其造成破坏的处方药中汲取一些见识似乎很重要。只要我们愿意仔细聆听空白,即释义,就可以说出最全面的官僚化医学知识。甚至首字母缩略词都有感觉。
关于药物的注释:抗抑郁药物已经进入五十多年了,目前尚不清楚药物是否比安慰剂好。关于功效或副作用的长期研究并不多,而FDA在批准之前几乎不需要进行任何试验。每种药物都对它为什么起作用具有或多或少合理的科学解释。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是,有些人服用后会变得更好,有些人则没有,还有一些人不服用会变得更好。
当然,从患者的角度来看,这都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您跳出皮肤,医生说您要服用一些药,就可以服用。就我而言,没有一个人表现出色。但是只有一对夫妇有无法忍受的副作用或使抑郁症恶化。
以下记录已被轻松编辑。拼写错误已得到纠正,缩写已标准化,医生的姓名也已更改。
患者被视为有礼貌的探访,因为他实际上不再符合在这里进行咨询的资格,因为他于今年6月从这里[哈佛]毕业。他计划去哥伦比亚研究生院就读。
他提出了有关天主教的非常激烈的问题。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开始越来越多地质疑他是否可以支持强调正统观念和缺乏调查的思想体系。他以我和他本人的智识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尽管有理智,他的确在此方面受到了许多情感动荡的影响。支持他走向中间立场,按照他的风格,这对他来说很难。
他对教会的失落感到恐惧,因此,可以澄清的是,他不必放弃教会或他在教会中所属的组织来进行审问,而他也将无能为力。满足于他担任的任何职位,直到他向自己和他人提出问题为止。他还担心他的某些行为是不适当的,而且我不认为这些行为是不适当的,除非它们表明一个年轻人在生活中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处于严重动荡中,并向患者说明了这一点。
他将与几位牧师交谈,而且确实可能在他到达哥伦比亚时寻求精神病学方面的帮助,以解决半瘫痪的强迫性人格的人格问题,即,他经常因自我怀疑和无果断力而瘫痪。
在面试结束时,他问他的困难是否会使他的选票延期,我说我不这么认为。
该患者曾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院就读,但实际上在功能上有严重的强迫症,因此不得不辍学。他在纽约市的诊所接受治疗大约八个月,但由于大约两个月前不清楚的原因而离开治疗。他现在在这里,希望自己团结起来,并计划通过扩展[学校]参加六门课程。
他来找我重新建立联系,并询问他是否可以接受治疗。我知道他的治疗对他来说一直很困难,但是将他视为一个非常麻烦的人,我敢说可能比青春期的适应反应更病-更可能是具有强迫症特征的边缘性人格。显然,他无法在该诊所接受治疗,并且不确定他是否要接受治疗。我告诉他,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应该随时与我联系,我会在该地区找到他的诊所。
这是这位33岁年轻人的首次精神卫生服务访问,他目前正在国际研究中心担任接待员。他向首席投诉人提出:“我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我曾尝试去诊所,但不确定是否应该去。我认为这些症状正在恶化。”
该患者是一个整齐整齐,口齿清晰,极度焦虑的年轻人,在过去的四个月中一直表现出焦虑史。他说,自4月(33岁)起,他变得越来越焦虑,难以入睡,午夜醒来和清晨醒来。他说在过去的几周里,他每晚只能睡大约五个小时。他描述了强迫饮食和大量摄入“垃圾食品”。他说,自从四月份以来,他已经增加了大约八磅。他报告能量减少,性欲减退,性兴趣下降以及勃起困难。他否认有自杀或杀人罪。他否认有幻觉或妄想的历史。他否认混乱的情节。此外,他否认吸毒或酗酒。
在过去的四个月中,他变得越来越疲倦,无法应付目前的状况。他说,他回想起他21岁那年的某个时期,当时他决定离开他一直信奉的天主教宗教秩序。
自从下令奉献给贞操与贫穷的外行命令以来,他一直无法致力于任何追求。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从一位治疗师转到了另一位治疗师,并且最近参与了原始疗法。他参与原始疗法已经持续了六个月,但他现在说他想寻求其他途径,无法解释原因。他还看了几位理疗师,包括哈佛社区健康计划的一位理疗师,他为他开了一些安定药,他按需要口服2.5至5毫克的剂量,夜间最多服用5毫克。他说,这偶尔可以帮助他入睡,但从长远来看并没有减轻他的焦虑。
他还说,大约一个月前,他见过一位治疗师为他开了Sinequan。他服用了几剂,但表示没有帮助,因此他停止了这种药物的治疗,此后也没有见过治疗师。
患者报告严重焦虑和痴迷症状。他报告无法做出任何决定,即使他是否能够继续治疗也是如此。他担心自己的医疗上可能有问题,因此已预约去谢泼德医生见面。除了立即缓解或保证他的症状不会变得更糟之外,他现在不确定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他担心自己会变得如此疲倦,以至于他将无法返回诊所,甚至无法走过校园去见我下次约会。
我建议他再来进行进一步评估。我将在星期五见到他,然后再请他休假两个星期。他说他确实有朋友会拜访他,这样他就不会被完全孤立。我们还讨论了他可能会在本周的任何时候进入步入式步伐的可能性,或者在他认为有需要时可以致电急诊室的可能性。
我的最初印象是,这个年轻人表现出焦虑不安或焦虑发作。他否认过度换气或心pal。但是,他确实描述了一些恐怖的症状,因为他担心自己会留在家里而无法离开。我认为此时无需紧急住院。我讨论了开始使用抗抑郁药的可能性,这可能有助于治疗抑郁症和惊恐发作症状。但是,我还建议他在开始服药之前需要进一步检查。
该患者过去似乎很难进行预约,并且我讨论了继续进行评估和预约以完成评估的必要性。我的计划是在周五见到他,并在接下来的两周内请他继续评估。
在詹妮弗·霍恩斯坦博士的安排下,我今天见了塞西亚拉巴先生。我的评估与霍恩斯坦博士的观点一致,是该人患有严重的内源性抑郁症,并伴有精神分裂症人格。
他承认的严重抑郁症的症状已经出现了两到四个月,包括频繁的清晨醒来;便秘;对性缺乏兴趣;日间变化,以清晨最差;体重增加八磅,食欲增加;并大大减少了能源。我不认为他患有真正的惊恐发作,而是焦虑的躯体症状。
唯一的情感疾病家族史是堂兄,母亲的兄弟儿子,他在21岁时自杀。没有酗酒的家族史。
当然,从十年前的水平开始,他的机能长期下降是令人不安的。 1969年,哈佛大学以平均2组的成绩毕业后,他从哥伦比亚大学退学,在那里他学习历史。从那以后,他已经在当地福利部门担任社会工作者多年,但是他说这项工作主要是书面工作。去年,他一直在哈佛担任接待员。他没有亲密的朋友,尽管曾经发生过性交,但他却没有亲密或持久的关系。
他形容他的母亲虽然很紧张,却一直在统治着自己,而父亲则形容为一个胆小,虚弱的人。父亲担任办公室工作,母亲担任订书机。有一个兄弟正在萨福克社区大学(Suffolk Community College)上夜校,并在公共工程部工作。因此,仅去哈佛并在那里做得好,患者就大大超过了他的家庭的成功水平。
我不知道他随后的衰落是否部分归因于他的成功所代表的恋母癖。现在,他对失去控制有多种恐惧,他幻想着这种失控会导致他变得被动,无法担任工作,去福利或去医院并且无法照顾自己。这可能是他早期的成功所引起的回归。
他描述了自己想成为二,三年级的牧师,而这种角色在他的社区中受到了高度尊重。目前,他担心自己背弃宗教信仰可能是一个错误,为此他可能会被判处地狱。他还担心强迫性手淫会受到惩罚。他说,在最近几个月失去性欲之前,他每天都要从事十年。
考虑到慢性精神分裂症的适应,十年来功能的明显下降,以及他对宗教和哲学的文化认可,尽管他在文化上得到了认可,但我为一种思想障碍苦苦寻找,但无法满足于一个人的存在。在过去四个月中,他的功能显然与他过去十年中长期的功能水平不连续。在这四个月中,他有躁动的内源性严重抑郁症的经典体征。
体格检查已经完成并且是正常的。 CBS,SGOT,尿液分析和甲状腺功能检查正常。 BUN略微升高。地塞米松抑制试验为阴性。
据我评估,他可能会接受三环类抗抑郁药治疗。我今天开始与他讨论此问题,明天将与他见面进行进一步讨论,并且可能那时让他开始使用地昔帕明。
首席投诉人:患者见过梅森医生一次,由于经济原因,他将他转介到这里。通常感觉在情感上很脆弱。精力旺盛,无法做出人生决定。觉得他在专业上漂流。 “他所做的事情简直太夸张了!”
当前问题的历史:早在21岁时就脱离了宗教传统,天主教的创伤,并认为他从未真正康复过。
病史/当前药物:身体健康,而不是“精力充沛”。没有药。禁止饮酒或吸毒。
入院时的印象:患者发现很难说话,似乎非常紧张和沮丧。
问题1:抑郁表现为社会孤立,无法做出职业决定以及压倒性的内感。
目标(短期):患者将更多地了解其行为与抑郁之间的联系。病人对自己的选择会感到更少的绝望和内。
问题2:强迫症和抑郁的人格障碍导致他的瘫痪和缺乏亲密关系。
目标(短期):患者将变得更加灵活,更能容忍自己和自己的情感。
识别数据:Scialabba先生是一位39岁的白人单身男性,他在哈佛大学从事全职工作。他于196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Scialabba先生自称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后离开了教堂。麦克莱恩(McLean)的心理医生大卫·梅森(David Mason)博士推荐了他。
数据来源:自8/87起,LICSW的Roberta Tate就曾见过Scialabba先生每周一次的心理治疗。 Juan Durendal医师在7/23/87对患者进行了评估,本报告中的某些数据来自该评估。
首席投诉人:Scialabba先生形容自己“在情感上脆弱,举足轻重,无法做出人生决定。我的工作资格高得离谱。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停滞不前,想知道是否有药物可以帮助我。”
存在问题的历史:Scialabba先生的精神病症状可以追溯到17岁,当时他有任何性冲动而变得无行为能力的焦虑,并且会犯有罪恶的沉思,破坏了他的正常活动。他去找一个牧师,他告诉他对病人的性冲动对上帝负责,而这种焦虑的发作就停止了。 Scialabba先生还加入了一个虔诚的全男性天主教组织Opus Dei,他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就非常参与该组织。他感到传教士热衷于converting依他人,并让他们参与Opus Dei。 Scialabba先生将他的承诺描述为“强烈,苛刻和终身”。大学四年后,他“对天主教失去了所有信仰”。
Scialabba先生形容他离开教堂和Opus Dei极为困难,他形容混乱和人格解体,他不知道自己打算做什么,但他参加了Opus Dei和试图谈论他的信仰丧失。相反,他变得烦躁,不得不被带出房间。 Scialabba先生觉得他从未从这种情绪低落中恢复过来。他将离开Opus Dei的那段时间描述为他一生中最有意义,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当时他感到所有人生以及理智和哲学追求对他都是开放的。
他曾在欧洲知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法学院尝试过研究生院,但他退出了这两个领域,因为每当他尝试在哲学或知识史上进行认真的工作时,他都会变得不堪忍受,不得不停下来。在哥伦比亚工作了一年后,他回到了剑桥,从那以后一直留在这里。
Scialabba先生曾做过一系列“不屈不挠和无用的工作”,例如代课教学,福利社工,目前是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接待员/工作人员助理。 Scialabba先生在过去的五年中,为Village Voice和一本名为Grand Street的杂志进行了大量的自由撰稿。
Scialabba先生现年48岁,出生于波士顿,在东波士顿长大。他的父母生活,结婚并居住在东波士顿。他是一个哥哥中两个孩子中的第二个。他是单身,从未结婚,在45岁或46岁时与珍妮丝(Janice)有关系,她是一家学术刊物的编辑,并撰写论文。这段关系已经持续了2.5年,Scialabba先生没有孩子。他没有很多朋友,但是有几个。他拥有历史学硕士学位,是国际研究中心的建筑经理,但花大量时间从事自由书评。他在国际研究中心工作了16年。他独自一人住在剑桥,不抽烟,不喝酒,不使用任何药物,没有这些病史,没有家族史,就精神病史而言,他有一个堂兄表妹,他在20岁时自杀。他的母亲是一个严重的运动障碍和严重的痴迷者,诊断出自一位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对他而言似乎是正确的。他没有任何身体问题,因此服用Zoloft的剂量最高为250毫克,尽管他维持了50毫克的三年维持剂量。他没有很规律的运动,每周慢跑一次,每天早晨做5-10分钟的健美操。在心理治疗方面,他已经接受过多次心理治疗,但他说失败了,只有一年多了。在过去的15年中,他经历了两次临床抑郁症,都持续了几个月,但情况非常糟糕。他已经见过伍德库特博士大约五年了。
他今天在场指出,六周前的那集令他有些震惊。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他指出五年后的三年前他开始接受心理动力疗法。那是他喜欢的人,但似乎无济于事。他认为自己的担忧部分是生物化学的,他对佐洛夫(Zoloft)表示感谢。
他读过许多文章说认知疗法的成功率最高,他读过《感觉很好》和亚伦·贝克写的一两本书,尽管他对此表示非常鄙视,现在仍然如此。他同情心理分析的思想,但他对这些忧郁症感到沮丧。
他指出的总体问题是,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是宗教秩序的一部分,他于夏季在大学和研究生院之间的21岁时离开。他非常激动,不得不退学。貌似,他的生活中的各个部分再也没有回到过一起。他感到自己无法做任何智力工作,再也没有恢复过生活。当他尝试阅读哲学或政治历史时,他无法集中精力,感到一定的背景紧张。在过去的15年中,他一直受到文学批评,撰写了约150本书的评论,获得了国家奖项。但是,这与从事职业并不相同,他仍然感到有点残疾。从微观上讲,他一直非常执着,烦躁,沉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