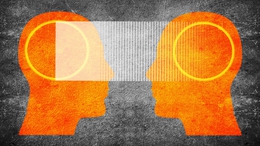遗失思想:冥想的心理风险
在2017年3月的一个无云的下午,Megan Vogt将她的卡车推向沿海平原和阿巴拉契亚山麓之间的特拉华镇。她正在迈向丹巴班堡的沉默休息一下,这是一个专门从事名为vipassana的冥想中心的冥想中心,它的网站描述为“普遍存在的普遍弊端”,这些普遍存在的“普遍存在”提供“从所有污秽的全部解放,所有杂质,所有痛苦的普遍存产” 。“那些参加Dhamma Pubbananda的撤退的人承诺观察严格的规则(没有阅读,没有跳舞,没有祈祷),并留下整整十天,因为它是“既不情愿,也是不可取的。 。 。在找到纪律时太困难。“梅根知道她必须丧失她的手机并观察强制性的“高贵的沉默”,所以她最后一次打电话给她的母亲。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她说。 “我会在十天内与你交谈。”
在撤退的第一天,梅根,一个开朗的二十五岁,蓝眼睛和肩膀长度的头发染成了一枚红衣主教,早上四点醒来,醒来铃铛。为了累计十个小时和四十五分钟,她坐在地毯上坐着,她的脊椎直立,并试图专注于她的呼吸。在休息期间,她在中心十三英亩的山毛榉树和橙色百合花中走。那天晚上,每个人都聚集在冥想大厅里,一个教练将一个录像带插入一个旧的录像机。在屏幕上是一名带有柔软,戴着眼睛的老人,坐在地板上交叉腿。缅甸商人转向大师的萨塔亚纳·戈伦卡(Satya Narayan Goenka)在五十年代冥想,希望缓解他的慢性偏头痛,对他继续建立一个以上一百多个Vipassana中心的全球网络来说非常满意。 Goenka于2013年去世,但他的撤退上的学生仍然从硕士的颗粒状记录中获得了大部分教学。
“第一天结束了,”Goenka说。 “你有九点剩下工作。”他的声音是砾石,他的举措几乎不合适。 “为了获得这里的最佳结果,你必须非常努力地工作,”他说。 “勤奋,耐心,耐心地,但坚持不懈地。”他谈到了学生在未来几天遇到的困难。 “身体开始旋转。 “我不喜欢它。”心灵开始升级。 “我不喜欢它。”所以你觉得非常不舒服。“他称未经训练的思想“一束结,戈迪亚结” - 张力和激动的引擎。 “每个人都会意识到一个人的疯狂。”他用一个同情的空气看着相机。 “这种技术会帮助你,”他说。 “你必须去痛苦的来源。”
当时,梅根的生活在助势中 - 她刚刚经历了一个分手并决定搬到犹他州,她计划在有机农场上工作。十天的冥想听起来恢复,一种将页面转到新章的方法。她发现休假的早期几天在普通的意义上挑战:她疼痛膝盖,痛苦的痛苦,饥饿的痛苦。但它没有什么是她不习惯她作为一个美洲志愿者的时间,维护徒步旅行径出来,或她在国家公园露营的月份。
在第七天的早晨,梅根去外面冥想一棵树。她现在已经登录了超过60多小时的冥想。她不确定她坐在那里多久了。 “时间已经放慢了,”后来写道。蕨类植物和草地振动;他们是由振动制成的,就像她一样。梅根感觉到一个精致的宁静,不像她所知道的那样。眼泪来到了她眼中。 “我很高兴。我终于知道了我在世界上的地方。我是地球的孩子,我需要分享我的快乐。“
但是几个小时后,梅根的幸福消失了。她累了,然后排干了。她躺在床上,无法备受备份的能量。下一个冥想会议开始了。她感到沉重,负责世界上错误的一切。也许我是圣洁的,她想。也许我放在这里来治愈每个人。她强迫自己直立,把脚放在地板上。
走进冥想大厅,梅根看着沉默的冥想者的行,他们的眼睛闭着或凝视着墙壁。通过她身体的“巨大的恐惧”涌动,她发现自己的恐慌,无法移动。 “我刚刚划出太空,”她稍后写道。 “我不记得我在哪里。我是谁。我在这里做什么。“那么黑暗的想法涌现出来了:是世界末日?我死了吗?为什么我不能运作或移动?我现在可以听到佛陀。他告诉我冥想。我不能,我很困惑。这是一个测试吗?我应该喊出“我接受耶稣作为我的主和救主?”我应该做些什么?我感到很困惑。
Warning: Can only detect less than 5000 characters
他们得出结论,“我们期望在普通人的某些地方使用任何形式的抑郁程序,”包括冥想。
正是在梅根在冥想大厅解开后发生了什么情况。她走到外面,试图撕毁围栏。另一方面,她闯入无法控制的笑声。肯定的是,其中一位教师是一个名叫yanny hin的中年女人,意识到某些事情是错误的。欣到厨房里的志愿者,乔迪贝克,并问她是否介意参加梅根。 Beck尝试与Megan进行谈话,但不能跟随她的思想训练 - 关于上帝“回到她身边”,因为她所做的事情。梅根一直在问,“耶稣惩罚我吗?”贝克告诉我。 “她不明白她发生了什么。”
当她咆哮时,梅根提到她已经停止服用了她的药物。自二十年代早期以来,她一直处于Zoloft的最低治疗剂量的Zoloft。在承认迈根撤退之前,该中心的管理人员要求她的医生填写了一个证明她身体健康的表格。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患者在课程中遇到困难,您可以向他/她提供吗?”梅根的提供者检查了。 HIN指示贝克为剩下的撤退管理梅根的药片,但该中心没有试图联系Megan的医生。
梅根在她的房间里过了很多三天,试图专注于她身体的感觉。贝克坐在她身边。 “她总是可以选择离开,”贝克说。 “她想留下来。她加倍了。她努力了。“根据Beck,Megan告诉Hin,她觉得她疯了。欣格指示梅根关注她的呼吸。在一次会议期间,梅根坐起来遇到了麻烦,所以欣喜让她躺下。当梅根握紧她的拳头时,欣告诉她专注于她手中的感觉。 “Yanny没有感觉到这是她无法教她的方式,”Beck告诉我。当梅根搅动时,“指示总是一样:闭上眼睛,回到冥想。” (Yanny Hin拒绝接受对这个故事的采访。)
在最后一个晚上,在梅根的心理健康危机显着发作后超过了60多小时,贝克设法与梅根的家人取得联系。 “她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糟,”贝克告诉我。 “她看起来像是自己的幽灵。她没有睡在几天内。她已经停止淋浴。“贝克,谁月光作为调酒师,告诉我,当有人无法落后一辆车后面时,她认可。 “她没有没有帮助地离开。”
当梅根的父母和她的妹妹,乔丹,第二天到达时,贝克要求他们一次访问梅根一个,以免压倒她。她的母亲克里斯先进了。 “这并不困惑,这是精神病,”她说。 “那不是我的女儿。”乔丹进来了下一个。梅根在床脚下驼背,盯着地面。她看起来苍白。约旦坐在另一端。
“这是我,”约旦说,伸出她的手。 “你可以碰我,我在这里。”
梅根从她的家庭中重新破灭,抵制进入汽车。 “我必须在这里死去,”她哭了。最终,欣婷说服了梅根和她的母亲和妹妹离开。她的父亲,史蒂夫,沿着梅根的卡车。当他们开车时,梅根希望死于暴力的紧迫感。她紧紧抓住她的脖子。她用毯子塞满了嘴。她试图爬进前排座位上,拿到手套箱,在那里她知道她的母亲保持开关。随着汽车加速在州际公路上,梅根撬开了门。乔丹对她举行并闭嘴。
克里斯叫史蒂夫,并告诉他,她直接前往马里兰州的马里兰州大学,有一个精神病单位。梅根尖叫着她的母亲,“停止与魔鬼说话!”乔丹脱掉了一条梅根为她脱颖而出的是红木皮和松坚果贝壳的项链。她把项链放在梅根的手中,“只是试图让她觉得有一个体力的现实。”
在急诊室,梅根反复,一遍又一遍地,“我做了一些可怕的事情,我做了很糟糕。”
“宝贝,你做了什么?”她的母亲恳求。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工作。”
根据医院记录,梅根出现了“乱七八糟的折扣”,似乎“回应内部刺激”。她的初步体检是“有限的,因为患者非常混乱和害怕。不希望任何人触摸她。“由于医务人员带着她的威力,梅根摧毁了她的IV并推出了主治医生。医生然后强制地施用了肌肉注射的地理,一种强大的抗精神病症。除了她的心理困扰之外,无论她的疾病都在造成身体反应:她的胃搅拌,她都很寒冷。她测试了可能诱导精神病的药物和感染;一切都回来了消极。
她在医院的第一个晚上,梅根始于一个新的药物方案:抗精神病药Zyproxa,以及Ativan,苯并二氮卓用于治疗焦虑。两天后,克里斯,史蒂夫和约旦来到了几个小时。梅根告诉他们,她不记得她在那里遇到了如何,她的回避是一个阴霾,但她被迷茫而且在一个明亮,几乎卑鄙的心情。 “我不敢相信我是一个坚果,”她说,笑。 “人们会觉得我疯了。”他们离开后,一位医生在梅根的图表中写道,她“看到他们后感觉更好”,但她也可以听到音乐演奏。
一周后,梅根的精神病浪潮得分。她正在睡得更好,经常吃饭。她说她可以更清楚地思考,并告诉她的医生,她是“对不起一切”。医务人员鼓励她谈谈或写下她的经历。他们用纸和一支笔留下了她。 “我在第七天失去了它,”梅根写道。 “我在正确的道路上。我放弃了所有的东西。但是我意识到我也不得不放弃我的身体,这就是让我陷入恐慌的原因。“她相信她的崩溃使得“过于睡了三天的脑子过度劳累”。
梅根没有给出正式诊断,但被告知她可能表现出双相情感障碍的症状。她的Zoloft处方被停产,因为她的医生认为它可能会为她的情绪波动做出贡献。 Megan没有提取症状,并提供Zyprexa和Ativan的供应。建议她在一周内看到一个精神科医生,如果经历过“赛车思想,增加的言论,情绪宽容或减少睡眠需要”,就可以立即寻求医疗注意力。有了这个,梅根在“医学上稳定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安全问题”。
乔丹们为姐姐发生了一些线索,为互联网进行了彻底挑剔。她发现了一个位于布朗大学的猎豹大学的在线支持小组的Facebook页面,为冥想沉淀出来的心理健康问题的人提供了指导。其网站特色文章来自学术期刊和冥想诱导的医疗紧急情况的第一手账户。 “当我说猎豹屋真实地拯救了我的生活时,我并没有夸大,”写下了一个“前冥王星 - 危机”。乔丹向集团发送了一条消息。 “我姐姐本周进入了冥想诱导的精神病州,我正在寻找帮助,”她写道。 “她完全迷失方向,深信她需要杀死自己。”乔丹要求她的信息转发给集团的促进者,这是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和棕色的神经科学家,棕色命名为Willoughby Britton,他们已成为迄今为止冥想的最重要的倡导者,即使对于没有潜在的精神病疾病的人,冥想也可能有害。
布里顿已经开始作为狂热的冥想者,而是作为中间的研究生,她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发现。作为她在亚利桑那大学博士研究的一部分,Britton进行了一项研究,以确定定期冥想对睡眠质量的影响。当时的共识是冥想帮助人们更好地睡眠,但大多数现有的研究都依赖于自我报告。 Britton是她的子领域的第一个研究人员之一,以一夜之间将受试者带入实验室,测量其脑波,眼睛运动和肌肉张力。布里顿收集了两百夜的数据夜晚。与其他研究一样,她的十二名受试者表示,自从每周五天举起冥想以来,他们已经睡得更好。并且数据似乎支持每天冥想不到30分钟的小组。但任何超过半小时,趋势开始沿另一个方向移动。与八人对照组相比,每天冥想超过三十分钟的受试者经历了较浅的睡眠,夜间经常醒来。参与者报告冥想,他们的睡眠变得更糟。
Britton的样本大小很小,但其他研究人员还记录了这一明显的悖论阳性自我报告,结合了负面结果。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2014年学习使两组参与者与公开敌对的评估员进行面试。一组预先冥想三天,另一组没有。冥想的参与者报告在采访后立即感受到压力较小,但它们的皮质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