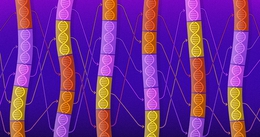失去思绪的神经科学家说它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 石英
您可以成为大脑专家,并花30年的学习精神障碍,它仍然不会为自己的疯狂做好准备。专业知识将无法解释为什么你不再识别你的房子或汽车,或者为什么你在头上有一个装满紫色的紫色指甲花的早晨慢跑,并且不知道你在哪里,即使这是你自己的邻里,你自己的街道,这些是你每天都通过的树木和鲜花。
如果有人应该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的变化并将它们连接到大脑中的转变,它是芭芭拉林卡卡。作为Marylanda,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神经科学家和人类脑收集核心主任,Lipska已经戳了,刺激了,检查,切割,切割和分析了无数的大脑,试图找到疾病与健康之间的区别。
然而,当她在2015年失去自己的心灵时,Lipska不知道事情发生了很大。她的医生家庭也没有。 “我们完全忘记了它,”她说。
现在,Lipska必须检查有时候,以确保她正在思考。 “吓到我了。当它发生时我不会看到它。我看着自己。我问了我家人的问题,“她说。 “我是谁吗?我逻辑吗?我有意义吗?我怎么会知道?这是一种可怕的经历。“
你可能永远不会失去理智,但是你将有很大的机会,或者已经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候已经存在了心理健康问题。焦虑,抑郁,注意力缺陷障碍,创伤后应激,精神病,精神分裂症都是常见的。
根据国家联盟的精神疾病,在美国每五名成年人中,每五名成年人或超过4300万人经历精神疾病,或者在任何一年中,都会在任何一年中经历精神疾病。根据一项全球武士医学期刊的报告,在全球范围内,每四个人都会患有生命的心理健康状况。
然而,据报道称,很少有资源致力于健康的这一关键方面,而且结果是全球危机 - 这将是2030年的“人类能力的纪念性损失”,根据该报告。由于心理健康服务是“常规比身体健康的质量更糟糕......所有国家都可以被视为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在柳叶服曲中写下全球专家。
Lipska认为世界可以在治疗精神疾病方面变得更好。但是,她在她的书中解释了失去自己思想的神经科学家:我在2018年4月出版的疯狂和康复的故事,部分解决方案在于停止区分心理和身体问题。
神经科学家希望全世界了解精神疾病是器官故障,相当普遍和危及生命。在她的书中,她争辩说,我们仍然判断大脑故障,好像它们是角色赤字,对一个人的价值的反思而不是物理过程的结果。
10月12日与Lipska发表讲话,我问她是否会对大脑认识到真正理解的大脑。头脑可以理解心灵吗?这就像眼睛试图看到自己,毕竟。
“是的,”Lipska回复。 “它不会发生在我的一生中,但我们会有一天会理解大脑,然后我们将像物理疾病一样治疗精神疾病,表现在一个极其复杂的器官中。”
“没有人有罪,因为他们是精神病患者。这不是他们的错。“
在此,Lipska是意图的。从她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精神疾病。大脑不是像心脏那样的简单器官,这基本上是泵。这是一个有数十亿神经元和数十亿个联系的器官,在不断的转变,随着每一种互动和经验而改变,吸收文化,在我们的行为中表现,并运行个人节目。
有时节目并非好处,它完全失去了董事。 “但没有人有罪,因为他们是精神病患者,”Lipska说。 “这不是他们的错。这是一种像其他任何疾病,我们只是不明白。“
Lipska的个人经历改变了她对精神健康和精神疾病的方式,因为她写在她的书中。对于她的大部分成年生活,她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坚定的雄心勃勃的研究员,致力于她的工作,家庭和跑步马拉松。但在2015年被诊断出患有脑癌后并开始服用疾病的药物,她成为别人 - 而不是她喜欢的人。 “我完全不安。”
她生气,令人兴奋,苛刻,坚持不懈,不合理,不宽容,有时对自己和其他人有危险。她做出了不好的决定。有一天,她试图用超市独自走家。她迷路了,小便在自己身上,最终搭便了一个房子,她无法识别或指出司机。她对她心爱的孙子们吝啬,粗鲁到试图帮助她的医务人员。她在非威胁的情况下看到了威胁,并且错过了坚持做她的事情的真正危险,就像驾驶一样。
在2015年患有脑癌患有脑癌后,她成为别人 - 而不是她喜欢的人。
她不能准确地说,是什么导致她的行为变化,无论是癌症还是药物或疾病的压力或所有三种合并。但她可以指向受影响的大脑中的地区。 “在我的案子中,额头皮质有很多压力,这对我们的行为进行了调节,”神经科学家说。当她的额度皮质发生故障时,她无法再控制自己 - 所有关于办法和何时做某些事情的规则以及如何沟通,以及如何沟通,变得无关紧要。对于所有实际目的都不存在,他们无法进入。
经验改变了她的工作。经过一生的学习大脑,寻找神秘器官中疾病的证据,她更敏感 - 更加了解精神疾病的人们如何遭受遭受的人,以及对那些生病的人和那些围绕着他们所涉及的斗争。
“当然,我以前知道这一切,”她解释道。但是,理论上的知道与自己的影响不一样。因此,当她从癌症中恢复而且压力从她的大脑脱落时,她将她的科学知识应用于可怕的个人经历并写了她的书。在一段段落中,她写道:
尽管我一直都在学习大脑疾病,但在我的生命中第一次认识到它有多令人深受令人深刻的令人满意,这是一个不起作用的大脑。我记得从我疯狂的日子和几周内记得,我变得越来越害怕,我会再次失去理智。也许疯狂在当时描述我的病情不是正确的术语。毕竟,它不是官方诊断,但它通常非正式地使用,以意味着不稳定,精神错乱,愤怒和无组织的行为。因此,我认为自己经历了与一系列精神障碍相关的症状。换句话说,我有一个疯狂的刷子。我回来了。
这本书也努力帮助缓解精神疾病的耻辱。 “如果像我这样的人出现这个问题并承认尽管他们的意志,他们会失去它,事情可以改变,”Lipska说。她走出了肢体,暴露了她的最令人不愉快的方面,以其他方面的高度成就和令人钦佩的存在,使社会可能会意识到每个人,任何人都可以失去主意,永远失去他们的思想。
“如果像我这样的人出现这个问题并承认尽管他们的意志,他们会失去它,事情可以改变。”
在这本书发布后,Lipska惊讶地发现有多少人听到她要说的话。她已经被欣赏的消息从那些说她启发的人的人们淹没了。尽管如此,她不确定为什么她的经历是鼓舞人心的,因为它只是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情 - 她失去了一段时间。 “我没有选择这条路,”Lipska指出。这是一个可能会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
当我停下来涂抹她对我一个问题的回应时,她打破了沉默:“我有道理吗?”她问。
在那一刻,很明显,Lipska没有夸大自己检查自己。她仍然生活在她经历的替代现实的阴影中。神经科学家不再完全相信自己或依靠让她成为一个世界着名的研究员的大脑。一时间,她的思绪失败了,现在她谨慎。 “我不沉浸在消极之中。我只是一种表现出疾病的方式。现在我必须更加意识,“她说。
我希望我能说我不知道Lipska在谈论什么。但是我愿意。这就是我读她的书的原因。
有一天,我的大脑破裂 - 或者也许不是一天。它可能是一个累积过程,这是一生使用的结果。它可能是坏寿司 - 有一条叫做梦想鱼的鱼,导致36个小时的地狱般的幻觉,我很乐意在最终的疯狂中用疯狂钉住。但它可能是一百万件事。我永远不会知道。
这,我可以告诉你。我头疼。感觉像一个洞穿过我的大脑中心钻了,一切都通过它而过去,现在,未来,事实和小说,我的所有个人故事和我所消费的人,新闻,电影,电视,书籍。这一切都变成了一个典型的故事,我试图排序但不能。
我到处寻找意义。在车牌,在保险杠贴纸和街道标志上,我在垃圾桶里发现的收据时,当我走路的时候,在遛狗,在飞行开销的鸟类中,在邻居房子的灯光闪烁,在隔壁的灯光下,在倾倒的雨中,在我的倾盆大雨中突然间的书籍,当我看时,没有内部没有写作。我看到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我生命中不同点的角色,所有人都在森林里的一辆大篷车中驾驶,例如,所有的狗都在他们的方面。
我在这段时间里有回忆,但他们不可靠。一切都在交织。你本可以告诉我自己的任何东西,我都相信它可能。也许我是一个罪犯。当我作为刑事辩护律师工作时,我曾经拥有的每一个客户都可能是我。任何故事都可能是我的,虽然我不记得犯罪,但我觉得足以承认任何事情。
在家里,在长期凝视之后,我在墙上重新安排了墙壁上的所有艺术品。当我的丈夫问图像发生了什么时,我告诉他我试图重写故事,所以它会有另一个结局。他耐心等待,解释了电影海报和漫画并没有告诉我们的故事。我们没有吸血鬼在失去的男孩身上。我们没有居住在Caligari博士的内阁中。他实际上不是惩罚者。但是,第二天,当艺术都在墙壁上,他超越了担心,特别是当我告诉他时,我会被锁定,这一切都与唐纳德特朗普有关。
我看到了一名医生。除了我似乎苍白和瘦弱,她不知道是什么错。接下来我看到了一个精神科医生。他说,“与你的教育一样多的人,不要只是疯狂。”他的无知焕发我。
然而,他的反应类似于我以前在和平军团服务时从护士获得的那个。当我告诉她时,她笑了路,我在一个小小的偏远的村庄,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干净的人。”后来,我患有脑疟疾,并且已经发烧了几个月,所以我的大脑真的有些不对劲 - 但她是正确的,我也没有疯了。
我们假设有一定类型的人失去主意。事实上,它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这将我们带到Lipska的观点。我们假设有一定类型的人失去主意。事实上,由于任何我们甚至不知道的任何原因,都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而且因为大脑及其行为表现都是如此神秘,因为我们对此无知,我们害怕和羞于摧毁我们的权力。
当我们感冒或打破骨头或被诊断患有癌症时,我们感觉不相同类型的耻辱。然而,大脑是一个不同的故事。 “你可以失去你的工作。你可以避开。说你有精神疾病就像'哇,'“ Lipska笔记。但是,她说,除非,我们不会找到解决精神疾病的方法,并才能消除保密和耻辱。
在我的情况下,脑MRI没有任何普通的。这是一个缓解的东西,但也有点令人失望。要指出的一些物理事情至少会解释这一体验。
我如何再次阻止我的思绪再次变得混乱?是什么让它发生在第一个地方?
最糟糕的是持续了几天。两周后,我或多或少罚款。我和朋友说话。我再次读,没有混乱。我用津津乐道解决了无限的笑话,感受了与作者David Fost Wallace的新血缘关系,他不能与他的大脑一起生活,并自从我第一次举行令人艰苦的文本以来自杀。我回到了我身边。
一切都恢复正常,有点。但没有什么再也不会是一样的。像Lipska一样,我不再完全相信我的大脑了。对我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而是实际上,一切都是感知;那个现实是微妙的。似乎我们只有我们的大脑过滤和分开经验的能力,并保持一切。但是我如何阻止我的思绪再次变得混乱?是什么让它发生在第一个地方?
汉娜UPP是在纽约的Bryn Mawr大学生,在2008年失去了她的身份。她在这个城市失踪了。安全摄像头在健身房和苹果商店发现了她,但当人们面对她询问她是否是失踪的女人,她否认了它。三周后,她被赛人渡轮船长在水中找到并被带到附近的医院,在那里她能够告诉医疗人员她的名字。 UPP从自己中消失了。然后她回来了。
医生后来得出结论,她经历了一个狡猾的状态。术语“Fugue State”-Think Fugitivity - 首先在1901年法国心理健康杂志中使用了一篇关于一个关于一个年轻女性的一篇文章,似乎在短时间内转变为其他自我。在催眠下,她可以描述备用自我的行为,但在意识时,她无法记得居住在另一个现实。
在精神病学的领域,与奥秘的那是陌生的,魔法州,也许是恰当的,完全难以捉摸。他们很少见,极端逃离自我,持续几小时到几年。但他们确实发生了,他们似乎被共同生命压力源 - 财务困境,工作问题,关系困难等所引发的。
在她母亲的死亡和发现她的丈夫有一个情人后,1926年被诊断出患有一个解离的牧群的神秘作家阿加莎·科里。
例如,奥秘作家阿加莎·科莱斯蒂在她母亲的去世后被诊断出患有一个解离的牧圈,并在发现她的丈夫有一个情人之后。她留下了一系列混淆的笔记,消失了几天,被湖泊抛弃了她的车,并被发现在另一个名字下的水疗中心。
这些分离国展示了实际上的“自我”是多么微妙。 “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叙述,人格稳定。这是一个小说。当一个人进入一个狡猾的人并成为别人 - 或者不是 -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夸张版本,“瑞典伦敦伦敦伦敦省心理学教授EtzelCardeña告诉纽约人。
换句话说,自我是对各种的制造,比实际的存储器汇编。
“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叙述,人格稳定。这是一个小说。“
我们需要自我的经验,无论是暂定的还是虚幻,以便运作。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教授David Spiegel,并认为在没有身份的情况下,在世界上不可能在世界上,从所有其他人分开自己的方式是不可能的。 “它可能是稀疏的,它的结构或细节越来越少,但我不知道你是否可以成为一个运作的人,没有一定的东西,”他告诉纽约人。 “你需要某种方向来理解你是谁以及你在这里做什么。”
证据证明,这是经历突然解剖国家的人,从自己突然破坏,往往不知不觉地取代他们的身份。例如,2013年2月,Michael Boatwright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棕榈泉醒来。他拥有美国护照和加州身份证,但他只是瑞典语,坚持他的名字是约翰ek。事实证明,他像孩子那里住在瑞典,并且一段时间从他自己消失,用过去召唤的替代品取代他的身份。船员被诊断出患有“以击球状态的瞬态全球艾尼西亚”。
没有药物治疗曲灵音态,对他们来说相对较少。与其他形式的胃杉一样,它们可能由于大脑部位之间的关系而发生的不平衡,抑制回忆的响应和肢体系统的关系。根据Spiegel的说法,分离障碍的人通常具有肢体系统,特别是海马的过度活跃的正面皮质和低活性,导致抑制记忆。它似乎损失了记忆力导致自我遗弃。
恢复可能是突然和完整的,就像一个28岁的尼日利亚医科学生,在他的房间里幻觉迷失了两天后失踪了两天。他再次在他哥哥的家中重新出现在英里之外,几天后,没有回忆临时发生的事情。研究人员认为,他的案件是由医学考试的压力引起的,他以前失败了,他以前的失败了,他必须借钱。他没有精神疾病的历史,没有毒品,没有喝酒,没有任何伤害他的大脑。他刚刚在一个特别紧张的时间内留下了自己,再次再现了。
这些极端的逃避自我案件,并返回,强调了心灵的脆弱性和韧性。我们完全依靠生存,制定自己似乎属于我们的自我。但它可以失败,每小时或几年或一生。更常见,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提醒,这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
我问Lipska如果更容易讨论她发生的事情,因为她知道癌症和药物可以解释为什么她的大脑改变了,最终导致她的奇怪和无法控制的行为。但她驳回了癌症或药物为她提供了独特的借口:“这都是身体疾病。”
身体和精神疾病之间的错误区分是推动危机,耗资的生命和金钱。
这是她的重复主题。 身体和精神疾病之间的错误区分是推动危机,耗资的生命和金钱。 NAMI报告,严重的精神疾病耗资每年损失的1932亿美元。 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内表示,抑郁症是青少年之间的第三个疾病和残疾的主要原因,并且自杀是15到19之间的青少年死亡的第三个主要原因。“我们应该做更多的研究,”Lipska说。 “它需要更好资助。 和精神疾病需要保险。 有一个关于它的禁忌,我们害怕做一个大的臭味。 如果我们了解它,就像我们理解癌症一样,我们就可以提出一种处理障碍和治愈的机制。“ Lipska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