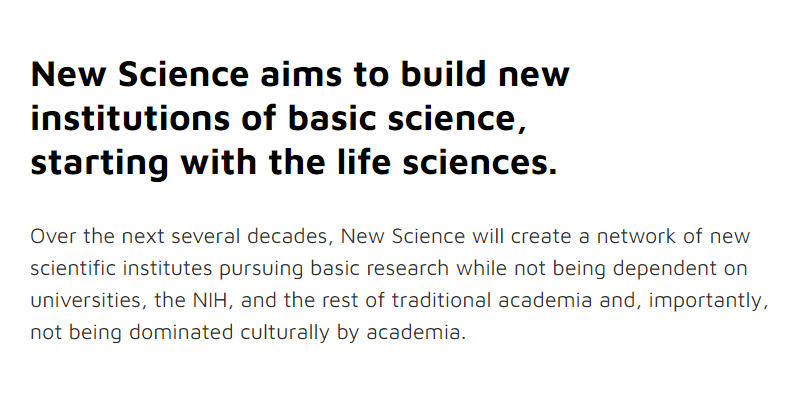新科学,科学硅谷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新科学将创建一个新的科学机构网络,追求基础研究,同时没有依赖大学,NIH和其他传统学术界,重要的是,没有由学术界占主导地位。
我们的目标不是取代大学,而是制定互补机构,并为现有的机构提供许多需要的“竞争压力”,并防止他们进一步的骨化。新科学将对科学进行科学,硅谷为企业家精神做了什么。
新科学是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研究非营利组织,待定了501C3状态。董事会由Alexey Guzey,Mark Lutter和Adam Marblestone组成。通过Tessa Alexanian,Tyler Cowen,Andrew Gelman,Channabasavaiah Gurumurthy,Konrad Kording和Tony Kulesa建议新的科学。
在2022年的夏天,新科学将在波士顿举办一个人的研究奖学金,为年轻的生活科学家们,在此期间将收集初步数据,以便为他们的雄心勃勃的想法。这是由冷泉港实验室的启发,该实验室始于领先的分子生物学家来到夏天来悬挂并在随机项目上工作,最终享有8名诺贝尔奖获奖者。
该计划是逐步提高项目资助的项目范围和新科学资助的人数,最终达到了在传统学术界以外的整个实验室,然后是整个新的科学机构网络。
在此过程中,我们打算能够在传统学术界工作的研究人员能够在学术界工作的问题上工作,并通过吸引那些吸引那些人来增加努力推动科学前沿的绝对数量谁想追求基础研究,但没有选择在传统学术界追求职业生涯。
准备夏天的夏季研究员奖学金,为年轻的生活科学家们在探索性研究项目上工作,他们在2022年否则无法在另外工作
继续挖掘科学工作的结构究竟是如何发布该研究的结果
如果您' d想了解更多关于新的科学'下一个步骤和/或对以下内容感兴趣:
参加上面提到的夏季团契,作为学生,导师,组织者或其他
并让我们在一段时间让科学推进一名年轻科学家,而不是一次葬礼。
[T]他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隐藏起来,因为它们只能通过不会发生的事情来衡量。没有人跟踪NSF或NIH的资金是否拒绝的研究计划的缺乏的发现或发明的缺乏而不是资助的那些。没有人分析系统的效率。我们假设它有效,因为许多人发表了许多论文,有些人设法做出一些发现。
我最近和生物学的博士教演员交谈,并问他对学术界完全破碎的硅谷的普通观点。他告诉我,当然这就是硅谷的人会认为是什么,这是完全错误的。是的,他说,学术界有其存在的问题,但它确实给了许多辉煌的人有机会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研究,如果你努力努力,就有有难以解决的学术界的明显限制。总的来说,他说,学术界大多是工作。
尽管有任期,他的高级学校PI被迫在40年代后期关闭他们的实验室
他的第一个Postdoc PI无法为真正感兴趣的问题获得资金,并且不得不转向更有趣但“更热”的研究领域,更多的是NIH资金
他30岁的他自己正在进行第二次邮政编程,并正在研究一个项目,他考虑了渐进的项目,因为如果他没有充分聘用以作为助理教授被雇用的足够的出版物,他将无法找到工作,如果他是助理教授没有受到限制,他将一直在研究完全不同的东西
多年来,像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发生了几次,这就是亲自劝我的事情,即学术界在患有非常严重的问题。
虽然学术界确实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但是至少有一种自由和追求你相信的基础研究,而且对某种模型研究员来说是非常严格的,偏离偏离,谁是原始的,但不是太称了(到得到同行评审委员会资助的);雄心勃勃但不是理想主义(在某些期刊上发表很多);并且努力工作但在他们的个性特征中并不不平衡(同时管理实验室,雇用良好,以及除了进行研究之外还与资金景观保持良好)。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全职工作,而在拥有正常的生活和家庭的同时,在学术界的起来管理咨询结构中,您就没有建立了您的职业道路。或者,相反,您根本无法开始建立一个实验室,该实验室将致力于在不等待的情况下追求研究计划,直到您在30(在最佳情况下)或35或40处。
借着乔治教堂的一个例子:乔治教堂是哈佛大学的科学家,他们是基因测序的先驱之一,也可能是最着名的合成生物学家。
他养父母是一名医生。他去了一个花哨的高中,在那里他开始讨论科学,然后到杜克大学,在那里他在整个本科学院进行了研究。他被录取到毕业生。他有一切都是为了他(嗯...除了诵读诵读和疯狂脑梗)。
在毕业生学校,教堂每周在实验室和出版论文中工作105小时......然后公爵踢了他,为教会提供这封信。原因?他停止去了一个课程,即他在本科生在本科生,一塌糊涂的课程中,杜克的官僚决定踢他。幸运的是教会,他重新申请了哈佛大学,哈佛大学重新承认了他。当然,他成为我们时间最受欢迎的科学家之一。
教会教会在杜克拥有超过5年的时间,无法阻止公爵的官僚踢他。公爵显然不关心20岁教堂正在做的任何科学 - 尽管他基本上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家,决定了他自己的研究计划 - 他们可能认为他只是一个才华横溢但懒惰而傲慢的毕业生谁需要讲授课程。教堂明显辉煌,完成了他的一切,仍然可以努力阻止他被踢出毕业生。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我们的科学机构能够赋予年轻的教堂,而不是试图毁灭自己的生活。
虽然激励和正式的结构很重要,但是,如果您想到它,例如,公司则往往会相似地构建。他们都拥有员工,经理,经理管理者,人力资源部门等。如果我们采取两家拥有相同的组织和激励结构的公司,其中一些都将成为条纹和Facebook,其中一些人将获得电视显示利润(MR)。差异在于文化中的人们,详细说明并不清晰清晰,并抵制被明确地写下和编纂,在不同的规则的不同执行中。各国可以说类似的事情。您可以复制美国政府的所有法律和结构,这绝对不会导致您所在国家/地区突然(或以前)突然(或以前)的GDP。关于研究组织可以说类似的事情。
在写下NIH的情况下,我注意到了一个类似的恐怖模式的难以辨别的模式:看着获得资助的研究提案的标题以及获得资助的人的信息 - 但只在某种程度上 - 你永远不会学习例如,通过查看NIH的程序和统计数据,例如,这些拨款的重要部分是由毕业生和博士学位编写的,他们的PI名称盖上他们的PI名字或者实际上追求的项目差异相差从项目州名义上是很多,在NIH和科学家之间的一种不询问 - 不要讲述动态,允许他们在NIH不会正式资助的事情上工作。
在我的脑海里,所有这一切都要对文化的原始结构,并以识别易懂的难以清晰的难以辨认的,引领令人不愿意支持一些宏伟的“看到像国家重建科学机构的计划”。我曾经曾经痴迷于机制设计和激励结构,但我很想相信我们是Bob-Taylor约束的比我们是理想的组织 - 和激励 - 结构 - 基本研究 - 机构受约束。虽然我相信有明确的结构改善 - 就像让真正有才华的人没有博士开始自己的实验室 - 新的科学不太可能试图开展一个计划,比如介绍科学家的UBI,废除学术期刊,并将学者返回到他们的自然卢梭的高尚野蛮人,或这种类型的任何东西。
相反,我相信在组织基本科学研究方式中实现大规模改善的最有希望的方式是开始小,帮助个别科学家,并为更好的世界做出小步骤。
Hhmi Janelia是我在上面提出的积分的指导例子。它是一家独立的研究所,自2006年开业以来,在不到20年的情况下对生物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仅通过慈善资金启动,并明确建模贝尔实验室和剑桥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然而,虽然Janelia已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研究机构之一,并且尽管是明确的设计和构造的,但仍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证明,而构成是生物学的贝尔实验室,在不到20年的情况下它似乎已成为,也许有点不寻常,但大多数是既定的学术界的生长,与其余系统紧密结合。为什么发生这种情况的一个解释的一部分是在Janelia工作的人是来自学术界的科学家,他们预计几年后会返回学术界,这意味着他们在Janelia的成就不是由那些评估的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做某事,而是由既定机构深入了解。
新的科学旨在追求他们性质可以与文化正交和学术界的激励结构的项目。
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他们的职业生涯尚未以学术界的生活完全改变他们的职业生涯。
足够短,以便做出截然不同的成本与学术界的预期严格限制了缺点
使参与者能够学习一吨,并了解其他超级智能年轻的研究人员并对齐导师,从而长期帮助他们,无论他们选择的未来道路如何
长期项目将为推动基础科学的前沿,为今天组织的方式推动基础科学的边境,避免不得不应对他们传统学术CV的内容的人们对科学方式的一定程度的怀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