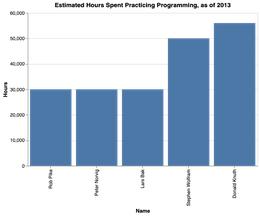我的正念练习使我崩溃
在北卡罗来纳州山区的一个下雪晚上,我在佛教冥想静修的第二天晚上依偎在床上。我精疲力竭,独自躺在我的小木屋里,渴望有营养的睡眠。它没有来。我的身体出奇地焦躁不安,尽管被裹在一堆毯子里,我仍然很冷。我一直在练习的冥想类型是禅那,一种深度的定力状态,据说对佛陀的觉醒是必不可少的。一整天我都专注于呼吸,扫描身体寻找各种感觉。我还有 13 天的时间去工作,目标是体验高度精炼的意识状态——也许还有其他的东西。当我躺在那里在轻快的黑暗中沉思时,我突然感觉到我的内心越来越紧绷。就好像我受到了如此轻柔的伤害。然后很快,压力越来越大,我呼吸急促的断断续续,剧烈地颤抖起来。我是一根被调到超出最高范围的吉他弦。弦弹了出来。一股恐惧刺穿了我的胆量。那是我分开的时候。接下来的四个小时是恐怖、恐慌和偏执的地狱。几乎没有任何想法,只有我的身体在乞求逃离我的皮肤,像一条为生命而战的鱼一样抽搐着。恐惧是一个无底洞。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某件事,一切,都大错特错。有几分钟,我完全不动了。甚至当我重新获得控制权时,我也无法寻求帮助。我不确定我是否真实,或者我小屋的门是否真实,或者它外面的任何人是否真实。我曾在自己的头上打了一拳,只是为了感觉有什么坚固的东西。我无法帮助自己,因为我无法找到自己。我在哪里?我变成了谁?最后,几个小时后,攻击慢慢熄灭,我渐渐离开了。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夜晚。
第二天早上,在煮咖啡的时候,我盯着奶精看了两分钟,整个人都麻木了。几个小时后,我一动不动地站在被风吹过的悬崖上,从右肩上方的某个地方观察自己,就像一辆破车一样停在路肩上。那天下午,我将我的经历传达给了监督大约 40 名禅修者闭关的两位老师。他们都善良、富有同情心、热情好客,建议我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改变我的冥想练习以减轻我的症状。我向他们解释说,问题是我无法停止正念或意识到内在发生的一切我的思想和身体,以及这种意识感觉就像把我窒息而死。在尝试了一天的替代冥想方法之后,我离开了静修所。在 90 分钟的 Lyft 车程到我姐姐在诺克斯维尔的家中,我被压垮和困惑。在那里,我花了一个星期试图在她的地下室康复,看电视真人秀,和我的小侄子在地板上摔跤。一周后,我开车回新奥尔良的家,但不幸的是撤退的影响并没有留下。那天晚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可能听起来很奇特、离奇、精神病和不寻常,但实际上它比许多人想象的更常见和更可预测。随着冥想练习在西方迅速流行,它们带来了一系列不良体验,远远超出了减轻压力、减少焦虑和减轻疼痛的典型好处。几个世纪以来,佛教教义经常探索意识的断裂、破坏和改变状态,但是当这些实践进入西方文化时,对冥想的不利方面的充分理解在过渡过程中丢失了。事实上,今天正念冥想主要用作心理健康问题的标签外治疗,这是一个奇怪而曲折的旅程,这是亚洲佛教徒几个世纪以来为实现解脱而实践的一种技术,从而避免重生。这种品牌重塑主要粉饰了冥想的负面体验,并将其定义为与西方心理健康目标保持一致,创造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静修中心、课程、讲师、顾问和应用程序业务。根据 Marketdata Enterprises 2017 年的一份报告,预计到 2022 年美国冥想市场将增长到 20 亿美元。 作为基于正念的减压 (MBSR) 讲师,我花了四年时间从事冥想教学作为全职工作。作为一名长期的冥想者,我在 10 年的时间里进行了大约 4,000 小时的练习,其中包括 100 多天的静坐静修。我对佛教和世俗的冥想框架都非常了解,读过无数关于这个主题的书籍,并接受过许多著名的西方冥想老师的指导。
在这次闭关之前,我是一位毫不掩饰的正念传道者。我相信冥想使我的生活发生了许多积极的变化。它减少了我的反应,帮助我建立了更好的人际关系并帮助我控制了饮酒。它让我对自己的思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许最重要的是,它给了我一门手艺和一个框架,通过它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目标。在撤退后的几个月里,我遭受了治疗师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我经常经历不自主的抽搐和简单的任务,比如做饭引起的惊恐发作。我有时会被自己的身体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有时无法将自己与周围环境区分开来。最微小的逆境时刻,例如交通堵塞,感觉就像死亡。我的身体是一个酷刑室,让我充满恐慌、恐惧、绝望和痛苦的感觉。我什至随身带着一个绿色的软球,我拼命抓住它以防止分离性发作,而且我很少在口袋里没有 Xanax 的情况下离开房子。这个地形很新鲜。我以前从未经历过精神病发作,除了偶尔出现轻度焦虑和抑郁之外,也没有精神疾病史。在撤退之前,我没有任何重大创伤的病史。当我在冥想引起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中度过生活时,我也感到被出卖了。虽然我粗略地提到了冥想期间的困难,但主要的框架是积极的。我清楚地记得一位资深老师回答了一个学生应该打坐多少的问题。事实上,当我报告早先的闭关时抽搐和颤抖时,老师们从未表示过担忧。我遇到的大多数关于负面体验主题的文献都将它们描述为一个人正在走向觉醒状态的阶段或迹象。在我看来,从来没有理由停止追求冥想。十多年来,我没有遇到任何一位老师描述过任何冥想可能有害或应该停止的情况。所以,我坚持了下来。 Willoughby Britton 是布朗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和副教授。她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研究冥想负面影响的专家。
在我灾难性的撤退前九个月,我偶然遇到了她。她正在洛杉矶主持一个名为“Do No Harm”的会议,讨论冥想的不利影响。我在那里是因为这是我完成基于正念减压的教学认证的最便宜的方式,并且当时对该主题的兴趣很小。参加者大约 300 人,是美国正念运动的知识分子:治疗师、冥想老师、神经科学家和医生。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非常突出。他们的职业生涯是将正念冥想作为一门心灵科学进行宣传,与西方关于心理健康的思想完全兼容,如果不是更胜一筹。 Britton 谈话的重点是她与丈夫 Jared Lindahl 于 2017 年共同发表的一篇论文的结果,该论文称为“沉思体验的多样性 1”。在其中,他们研究了 60 位西方佛教冥想者的痛苦和功能受损的冥想体验。他们在研究中记录了 59 种不利影响,包括无意识的抽搐、恐慌、焦虑、分离和知觉过敏——这与将正念冥想作为解决我们所有困境的灵丹妙药的主流品牌相去甚远。他们的信息并没有受到特别的欢迎。为什么会这样?房间里许多人的生计——包括我的——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正念将成为现代不满情绪的救星。 Britton 和她的共同主持人 Lindahl 和治疗师 David Treleaven 正在打破泡沫,让一些出席的人感到沮丧。我之前参加过的几乎每一次正念静修、活动、谈话或讨论都涉及神经科学、心理学、证词、轶事、诗歌和冥想的融合,所有这些都被拼凑在一起并综合起来,以加强正念作为一种治疗方法的卓越性.但是布里顿和她的共同主持人将大部分科学视为草率,指出当前研究体系中存在相当大的误解和弱点,质疑世俗的正念计划是否真的是世俗的,并且通常会扼杀很多感觉良好的氛围期待在这样的聚会中吸收。有一次,一位著名的正念书籍作者站了起来,对布里顿的工作发表了大约 10 分钟的反驳。他的语气变得越来越居高临下,他漫无目的地宣传自己的会议,并哀叹是我们错误的自我意识导致了大规模的人类苦难和气候变化。作者的独白以他引用鲁米的诗“宾馆”作为结束,作为人们如何处理令人痛苦的冥想体验的典范。禅修老师经常使用的这首诗表明,我们应该欢迎我们所有的情绪、感受、经历——无论好坏——就像我们欢迎客人到我们家一样。
在他爆发之前,布里顿曾描述过冥想者失去了感觉自己身体的能力,失去了对孩子的情感,并且在一个特别麻烦的场合,失去了识别红灯含义的能力。 “在让外面的任何人或任何东西进入之前,先从钥匙孔看一下可能是明智的,”她反驳道。我在洛杉矶的最后一天骑着赛格威,购买合法的大麻,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校园池塘里盯着一些海龟。我对布里顿的信息感到不安但又很感兴趣。她描述的一些不利经历与我面临的挑战相似。但是,在这一点上,我已经进行了十年的密集正念冥想练习。我太深了无法出去。我为什么开始冥想?简短的回答是,2009 年,我在法国区的一家酒吧里为一些什锦饭、一个热吻和一个我不喜欢的流浪评论开始了拳头。几个小时后,我用拳头打破了窗户,把衬衫放错了地方,喝了大约 16 瓶 Miller High Life,晚上结束了。我的女朋友不高兴。我不高兴。有些事情必须改变。那个时间点代表了我在过去十年中与愤怒和其他负面情绪进行的持续斗争。我喝多了。我偶尔会砸坏卡住的打印机。我与女性的关系不稳定。我的思绪不受控制地飘荡着。我正在 20 多岁的时候做一些在 19 岁时感觉还可以的事情,但不再感觉良好。我想要一个更平静、平静的心,所以我找到了一个禅宗中心,开始每周一次的冥想练习。效果是深远而直接的。事后一切都变慢了。那里有和平、空间和幸福。这就像一种药物。我立即想要更多。 2011 年,我在 SN Goenka 的内观传统中参加了我的第一次冥想静修。我在沉默中度过了十天,每天花 10 到 12 个小时专注于自己的呼吸和身体。这很折磨人,但在闭关结束时,我有了改变人生的经历。
在我的房间里独自冥想时,我全身抽搐,并以完美的平静观察到悲伤、绝望和可怕的痛苦从我的肠子里冒出来,进入我的胸膛,然后从我的嘴里冒出来。天顶之际,一连串的影像从我闭着的眼睛的黑暗中浮现出来,我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同时泪流满面。就好像我清除了一生的负面情绪。之后,我在没有不满的状态下漂流了几个月。我也开始体验那些感觉陌生的记忆——就像它们不是我的——可以观察到自己在睡觉,并且能够通过简单地将注意力集中在上面来平息哪怕是最轻微的激动。我觉得我有一种超能力。我的酒量减少了,我的愤怒得到了缓和,我能够在工作中集中精力在更高的水平上。几个月后,我结束了一段有害的关系,并很快结交了一批新朋友。我在许多方向上蓬勃发展,并为此进行了冥想。一年后,我又回来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参加了全国各地的冥想静修,阅读了大量关于佛教的书籍,甚至从新奥尔良搬到旧金山湾区来深化我的冥想练习。我经常开玩笑说,唯一阻止我成为和尚的就是不得不缝制自己的长袍。但是,这大多是事实。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完全相信佛教的许多教义,尤其是所有痛苦都是渴求或欲望的产物。对我来说,不言而喻,如果我能培养一种无反应的状态,我就可以没有不满。许多冥想老师的论点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冥想是一种完全世俗的努力,可以在与宗教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进行。他们认为,这本质上是对头脑的锻炼。然而,在我实践六七年后,我取得的任何进展都逐渐消失了。我的身体越来越烦躁,开始用药物和酒精自我治疗。回想起来,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我第一次经历了分离性体验,其中自我意识的元素以某种方式分离,损害了我的运作能力。
似乎我冥想得越多,感觉就越糟。我迫切地想找到一个框架来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并在冥想书籍中寻找关于长时间痛苦的参考。在我的书架上,我发现了一本我拥有一段时间但从未读过的书。它被称为“掌握佛陀的核心教义”。封面图片是一位坐着的禅修者的剪影,粉红色的波浪线向四面八方射出。作者是阿拉巴马州的一名急诊室医生,他宣称自己已经完全清醒了。他称自己为阿罗汉·丹尼尔·英格拉姆。完全合成英格拉姆 620 页的大部头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会坚持对我来说最突出的部分。英格拉姆这本书的核心是一个佛教模型,它描述了 16 个阶段的冥想进程,每个阶段都有一组一致的特征。其中两个阶段让我眼前一亮。一种是“升起与消逝”状态,有时也称为 A&P。根据英格拉姆的说法,这种状态包括“强烈的身体震动和释放,意识的爆炸,如烟花汇演或龙卷风,视觉,尤其是强大的精细漩涡。 “电”振动在脊柱和/或耳朵之间向上或向下爆炸。”英格拉姆接着说,在 A&P 之后,冥想者已经跨越了一个门槛或“不归路”。他们现在注定要陷入他所描述的“黑夜”,一系列阶段,如解体、痛苦、厌恶和恐惧。根据英格拉姆的说法,人们必须通过这些可怕的经历继续冥想,直到达到更深的觉醒状态。他明确表示,停止的后果是严重的。 “如果他们在暗夜阶段(或 A&P 之后的任何时间)放弃,暗夜的品质几乎肯定会继续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困扰他们,削弱他们的精力和动力,甚至可能会引起感情不安、抑郁、偏执,甚至自杀的念头。因此,非常非常鼓励明智的禅修者尽管有潜在的困难,但仍要坚持修行,以免陷入这些阶段。”尽管看起来很奇怪,但无法描述这种诊断对我的缓解程度。英格拉姆的书以一种没有冥想老师或治疗师做过的方式验证了我的经历。有了这个诊断,我目前状况的结果对我来说很清楚。我醒了一半。我必须到那里去,否则我会继续受苦。我已经没有选择了。
我第二次遇到威洛比布里顿是在我灾难性的冥想静修三周后。我急切地寻求帮助。我的身体一直处于生理痛苦中。我一直在努力与我的妻子进行眼神交流。驾驶汽车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我的左肩感觉通电,无法控制地抽搐。我很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 Britton 经营着一个名为 Cheetah House 的组织,她通过该组织为陷入困境的冥想者提供咨询。她自己也有过不好的经历。我们是通过 Skype 认识的。当我向她描述我的症状时,我很沮丧,她仔细地做了笔记。然后,布里顿告诉了我一件激怒我的事情。这让我想敲掉某人的牙齿。她说,正念冥想界的许多领军人物都有和我一样的经历,但他们只是不谈论它们。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什么他妈的人,能经历这种事,居然不警告别人!”我大喊。当我这样做时,我用右手疯狂地做着手势,就像我在空手道切开面前的空气一样。这是多年来我第一次放弃我的佛教伪装,让自己真正生气。我告诉布里顿在撤退和之前几个月发生的一切。我解释说,受 Ingram 的书和类似文本的启发,我每天冥想两个小时,如果不是更长的话。我描述了无数次我所有的思想如何瓦解,我如何长时间沐浴在深沉的、非概念性的幸福状态中。我认为觉醒就在眼前,现在感到破碎和背叛,我说。布里顿向我解释说,我的冥想练习,特别是对身体感觉的持续关注,可能增加了大脑中称为岛叶皮层的部分的激活和大小。 “脑岛皮层的激活与全身性觉醒有关,”她说。 “如果你不断增强你的身体意识,在某一点上它会变得过多,身体会试图通过关闭边缘系统来限制过度唤醒。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在强烈的恐惧和分离之间摇摆不定。”她建议我尝试一种名为躯体体验的创伤疗法,并邀请我加入她为经历过急性痛苦的冥想者提供的支持小组。他们的故事令人信服,但令人心碎:源源不断的人使用冥想来寻求摆脱痛苦,而不是寻找更大的痛苦。
虽然有些人是无数冥想静修的老手,但其他人只是涉足冥想应用程序。一名女性,一名临床心理健康工作者,在她的医生建议她参加为期 10 天的冥想静修后,最终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许多参与者在使用 Sam Harris 流行的 Waking Up 应用程序后出现了问题。人们可能想知道这些受伤的冥想者是否有触发这些体验的先决条件。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一发现类似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