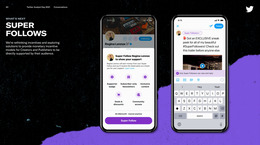你的注意力没有崩溃。它被偷了。社交媒体和现代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正在摧毁我们集中注意力的能力。我们需要趁现在还可以的时候收回我们的思想。
社交媒体和现代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正在摧毁我们集中注意力的能力。我们需要趁现在还可以的时候收回我们的思想
我的教子亚当九岁时,对猫王产生了短暂但异常强烈的痴迷。他开始用最高嗓门唱监狱摇滚乐,伴随着国王自己低沉的哼唱和骨盆的晃动。有一天,当我给他盖好被子时,他非常认真地看着我,问道:“约翰,有一天你能带我去Graceland吗?”我不假思索地同意了。直到一切都出了问题,我才重新考虑。
十年后,亚当迷路了。他15岁时辍学,醒着的时候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屏幕之间空白地交替——YouTube、WhatsApp和色情的模糊画面。(为了保护他的隐私,我改变了他的名字和一些小细节。)他似乎在以Snapchat的速度呼呼作响,任何静止或严肃的事情都无法在他的头脑中获得任何牵引力。在亚当长大成人的十年里,这种分裂似乎发生在我们许多人身上。我们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在崩溃。我刚满40岁,无论我们这一代人聚集在哪里,我们都会哀叹自己失去了集中注意力的能力。我仍然读了很多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感觉越来越像是在爬下自动扶梯。一天晚上,当我们躺在沙发上,每个人都盯着自己不停尖叫的屏幕时,我看着他,感到一阵低沉的恐惧。“亚当,”我轻声说,“我们去格雷斯兰吧。”我提醒他我许下的诺言。我可以看出,打破这种麻木的习惯的想法点燃了他的内心,但我告诉他,如果我们去的话,他必须坚持一个条件。白天他不得不关掉手机。他发誓他会的。
当你到达Graceland的大门时,不再有一个人的工作是带你四处看看。你被递给一台iPad,你戴上小耳塞,iPad告诉你该怎么做——左转;右转向前走。在每个房间里,屏幕上都会出现一张你所在位置的照片,而叙述者会对其进行描述。所以当我们走来走去时,周围都是面无人色的人,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看着他们的屏幕。当我们走路时,我感到越来越紧张。当我们来到丛林房间——猫王最喜欢的宅邸——时,一个站在我旁边的中年男子转过身来对他的妻子说了些什么。在我们面前,我可以看到猫王买来的巨大的假植物,它们把这个房间变成了他自己的人造丛林。“亲爱的,”他说,“这太棒了。看。”他朝着她的方向挥舞着iPad,开始用手指在上面移动。“如果你向左滑动,你可以看到左边的丛林房间。如果你向右滑动,你可以看到右边的丛林房间。”
如果你在工作时阅读文本,你就失去了时间,也失去了事后重新聚焦所需的时间,这是非常多的
他的妻子盯着他,微笑着,开始在自己的iPad上滑动。我身体前倾。“但是,先生,”我说,“有一种老式的刷卡方式,你可以做。它叫转动你的头。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在丛林房间里。你可以看到它未经处理。在这里。看。”我挥了挥手,假绿叶沙沙作响。他们的眼睛又回到了屏幕上。“看!”我说。“你没看到吗?我们真的在那里。不需要你的屏幕。我们在丛林房间。”他们匆匆离去。我转向亚当,准备对这一切开怀大笑——但他在一个角落里,把手机夹在夹克下面,在Snapchat中快速浏览。
在旅行的每个阶段,他都违背了诺言。两周前,当飞机首次在新奥尔良着陆时,我们还在座位上时,他拿出了手机。“你答应过不使用它的,”我说。他回答说:“我的意思是我不会打电话。显然,我不能使用Snapchat和短信。”他说这话时诚实得令人困惑,好像我让他屏住呼吸10天似的。在丛林房间里,我突然啪的一声,试图把他的手机从他手里夺过来,他跺着脚走开了。那天晚上,我发现他在心碎的酒店里,坐在一个游泳池(形状像一把巨大的吉他)旁边,看起来很悲伤。当我和他坐在一起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对他的愤怒和我对自己的愤怒是一样的。他无法集中注意力,我也觉得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失去了在场的能力,我讨厌它。“我知道有什么不对劲,”亚当说,手里紧紧握着手机。“但我不知道如何修复它。”然后他又开始发短信了。
那时我意识到我需要了解他和我们中的很多人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一刻是一段旅程的开始,改变了我对注意力的看法。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走遍了世界各地,从迈阿密到莫斯科再到墨尔本,采访了世界上顶尖的聚焦专家。我所学到的让我相信,我们现在面对的不仅仅是对注意力的正常焦虑,这是每一代人随着年龄增长所经历的那种焦虑。我们生活在一场严重的注意力危机中——这场危机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有着巨大的影响。我了解到,有十二个因素被证明会降低人们的注意力,其中许多因素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在上升,有时甚至是急剧上升。
我去俄勒冈州波特兰采访了乔尔·尼格教授,他是世界上儿童注意力问题的顶尖专家之一。他告诉我,我们需要问一下,我们现在是否正在发展一种“注意力致病文化”——一种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更难持续和深入关注的环境。当我问他,如果他掌管我们的文化,他真的想破坏人们的注意力,他会怎么做,他说:“可能是我们的社会在做什么。”法国著名科学家芭芭拉·德梅内克斯(Barbara Demeneix)教授曾研究过一些可能扰乱注意力的关键因素,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们今天不可能拥有正常的大脑。”我们可以看到周围的影响。一项针对大学生的小型研究发现,他们现在只专注于一项任务65秒。另一项针对上班族的研究发现,他们只关注平均三分钟。这不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变得意志薄弱。你的注意力没有崩溃。它被偷了。
当我第一次从Graceland回来的时候,我认为我的注意力正在衰退,因为我作为一个个体不够强大,因为我被手机接管了。我陷入了消极思想的漩涡,责备自己。我会说——你很软弱,你很懒,你不够自律。我认为解决办法很明显:更加自律,把手机扔掉。于是我上网,在科德角的普罗文斯镇海滩边订了一个小房间。我胜利地向大家宣布——我将在那里待三个月,没有智能手机,也没有可以上网的电脑。我完了。我厌倦了被束缚。我知道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非常幸运,而且从我以前的书中得到了钱。我知道这不是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我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这么做,我可能会失去我深入思考能力的一些关键方面。我还希望,如果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剥去一段时间,我可能会开始瞥见我们都能以更可持续的方式做出的改变。
在我没有网络的第一周,我在减压的迷雾中蹒跚而行。Provincetown是一个同性恋度假小镇,在美国同性伴侣比例最高。我吃纸杯蛋糕,看书,和陌生人聊天,唱歌。一切都急剧放缓。通常情况下,我每小时左右都会关注一次新闻,获取一些令人焦虑的事实,并试图把它们混为一谈。相反,我只是每天看一次实体报纸。每隔几个小时,我就会感觉到一种陌生的感觉在我内心汩汩作响,我会问自己:那是什么?啊,是的。平静的
后来,当我采访专家并研究他们的研究时,我意识到我的注意力从第一天开始恢复的原因有很多。麻省理工学院的神经科学家厄尔·米勒教授向我解释了一个问题。他说“你的大脑一次只能产生一到两个想法”。就这样。“我们非常非常专一。”我们的“认知能力非常有限”。但我们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错觉。现在,普通青少年相信他们可以同时关注六种形式的媒体。当神经科学家对此进行研究时,他们发现当人们认为他们同时在做几件事时,他们实际上是在玩杂耍。“他们在来回切换。他们没有注意到这种切换,因为他们的大脑会将其记录下来,以提供一种无缝的意识体验,但他们实际上在做的是时刻切换和重新配置他们的大脑,任务到任务——[而且]这是有代价的。”想象一下,比方说,你正在做报税表,你收到一条短信,你看了看——只看了一眼,花了三秒钟——然后你回到报税表。在那一刻,“当你的大脑从一项任务转到另一项任务时,它必须重新配置,”他说。你必须记住你以前做过什么,你必须记住你是怎么想的。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证据表明,“你的表现下降。你变慢了。这一切都是因为切换。”
这被称为“转换成本效应”。这意味着,如果你在努力工作的同时检查文本,你不仅会损失你花在阅读文本上的一点点时间——你也会损失事后重新聚焦所需的时间,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例如,卡内基梅隆大学人机交互实验室的一项研究让136名学生参加了测试。他们中的一些人必须关掉手机,其他人则打开手机并收到断断续续的短信。收到短信的学生平均表现差20%。在我看来,几乎所有人目前都在失去20%的脑力,几乎一直如此。米勒告诉我,因此我们现在生活在“认知退化的完美风暴”中。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第一次在Provincetown一次只做一件事,没有被打断。我生活在大脑实际能处理的范围内。我觉得自己的注意力在与日俱增,但有一天,我突然遭遇了挫折。我走在海滩上,每隔几步我就会看到孟菲斯以来一直在抓我的东西。人们似乎只是把Provincetown当作自拍的背景,很少抬头看海洋或彼此。只是这一次,我感到的痒不是大喊:你在浪费生命,把该死的电话放下。就是喊:把电话给我!矿这么长时间以来,我每天每隔几个小时就会收到网络发出的微弱而持续的信号,以及一点点的喜欢和评论,它们说:我看到你了。你很重要。现在他们走了。西蒙娜·德·波伏娃说,当她成为一名无神论者时,感觉世界陷入了沉默。失去网络的感觉就是这样。在社交媒体的修辞热过后,普通的社交互动似乎令人愉悦,但数量很少。没有正常的社交互动会让你心潮澎湃。
我意识到,要治愈我的注意力,仅仅消除干扰是不够的。这让你一开始感觉很好,但随后它会在所有噪音都消失的地方创造一个真空。我意识到我必须填补真空。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开始思考我多年前学到的心理学领域——流动状态科学。几乎每个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会在某个时刻经历一种流动状态。当你在做一些对你有意义的事情,你真的投入其中,时间流逝,你的自我似乎消失了,你发现自己深深地、毫不费力地集中注意力。流是人类能给予的最深层的关注。但是我们怎么去那里呢?
后来,我在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采访了米哈利·齐克森特米哈利教授,他是第一位研究流动状态并对其进行了40多年研究的科学家。从他的研究中,我了解到有三个关键因素是你需要进入流程。首先,你需要选择一个目标。“心流”将你所有的精神能量都集中在一个方向上。其次,这个目标需要对你有意义——你不能流入一个你不在乎的目标。第三,如果你所做的事情是在你能力的边缘——比如说,如果你正在攀岩的岩石比你上一次攀岩的岩石略高、略硬,这会有所帮助。所以每天早上,我都开始写作——一种不同于我早期作品的写作方式,一种让我筋疲力尽的写作方式。几天之内,我开始流连忘返,几个小时的专注都会过去,而不会让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我觉得自己像十几岁时那样专注于不费吹灰之力的伸展运动。我担心我的大脑会崩溃。当我意识到在适当的情况下,它的全部力量可以恢复时,我如释重负地哭了起来。
每天结束时,我都会坐在海滩上,看着光线慢慢地改变。好望角上的灯光与我去过的任何地方的灯光都不一样,在普罗旺斯镇,我能比我生命中的任何时候都看得更清楚——我自己的思想、我自己的目标、我自己的梦想。我生活在光明中。所以当我离开海滨别墅回到超链接世界的时候,我开始相信我已经破解了注意力的密码。我回到这个世界,决心把我学到的东西融入日常生活。当我乘渡轮回到波士顿藏匿它们的地方,与手机和笔记本电脑重聚时,它们看起来很陌生,很疏远。但不到几个月,我的屏幕时间又回到了每天四个小时,我的注意力又开始分散。
在莫斯科,前谷歌工程师詹姆斯·威廉姆斯(James Williams)告诉我,我犯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错误。威廉姆斯已成为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关注哲学家。个人禁欲“不是解决办法,因为同样的原因,每周在户外戴两天防毒面具并不是解决污染的办法。它可能会在短时间内阻止某些影响,但它是不可持续的,也不能解决系统性问题。”他说,我们的注意力正在被更广泛社会中的巨大入侵势力深刻改变。他说,解决办法只是调整自己的习惯——比如说,承诺与手机分手——只是“把它推回到个人身上”,而“真正起作用的是环境变化”。
尼格说,如果我们将注意力问题的增加与肥胖率的上升进行比较,这可能有助于我了解发生了什么。50年前,肥胖症几乎没有,但今天它在西方世界流行。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突然变得贪婪或自我放纵。他说:“肥胖不是一种医学流行病,而是一种社会流行病。例如,我们的食物不好,所以人们越来越胖。”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食物供应发生了变化,我们建造了难以行走或骑车的城市,这些环境的变化导致了我们身体的变化。我们集体获得了质量。他说,随着我们注意力的变化,类似的事情可能正在发生。
我了解到,影响我们注意力的因素并非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一开始关注的是科技,但事实上原因非常广泛——从我们吃的食物到我们呼吸的空气,从我们工作的时间到我们不再睡觉的时间。其中包括许多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从我们如何剥夺孩子的游戏权利,到我们的学校如何通过考试剥夺学习的意义。我开始相信,我们需要在两个层面上应对这种不断侵犯我们注意力的行为。第一个是个人。我们可以在个人层面做出各种各样的改变来保护我们的注意力。我想说的是,通过做大部分这些,我的注意力提高了大约20%。但我们必须与人平起平坐。这些改变只会让你走到这一步。此时此刻,我们好像整天都在被人往身上倒瘙痒粉,倒瘙痒粉的人说:“你可能想学着冥想。那样你就不会抓那么多东西了。”冥想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但我们实际上需要阻止那些向我们身上泼瘙痒粉的人。我们需要团结起来,对抗那些窃取我们注意力的力量,并将其夺回。
这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我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在很多地方都在实践这一点。举一个例子:有强有力的科学证据表明压力和疲惫会破坏你的注意力。如今,大约35%的员工觉得他们永远无法关掉手机,因为他们的老板可能会在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时候给他们发电子邮件。在法国,普通工人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并向他们的政府施压要求改变——所以现在,他们有了合法的“断开连接的权利”。很简单。你有权确定工作时间,你有权在工作时间之外不被雇主联系。违反规定的公司将被处以巨额罚款。有很多像这样的潜在集体变化可以恢复我们的部分注意力。例如,我们可以迫使社交媒体公司放弃他们目前的商业模式,这种模式是专门为侵入我们的注意力而设计的,目的是让我们不断滚动。这些网站还有其他的工作方式——可以治愈我们的注意力,而不是攻击它。
一些科学家说,这些对注意力的担忧是一种道德恐慌,类似于过去对漫画书或说唱音乐的焦虑,而且证据不可靠。其他科学家说,证据很充分,这些焦虑就像20世纪70年代肥胖症流行或气候危机的早期预警。我认为,鉴于这种不确定性,我们不能等待完美的证据。我们必须根据对风险的合理评估采取行动。如果人们对我们注意力的影响提出警告,结果证明是错误的,而我们仍然按照他们的建议行事,那么代价会是什么?我们将减少被老板骚扰的时间,我们也将减少被技术跟踪和操纵的时间——以及在任何情况下都值得追求的其他许多生活改善。但如果他们证明是对的,而我们不按他们说的做,代价是什么?正如前谷歌工程师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告诉我的那样,当我们面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类的重大集体危机时,我们将降低人类的等级,剥夺我们的注意力。
但除非我们为之奋斗,否则这些变化都不会发生。正如女权运动夺回了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权利(今天仍然必须为之奋斗),我相信我们现在需要一场关注运动来夺回我们的思想。我认为我们需要紧急行动,因为这可能像气候危机或肥胖危机一样——我们等待的时间越长,它就会变得越难。我们的注意力退化得越多,就越难调动个人和政治能量来对付窃取我们注意力的力量。它需要的第一步是我们意识的转变。我们需要停止自责,或者只要求雇主和科技公司做出微小的调整。我们拥有自己的思想——我们可以一起把它们从窃取它们的势力手中夺回。
以上内容摘自约翰·哈里(Johann Hari)于1月6日出版的《偷来的焦点:为什么你不能注意》(Sleet Focus:Why You Can Not Attention)。支持守护者和观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