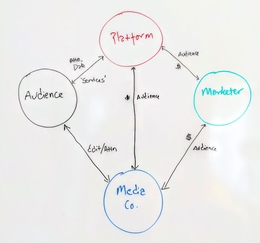社交媒体与话语的终结
一群思想家-大多是拥有著名学位的作家和有写作诀窍的学者-决定了话语。他们告诉别人该怎么想,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告诉了没洗过澡的群众最近自己在想什么。这些披露是非常严肃的,即使他们倾向于漫无边际,语无伦次,或显而易见。在那里,受过教育的人和那些希望被视为受过教育的人会挑选他们希望与之结盟的观点。正是通过这个过程,政治被创造、提炼和重提。(事实上,“Overton Window”这个短语就是由他们普及的。)。这是参与公共领域意味着什么的一部分。
我过去常常被非常严肃地告知,阅读主要报纸的观点版面是一种陶冶情操的活动。
我解释这一点,部分是因为开玩笑,但部分是因为我属于最后一代记得意见人士年龄的人。我过去常常被非常严肃地告知,阅读主要报纸的观点版面是一种陶冶情操的活动。但是当我25岁左右的时候,像“思考”这样的词已经是以自以为是的阶层为代价的笑话了。
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博客的兴起有关。与报道相比,写评论文章更便宜,速度也更快,而且任何人都可以创建博客。这在媒体中成为一种更广泛的趋势,这要归功于Craigslist以及后来吞噬广告市场的谷歌和Facebook施加的经济压力。写事实需要工作,而且工作必须付出代价。另一方面,观点是廉价的。每个人都有一个。
这是一个很好的内容生成解决方案,特别是在社交媒体起飞的情况下。社交媒体和观点写作是相辅相成的。编辑们根据他们喜欢的推文寻找作家。(我自己的职业生涯就是这样开始的。)。关于这位作家前几天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任何东西,人们很快就写下了观点。社交媒体一窝蜂地涌向任何能激发其想象力的观点写作。偶尔,人们的反应是赞扬的,但最响亮的反应是愤怒。
现在,任何人只要有一部手机和一句动听的话,就可以把一个受膏的意见论者烤成玉米棒。
固执己见的班级的规模一度受到报纸版面实际大小的限制。现在,任何人只要有一部手机和一句动听的话,就可以把一个受膏的意见论者烤成玉米棒。
在某些方面,意见阶层的衰落反映了以教会为代价的民主化、世俗媒体的崛起。启蒙运动后,西方公共生活走向一套世俗机构,其中包括一类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是讲坛。
当社会重塑自己时,这不会因为几本小册子(或者一两个标签)而发生。就像固执己见的阶级最初使用社交媒体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样,约翰尼斯·古腾伯格(Johannes Gutenberg)的印刷机存在了几个世纪-印刷宗教小册子、布道和圣经-直到它开始破坏宗教对公共生活的垄断。而印刷机只是一幅包括科学革命、宗教冲突、工业化和经济剥削的图画中的一幅。同样,我们目前的文化时刻是在一个背景下发生的,这可以用一只在着火的房子里喝咖啡的卡通狗来最好地描述。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活字印刷术,法国丽贝拉小册子(经常试图取消各种公众人物,尤其是王室成员的尖刻政治小册子)的制作是不可能的,而丽贝拉本人在法国大革命中发挥了不可否认的作用。同样,如果没有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的大规模采用,2020年的抗议活动以及围绕警察和种族的舆论突然转变也不会发生。
需要明确的是,意见人士并没有面临真正的断头台的危险-除了可能是比喻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将继续出版。他们中的一些人会继续赚很多钱!但它们将变得不那么重要-尤其是因为它们将不再设置Overton窗口。
事实上,甚至可能没有奥弗顿的窗户。参与政治生活甚至可能与成为网迷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区别。我不是说事实或逻辑会消失。但我们将不再假装他们在思想的自由市场中说服了其他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将公民生活与“参与思想”、“参与辩论”或娱乐“广泛的政治光谱”混为一谈。但随着意见阶层的垮台,面具被撕下,暴露出的政治很少,但却是相互竞争的信息邪教之间的冲突,这些信息主要通过情绪性而不是理性来传达价值观。任何“公平和不偏不倚”的薄薄外表都不会掩盖这些信息传播的堡垒。
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可怕;大多数互联网狂热分子的行为至少比美国主要政党中的一个(或者甚至两个)更负责任。
本周,“哈珀杂志”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我后来把这封信称为“那封信”。这封信由一些意见人士签名,然后还有J·K·罗琳(J.K.Rowling)出于某种原因(只是开玩笑,我确切知道原因),谴责了正在主导这种文化的“审查”,称其为“对反对观点的容忍,对公众羞辱和排斥的时尚,以及在盲目的道德确定性中解决复杂政策问题的倾向”。
这并不是对他们谴责的文化现象的特别清楚的表述,所以这封信背后的意思和意图是有多种解读的。这一点从一些签字人在Twitter上近乎即时的倒退中可见一斑,他们并不知道所有其他签字人的身份。抽象的“审查”是不好的,抽象的“言论自由”是好的。但是,如果不作进一步的阐述,就很容易同时讨论这两个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封信似乎是关于反对“非自由主义”的。
这封信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它似乎是关于反对“非自由主义”的。这里所说的“自由主义”,就是社会应该以自由、平等、多元的讨论为基础的一般哲学。因此,“非自由主义”是意见论者交替称之为“校园文化”、“取消文化”和“精神错乱”的花哨代名词。
这股非常模糊的反自由势力被韦斯利·杨称为“继任者意识形态”,他的这个词立即被一些保守派评论员采用,比如罗斯·杜特(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信上)和安德鲁·沙利文(他的名字出现在信上)。但这个词似乎只是把水搅浑了,因为他们关心的其实不是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带有宗教复兴标志的早期社会力量。
也许不足为奇的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杜特能够在这个时刻指出美国人所寻求的“精神复兴”的方面,尽管他似乎无法更进一步地观察到这一点。但我怀疑他也感受到了我的感受,就像一个在福音派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人一样:2020年游行和集会中弥漫的灵性魅力的感觉,新皈依者的热情,对道德正义的令人不安的渴望。
马修·伊格莱西亚斯(Matthew Yglesias)(这封信的签字人之一)将这一文化时刻称为“伟大的觉醒”,有点草率地将其与19世纪的宗教复兴相提并论,后者助长了废除奴隶制运动的火上浇油。他没有提到美国历史上的其他觉醒,比如18世纪美国革命的先驱,或者最近的20世纪大帐篷复兴,这些都为布什时代的福音派基督教政治铺平了道路。我们当前的时代主要被这样一种假象所定义,即宗教热情和情感情绪是政治附带的,所有这些都可以而且应该通过理性的话语来解决。这从来都不是真的,但我们至少是假装的。
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不能用旧范式的语言来充分描述-因此,我们听起来都像是试图谈论它的彻头彻尾的白痴。
这第五次大觉醒就是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转变”和马丁·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崩溃”。用圣保罗的话说,“我们不会都睡着,但我们都会改变--转眼间,在最后一声号角响起的那一刻。”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不能用旧范式的语言来充分描述-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听起来都像是试图谈论它的彻头彻尾的白痴。
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谴责“取消文化”的人所使用的各种谬论有关。
首先,“Wokness”(粗略定义为白人至上和父权制弥漫在我们的社会中)与非自由主义正在不断地混为一谈。正如我的朋友、“纽约杂志”编辑伊齐基尔·奎库(Ezekiel Kweku)所说,这既不是源于另一个,也不是必然的。有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在使用所谓的民间辩论的语言时,鼓吹“清醒”,并使用所有的繁琐语言,如“我同意”、“恕我直言”和“暂时扮演魔鬼的代言人”。
然后是关于“取消”意味着什么的斑驳和贝利谬论。有没有人因为受到强烈批评而被取消?还是有人因为收到死亡威胁而被取消了?还是有人只是因为失业才被取消的?想必,如果政客们激起了足够的愤怒,他们就应该丢掉工作。这项规定是否也适用於被正式或非正式指定为民意代表的知名人士?人们应该如何在真正引起愤怒的互联网暴徒和不配成为受害者的互联网暴徒之间划清界限?
但是,这种关于“取消文化”问题的普遍不一致并不完全是反觉醒的评论家的错。他们正在使用手中摇摇欲坠的旧工具,在一个正在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旧工作空间里工作。
尽管谈到了非自由主义和对言论自由的威胁,但激励这封信的真正恐惧在文本本身变得明显起来,就在信中的作者们围绕着一个明显的矛盾转来转去,即支持言论的联盟已经走到一起,要求批评者他妈的闭嘴:“现在听到要求迅速、严厉惩罚被认为违反言论和思想的行为的呼声太常见了。”主张者实际上并不害怕被压制。他们希望在没有一群无名小卒告诉他们自己是多么错误的情况下,占据专栏的几英寸。
尽管所有的借口都是逻辑和辩论,但旧的范式孕育了一个非理性和令人无法理解的不公正的社会。这些观点论者经常传播被揭穿或错误的科学,他们让一场关于气候变化的“辩论”继续存在,而这场辩论几十年来在科学家中从未存在过。他们容忍这种偏执,并将非人化视为一种意见分歧。尽管他们被认为是理性话语的典范,但他们从来都不是特别理性。人们只需要指出伊拉克战争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尽管如此,我还是对未来的日子感到不安。我承认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是一名专业的观点撰稿人,在网上被大刀阔斧地取消了,但实际上,主要是因为我已经过了30岁,同时低头盯着大规模社会变革的桶。但混乱与邪恶不是一回事。尽管恐怖统治可能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发生的,但它之前的制度造成的恐怖要大得多。用马克·吐温的话说:
只要我们记住并考虑一下,就会发现有两个“恐怖统治”:一个是在炽热的激情中杀人,另一个是无情的冷血;一个只持续了几个月,另一个已经持续了一千年;一个造成了一万人的死亡,另一个造成了亿万人的死亡。
对于我那些不安的老人们,我请你们记住,混乱不是邪恶,改变不是错误,冲突不是暴力,相关性也不是人权。一切都变了。虽然你有权对此产生伤害的感觉,但当你的感觉在新的情感市场中迷失时,不要感到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