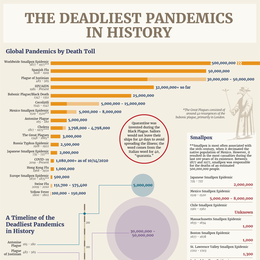结束致命瘟疫的无名英雄
1932年11月下旬,天气寒冷,刮风,两名妇女在正常工作日结束时出发,来到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的街道上。大萧条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全国各地的银行都关门了。该市占主导地位的家具业已经崩溃。珀尔·肯德里克(Pearl Kendrick)和格蕾丝·埃尔德林(Grace Eldering)都是一家国家实验室的细菌学家,他们正在利用自己的时间探访患病儿童,确定他们是否感染了一种潜在的致命疾病。科学家后来回忆说,许多家庭生活在“可怜”的条件下。“我们听了绝望的父亲讲述的悲伤故事,他们找不到工作。我们在煤油灯下收集了百日咳、呕吐、勒死儿童的样本。我们看到了这种疾病可能造成的后果。”
百日咳,又称百日咳,对当今发达国家的大多数父母来说意义不大。但它曾经是家庭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之一。
仅凭症状就很难诊断百日咳。一开始看起来什么都不像:流鼻涕和轻微咳嗽。在婴儿床上观察婴儿的父母可能会注意到她的呼吸暂停,但在胸部稳定上升和下降恢复时会放松。医生也可能错过:只是感冒,没什么好担心的。不过,一到两周后,咳嗽可能会开始剧烈痉挛,速度太快,无法呼吸,直到孩子绝望地喘气,让空气进入喉咙时,尖锐的、被勒死的吠声爆发出来。这种呼啸声使诊断明确无误。
法国里尔巴斯德研究所的研究员卡米尔·洛赫特说:“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你想知道他们如何度过这场危机。”。“它们让人窒息。它们让人窒息。它们变得完全发蓝。它们无法克服咳嗽,你会觉得孩子就要死在你手中。”这种情况可能持续三个月。时至今日,一旦进入百日咳阶段,任何医生都无能为力。
直到20世纪中叶,任何人都无法预防这种疾病。它的传染性如此之强,以至于一个患有百日咳的孩子可能会感染一半的同学和家里所有的兄弟姐妹。20世纪30年代初,百日咳每年导致7500名美国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婴儿和幼儿。幸存者有时会遭受永久性的身体和认知损伤。
所有这些都因为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而改变了。他们被雇来对医疗和环境样本进行日常检测。但对百日咳的研究成了他们的痴迷。他们工作到深夜,一开始几乎没有资金,一名记者称这是一栋“破败不堪的灰泥”建筑。他们受益于自己精心挑选的研究团队的工作,该团队在那个时代具有显著的多样性。他们还赢得了公众的信任和热情。市政府和私人捐赠者挺身而出,支付他们第一次临床试验的费用。医生、护士和普通市民聚集在一起提供帮助。母亲们不仅自愿抽出时间,还自愿将孩子作为实验对象。
资历较好的医生对此深表怀疑。但在过去30年里,其他研究人员多次失败,肯德里克、埃尔德林和他们的团队成功地研制出了第一种安全有效的百日咳疫苗。通过他们的创新,美国乃至全世界因百日咳导致的儿童死亡人数直线下降。
珀尔·肯德里克生于1890年,在纽约州北部长大,她的父亲是卫理公会传教士。她继续在雪城大学获得科学学位,然后在1917年夏天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细菌学。但是,尽管几十年来女性的教育机会一直在扩大,但就业机会并没有随之增加。正如一位医学教育家在1922年所说,传统的态度是“教育能增强女性的魅力、吸引力和家庭幸福感。”有一段时间,肯德里克成为了纽约州北部的一名教师和校长,这是当时受过教育的女性的职业道路,最好是结婚。
公共卫生是少数几个开始寻找受过教育的女性的科学领域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传染病控制在挽救生命方面取得的成功,为改善国内公共卫生的可能性打开了思路。大部分新工作落在了州卫生部身上,他们的实验室需要工作人员将新的诊断测试、疫苗和其他疾病控制工具投入日常使用。受过公共卫生培训的男性倾向于在大学或研究机构寻求声望和高薪的工作。国家实验室提供较低的工资、较低的地位和大部分重复性任务。拥有理科学位的女性似乎非常适合这种死记硬背的工作。
肯德里克在纽约州卫生部经营的一家实验室找到了工作。然后,在1920年,密歇根州富有进取心的州立实验室主任C.C.Young为她提供了一份工作,承诺“让它变得有趣”并“有充分的晋升机会”他信守诺言。1926年,密歇根州卫生部在大急流城开设了一个实验室,肯德里克成为该实验室的第一任主任。1932年,在休假期间,肯德里克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与公共卫生学院获得了科学博士学位。她回到大急流城,目的是研究一种疾病:百日咳。那一年,这座城市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疫情。当肯德里克写信给杨,请求允许他与当地儿科医生合作进行疫苗研究时,他回答说:“如果百日咳让你觉得好笑的话,那就去吧。”
Grace Eldering,出生于1900,在蒙大拿大学上大学,后来在海舍姆的一所学校工作,她在农场长大,在那里长大。和肯德里克一样,她对教书不感兴趣。从1928年开始,她成为了一名志愿者,然后在兰辛的密歇根州立实验室做了一名带薪员工,后来转到大急流城从事百日咳研究。在那里,她和肯德里克开始了他们的终身伴侣关系。
起初,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更快、更准确地诊断疾病,以便尽早隔离传染性患者,并在传染性阶段结束后尽快返回学校或工作岗位。他们选择的武器是咳嗽盘,基本上是一个底部涂有培养基的皮氏培养皿。这两名女性,以及医生、护士和团队中的其他人,会在病人咳嗽时,将打开的盘子拿在几英寸远的地方。该培养皿盖上盖子,然后返回实验室,进入培养箱,将细菌培养成适合分析的菌落。
1932年11月28日,实验室确认了第一批百日咳杆菌标本。四分之一世纪前,这种病原体在比利时首次被发现,但工作人员中没有人见过它。他们不得不将咳嗽盘上的标本与公开发表的报道进行比较。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报告说,这些菌落看起来“光滑、凸起、闪闪发光、珍珠般、几乎透明”,周围环绕着一个苍白的光环,细菌在周围培养基中吞噬了血液。
他们很快将研究扩展到一个雄心勃勃的全市咳嗽平板服务,用于监测和控制百日咳疫情。他们没有像其他科学家在规模小得多的研究中那样使用人类血液作为培养基,而是转而使用羊血,因为它更便宜,而且更容易获得所需的数量。(埃尔德林在牧场长大,知道羊的事。)这是他们实验室进行的许多此类改进之一,使他们得以大幅扩大该市的测试项目。
然后,在1933年1月,也就是他们第一次发现这种病原体七周后,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生产了他们的第一种实验性百日咳疫苗。
研制出任何疾病的疫苗仍然是一项基本的、没有配方的烹饪事业。研究人员必须试验不同的杀死或削弱病原体的方法,以使其足够安全地注射到人类患者体内,但仍然足够强大,以引发对该疾病的持久免疫抵抗。1931年,美国医学会拒绝认可当时可用的任何百日咳疫苗,认为它们对预防“绝对没有影响”,在发病后作为治疗手段“毫无用处”。
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的疫苗由用普通防腐剂杀死的全细胞博德氏杆菌组成,经过纯化、消毒并悬浮在盐水中。其他在他们之前开发过疫苗的人往往忽略了提供有关准备、剂量和其他考虑因素的关键信息,结果是一批疫苗可能与下一批疫苗相差很大。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在每一步都采取了更系统的方法,从最初收集细菌到测试他们的疫苗是否真的保护了儿童。例如,他们在实验过程中了解到,在某个阶段收集的细菌更有可能引发强烈的免疫反应,他们通过将其注射到实验动物和自身中,对疫苗的各种迭代进行了安全性测试。
这两位研究人员之前没有临床试验的经验,这在当时实际上是一门新的科学。但是,测试他们的疫苗是否能安全有效地保护儿童需要一项大规模、受控的现场研究,将一组接种疫苗的受试者与一组类似但未经治疗的对照组进行比较。设计审判必须是肯德里克所说的“我们的午夜工作”的一部分,工作时间过后。
肯德里克后来告诉记者:“我从没想过有什么事我做不了。”。她描述了一段大学时光,在两周的圣诞假期里,她不得不为75名同学组织膳食服务。她的观点是,她对自己承担的每一项任务都一心一意。这种决心甚至在她开车时就体现出来了:埃尔德林的侄女雪莉·雷德兰(Shirley Redland)到达了蒙大拿州,她仍然住在家里的牧场上。她回忆说,肯德里克“脚步沉重,人们最好让开她。”
然而,在与公众打交道时,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都没有给人以大胆或威严的印象。相反,他们总是彬彬有礼、彬彬有礼,而且有点拘谨。对于那个时代经历过性别政治的女性来说,谦逊似乎是必须的。肯德里克回忆说,在大学里,她让男性科学教师通过“尽可能谦逊”的行为来给她提供所需的指导她说,一旦她开始在实验室工作,她就低着头,专注于手头的工作,“让我不必担心我是否得到了和我的朋友约翰一样多的东西,比如说,他在我身边工作,但我很清楚我没有。”
这种自信和谦逊的独特组合帮助他们在开展临床试验时赢得了当地的支持。大急流城也愿意。当时,它作为将医学进步用于拯救生命的领导者而享有自豪的声誉。
在第一轮实地研究中,1592名儿童参加了研究,其中712名为疫苗接种者,880名为未经治疗的对照组。在每一家疫苗接种诊所之后,这两名妇女都在恐惧中等待一个关于不良反应的电话,而不是通常的轻微发烧。肯德里克后来承认:“我大部分时间都感到害怕得要死。”。“那些晚上你就是睡得不好。”但那个紧急电话一直没有接到。相反,数据来了:未治疗组有63例百日咳,其中53例严重。接种疫苗的组只有4例,均为轻度。
起初,医疗机构不相信结果。克利夫兰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一位受人尊敬的流行病学家詹姆斯·杜尔(James Doull)大约在同一时间进行了一项类似的研究,使用了不同的疫苗,但没有显示疫苗的真正益处。当公共卫生领导人要求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流行病学家韦德·汉普顿·弗罗斯特对这两项研究的结果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时,弗罗斯特似乎不愿前往密歇根州。“我非常强烈地怀疑肯德里克小姐的实地研究并没有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以提供真正良好的控制,”他写道。即使是对临床试验专家来说,也很难做到正确,而且“肯德里克小姐的实验很可能是可靠的。”
弗罗斯特最终还是造访了大急流城。在那里,他很快开始欣赏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对严谨科学的承诺。他建议改进他们临床试验的设计,两名女性和他们的团队重新开始工作。他们的新研究将需要更多的工作人员和更频繁的访问,以跟踪患者数年。
这一次,他们得到了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的帮助,她在1936年繁忙的大急流城之旅中参观了实验室。肯德里克后来回忆说,她是为数不多的局外人之一,他们似乎理解她和埃尔德林在做什么。随后,联邦工程进度管理局(federal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很快为额外的工作人员提供了资金。这项新研究吸引了4212名受试者,接种疫苗的受试者再次出现百日咳,其发病率显著低于未接种疫苗的受试者。在纽约州进行的一项疫苗独立临床试验也显示了同样的保护作用。
1944年,美国医学会将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的疫苗添加到推荐免疫接种列表中。结果,仅在那十年里,美国百日咳的发病率就下降了一半以上。死亡人数从1934年百日咳病例高峰期的7518人下降到1970年代初的每年仅10人。在此期间,肯德里克前往其他国家,从墨西哥到俄罗斯,帮助在那里引进疫苗,在拯救儿童生命方面取得了类似的成功。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在儿童生命早期进行如此多不同疫苗注射的“针扎效应”,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当时已经开始研制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联合疫苗,这是一种疫苗的先驱,现在常规保护世界85%的儿童。为了使疫苗在世界各地标准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肯德里克、埃尔德林和玛格丽特·皮特曼还开发了一种必要的方法,用于测试全世界每批全细胞百日咳疫苗的有效性。这些女性将百日咳的预防标准化、可靠、可复制——一句话——科学化,取代了过去没有食谱的大杂烩烹饪。
“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到底做了什么?”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中心的百日咳专家迈克尔·德克问道。“他们坚持认为可以制造出成功的疫苗。他们找到了制造疫苗的方法。他们利用新技术设计了一项临床试验来证明他们的观点。面对来自高层人士的强烈批评,他们证明了他们的结果是正确的。他们基本上为现代百日咳铺平了道路接种疫苗"
这些不朽的成就并没有让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出名,这似乎令人惊讶。两位女性都拥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埃尔德林于1942年获得博士学位),多年来,她们共同撰写了数十篇论文。但他们是非常隐私的,从来没有打算让工作与他们有关。“所有这些医学上的突破都是许多人努力的结果,”埃尔德林告诉一名记者,他在1985年想知道为什么他们的疫苗没有被称为肯德里克·埃尔德林疫苗,比如小儿麻痹症的索尔克疫苗。“我们不赞成这种想法,”埃尔德林说,“因为参与的人太多了,我们不想要唯一的功劳。你必须在疫苗上写上一连串的名字。”20世纪70年代,当女权主义运动开始关注女性被忽视的贡献时,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应邀出席NBC的“今日”节目。他们礼貌地拒绝了。
如果不是大急流城外的大峡谷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卡罗琳·夏皮罗·夏平,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的贡献可能会被遗忘。20世纪90年代,她听到当地女性谈论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的实验室,并深入研究她们的故事,最终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
夏皮罗·沙平采访的退休实验室技术人员之一是朗尼·克林顿·戈登,她是一名非裔美国人,拥有家政和化学学士学位,但未能在大急流城找到营养师的工作。潜在雇主称赞了她的资历,但解释说,他们认为厨师不会接受黑人女性的订单。一位朋友向肯德里克提到了她的困境,肯德里克为她提供了一份实验室工作。戈登告诉夏皮罗·夏平,她的任务是帮助她找到适合接种疫苗的博尔德氏杆菌菌株。一种百日咳毒株的毒力可能是另一种毒株的10000倍,找到合适的毒株对改进疫苗至关重要。“我每天都很努力地工作,”她说。“数以百万计的盘子。我还有眼睛真是个奇迹。”
一天早上,她开始工作,心想:“今天一定是这样的一天。”她开始整理盘子,突然发现了。“天哪,它太大了,太清晰了,”她后来回忆道,描述了细菌在周围培养基中吞噬血液的光环。“它只是告诉我:‘我在这里。’”她把那个盘子提请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注意,他们把盘子放了进去,“所有这些过程,重复、重复、重复,答对了,它就在那里,”戈登说。戈登的贡献没有其他记录。但和其他记得在实验室工作的人一样,戈登主要对自己参与拯救生命的工作表示感谢。
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都没有结婚。几十年来,他们一起住在一座舒适的四居室房子里,房子坐落在一个古老的苹果园里,坐落在一座俯瞰城市的山顶上。他们共享相同的休闲活动:阅读、园艺和观鸟。他们养宠物,经常一起旅行。雷德兰和她的姑姑和肯德里克在密歇根湖上的小屋里度过了一段时间;她说,有一次,他们在那里接待了她一个月,试图阻止她在19岁时结婚。(没用。)这两个女人互相照顾。埃尔德林在工作时试图修理空调时失去了一根手指,是肯德里克修剪了她的手套,缝合了手指。“他们在一起过着美好的生活,”雷德兰告诉我。“我认为从来没有一句严厉的话。”
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是否比同事和忠实的朋友更重要?当时,单身职业女性在一起生活很常见,因为她们只能勉强维持微薄的工资。在她的研究中,夏皮罗·夏平曾采访过一位名叫露西尔·波特伍德的化学家,他在20世纪40年代曾在实验室工作。当她问起这段感情时,波特伍德(Portwood)对夏皮罗·夏平(Shapiro Shapin)的录音机喊道:“我是女同性恋,如果那些女孩有什么阴谋,我早就知道了。”不管怎么说,他们的私生活只与他们自己无关。
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两位如此重要的医学先驱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与预防的矛盾性有关:当疫苗或其他医疗措施预防疾病时,它会导致人们忘记它预防的疾病。疫苗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目标,因为现在真实或想象的副作用似乎突然比疾病更严重。
肯德就是这样
......